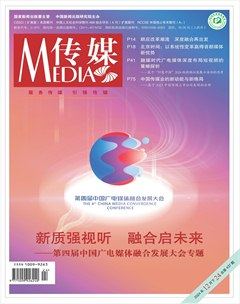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当前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发力方向。各级主流媒体如何通过媒体融合,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拓展媒体的功能与价值,已成为广受业内关注的议题。河南省项城市融媒体中心以构建服务型媒体为特色,突破媒体原有格局,利用媒体的信息网络优势,积极推动县域社会治理的媒介化、信息化、智能化,现已成长为地方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基础平台与创新力量。
媒体善治:媒介化治理的现实探索
县级融媒体的一大突出特点是地域贴近性,其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媒体服务功能的提升,实现自身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度融合。同时,“媒介化社会”的日渐成形,也推动着基层媒体的功能演进。媒介作为一种体系化要素开始更深刻地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并与之相融合,成为推动社会“善治”的核心驱动力量。
媒介化治理的发展趋向。“媒介化治理”的概念可以视为“媒介化”理论的一种延展,是媒介逻辑向社会治理逻辑嵌入的体现。媒介关联和重新塑造着社会各个领域,随着媒介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媒介化社会正在形成。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郭小安、赵海明曾发文谈道,“‘媒介化治理’不只将媒介简单视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而是将媒介作为新型治理哲学和‘治理权力信息化’的核心载体,在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融入媒介的基因,打造一种新的操作系统,或曰一种‘座架’,使之成为贯通和激活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动力机制。”媒介化治理是在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等各层面上所实现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它强调媒介与社会要素、社会环节的高度耦合,及其在社会治理中过程化和制度化的关键角色。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媒体作为信息传播和社会关系连接的基础平台,促使社会公共生活的各种参与者处于网络化、扁平化的系统结构中,弥合了现行治理范式与人们数字化生活方式之间的时代差异,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效能和多元化情境的适应性。
社区微治理激活自治潜能。“社区微治理”主要是指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造性地开发社区的自治潜力,带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长江师范学院尹浩认为,“社区微治理”的实质是力图改变目前城市治理权力和资源的配给方式。也就是说,“社区微治理”重在发挥社会力量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将治理单元从行政体系下移到社区,推动社区中人的治理关系变化,激发社区的自组织、自服务潜能。媒体具有天然的信息传播、社会协调与社会整合功能,在社区微治理的组织、动员、反馈以及技术基础设施提供等方面,均具有其他社会系统不可比拟的参与优势。近年来,项城市融媒体中心通过“媒体+服务”,构建了与各类政务资源、社会资源和用户资源广泛的链接能力,成为本地社会的信息枢纽和运营平台,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引领“社区微治理”,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上一个电子媒介时代,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美国学者赖特分别提出传播的“三功能”说、“四功能”说,揭示了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渠道,还在广泛地参与社会协调和社会文化的塑造。在当今的媒介化社会,主流媒体呈现出社区化、平台化的趋势,在更为深度地参与社会的运行,也为社会的多元协同治理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可能。
社区微治理的三项修炼。按照中央的部署,县级融媒体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主流舆论阵地,二是综合服务平台,三是社区信息枢纽。县级融媒体要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功能,同样也基于这三个方面的提升:第一,强化自身的公共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的作用;第二,发展自身多元服务提供者的角色;第三,巩固自身作为社会协同与整合者的地位。县级融媒体介入社区微治理,激发居民自治潜能,首先必须是一地的信息总汇和运营枢纽。为此,县级融媒体需要进行“三项修炼”:加强自身思想舆论的引导力、资源平台的整合力和社会生活的服务力。做好这三个方面,客观上对巩固国家的基层治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如今的媒体平台,已不再是单一的信息通路,其具备了聚合多种资源的能力,除了信息资源,还有社会资源、用户资源和数据资源。在这样的资源、数据的汇聚与整合中,媒体可以实现较之以往更为强大的社会服务功能,这不仅可以完成对传统媒体功能的升级,还可以通过介入人们的各种生产生活场景,发展为能深度参与社会运行与城市治理的“新型主流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