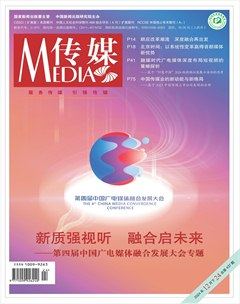摘要:刊物的时代背景、编辑宗旨与阅读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是传媒史和阅读史研究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引入概念史研究方法,通过对《新青年》中“科学”概念内涵从本体、方法和价值三方面的分析,旨在揭示文本核心概念与杂志编辑宗旨之间的关联。《新青年》涉及的领域从开辟多元主题向专注政治理论的转型;编辑理念由以学术争论引领舆论风潮转向以政治信仰开展革命动员;秉持的意识形态由崇尚自由主义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这些都见于作者笔下“科学”概念的工具属性切换。
关键词:《新青年》 科学 编辑宗旨 陈独秀
一本刊物的编辑宗旨,总是会约束着编辑对信息的收集、筛选和编排。而编辑工作的社会价值也正在这种信息的加工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在读者群体中得以实现。因此,刊物文章作者释放出的信息,就成为编辑宗旨和刊物价值之间的媒介。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既可以窥见编辑宗旨,也有助于评估刊物在受众之中的影响。笔者引入概念史研究方法,着眼于《新青年》这一中国近代极具时代特征的典型刊物,对其中高频涉及的“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展开个案分析,以期管窥刊物的时代背景、编辑宗旨和社会影响之间的关联性。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以下统称《新青年》),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6年7月25日为最后一刊,短短的十年多时间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和性质变迁重要的见证。关于其编辑出版史的研究不胜枚举,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早期的《新青年》主要以针对青年群体的思想启蒙为主,而后则转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共机关刊物。其中“科学”一词作为刊物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出现在每一阶段不同作者的笔下,其内涵有着时代所赋予的共同特征,也存在个体差异。据统计,“科学”一词在《新青年》中一共出现了1658次。鉴于出现频率高,及科学概念内涵的复杂性与相近、相反概念的多元性,故将“科学”一词在《新青年》中的用法,结合前后文语境,分为本体论角度、方法论角度和价值论角度三类进行分析。
一、“科学”概念的本体论角度分析
“科学”概念的本体论角度即从“科学”所涉及的知识范畴来看。结合“科学”的概念史可知,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无论是“格致”还是“科学”,已出现过所指代的知识范畴,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专指自然科学。在各个阶段的《新青年》作者中均可看到该种理解。任鸿隽在《何为科学家》一文中将“学”与“术”剥离,认为科学是形而上的理论,而非形而下的应用:“我们要晓得科学是学问,不是一种艺术……学是根本,术是学的应用。”另有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并称的用法,如马君武所言:“……不惟自然科学之理论上进步而已。凡技术工艺交通诸问题皆然,以造成今世界之文明生活。然其他精神方面及社会关系则不惟毫无进步,反有退步焉。”其不仅将理论与实践区别开,也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社会关系等领域分割理解。
2.指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总和。此种认知与前者的差异关键在于是否认同科学方法可以移植于人文社会领域研究,抑或对已有人文社会领域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是否持肯定态度。刘叔雅在反思一战之教训时,强调国家之兴衰存亡在乎科学,而“举凡政治、军事、工业、商业、经济、教育、交通、及国家社会之凡百事业,无不唯科学是赖”。将个体人文社会研究领域认同为科学的案例还有“实验教育学者,欧美最新之科学”“(孔道西)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马克思)郑重的归咎于经济科学的本身”等。1920年,陈独秀在对“新文化运动”的阐释中将狭义的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而广义的科学则包括了社会科学,可谓这种观点最具代表性的陈述。
3.指代自然科学和基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知识。这一种观点混淆了理论性的科学规律探索和实践性的技术应用。例如,“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德用闷杀瓦斯以攻敌。法则用铝质之嘴套以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