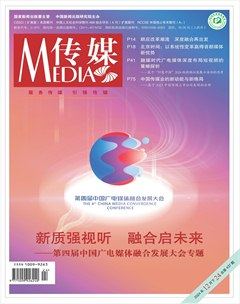摘要: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从思想到实践的文化革命,它不仅为中国电影的转向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思想启蒙,还为20世纪30年代及其后的中国电影创作提供了新方向。在这一时期,创作主体上的转向也重新建构了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中国电影从开始滞后于“五四运动”的崭新探索到开始探索民族文化和现实意义,使得中国电影从类型化的探索转向民族救亡和现实揭露的文化传播。本文聚焦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电影,论述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电影创作之间的联系及其对当下电影的启示。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 主体重构 民族主义 文化传播
20世纪初叶,《新青年》杂志高举“科学”和“民主”两大旗帜,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自此之后,新文化运动便成为现代中国叙述的元叙事话语,“反帝反封建”“爱国救亡和思想启蒙”的主题也凸显了中国亟须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命题。新文化运动所孕育的白话文、新思想、新政治和新文学,也成为达成这一命题必要的路径选择。甚至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绝大多数现代性叙事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此时的中国电影刚刚诞生十余年,逐渐摆脱了传统戏曲、文明戏的影响。在中国电影创作的萌芽阶段,创作者们将电影这一舶来品翻译为影戏,从翻译的名词便可看出电影人如何看待早期电影的发展方向,电影创作重点仍然是故事的戏剧性和中国电影的本土化。例如,张石川、郑正秋等人拍摄的《难夫难妻》、黎民伟拍摄的《庄子试妻》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社会问题、民族文化的典型影片。所以在新文化运动诞生并发展的时期,电影艺术正处于极力证明自身艺术门类合法性的阶段。20世纪20年代,上海明星公司拍摄的《孤儿救祖记》不仅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电影的本土化发展,更是让电影艺术进入了类型化创作的模式中。然而,这部标志着中国电影本土化的影片,其内容却仍类似于被时人所熟知的话本小说的苦情戏:一位善良贤淑的女子,经历了无数苦难,最终回归家庭。这一方面是传统叙事中“大团圆”结局的标准写法,另一方面也终归将女性放置于主流叙事之下。学者戴锦华在其文章《“五四”洪流中的一泾——中国电影的初创》中,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长期游离、滞后于新文化运动,中国电影的实践探索与新文化运动之间一定程度的“背离”成为主流论调。
诚然,早期中国电影创作中的主流题材,如神怪武侠片、鸳鸯蝴蝶派的时装爱情片、小市民趣味的时代片等,都更多地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学和现实性有一定的疏离。当然,类型化的影片创作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全部,早期影人的海外经历也重复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经历,在影片中再塑正面的中国形象,例如,张石川、郑正秋等人都在自己的电影理念中提到影片应该启发民智、治愈群氓。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的爆发,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电影也从类型化和市民阶层的趣味中摆脱出来,开始在现实题材中承担起文化现代化和重塑民族主体意识的责任。而在这一时期的电影艺术创作,被传统史学界以“左翼电影”这一名词来概述。李少白在《简论中国30年代“电影文化运动”的兴起》一文中表示,希望将“左翼电影运动”称为“电影文化运动”,因其体现了此运动领导者的地位。无论如何界定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其都增强了电影除传播传统文化外的现代性探索和政治动员功能,其创作也积极回应并主动践行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解放和革命性诉求。
一、新文化运动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主体重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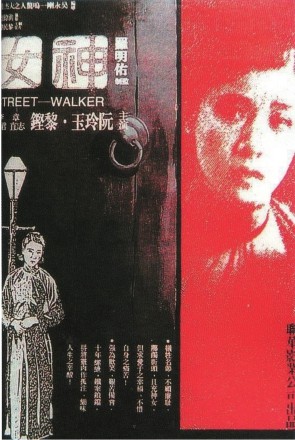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国土的大片沦丧更是唤醒了众多爱国人士。电影观众也从对市民阶层类型片的热衷,转向了对现实题材和救亡图存影片的深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