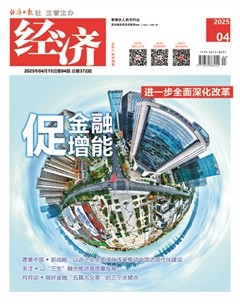从敦煌壁画的飞天,到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人类对翱翔的追求始终刻在文明的基因里。向天空“进军”不仅是对科技和空间的跨越,更是人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民航客机的主场一直在7000米以上的高空,而3000米以下的天空,则是一片亟待利用的广阔发展空间。2021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低空经济”;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将低空经济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低空经济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其为“新增长引擎”。如今,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低空经济已经成为各地争抢的“黄金赛道”。
作为我国低空经济的先行者,广州市有4200多家相关企业扎根于此,亿航智能、小鹏汇天、极飞科技等龙头企业云集,具有强大的产业基础。不仅如此,广州在低空经济政策出台、产业链配套、应用场景拓展等方面均走在前列。时至今日,广州已在低空经济领域创造了多个“第一”:拥有全球第一个飞行汽车工厂智造基地、全球第一家集齐从生产到商业化运营“四证”的企业、全国第一个国家级无人机器件检测中心、全国第一次城市公众复杂低空环境的飞行验证……从政策创新到场景落地,从技术攻关到标准制定,广州在低空经济领域不仅拿下了多项全球首创成果,率先搭建起“研发—制造—检测—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也为我国低空经济打造出了可复制的“广州样本”。
立法先行
低空经济通常是指以海拔3000米以下空域为主要运营空间,以有人或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各种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业态。正因是综合性业态,所以低空经济融合了航空制造、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诸多产业,是典型的新质生产力代表。然而,作为新兴产业,低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仍有诸多问号亟需“拉直”,如空域资源如何高效利用?飞行安全如何保障?应用场景如何拓展?
为了从制度层面突破传统空域管理模式,构建适应新业态发展的政策环境,广州市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为低空经济腾飞铺设制度“跑道”。2024年5月,由广州市发改委牵头组建的“广州市低空经济工作专班”正式成立,整合了广州空港经济区管委会等20多个部门和单位力量,统筹推进低空经济发展各项任务,这打破了传统行政管理条块分割的局限,为空域开放、技术创新、准入标准制定等关键问题提供了高效决策平台。工作专班成立后,迅速梳理出《广州市低空经济发展2024年重点工作清单》,并明确了责任单位和时间节点。在政策体系构建方面,广州打出了“组合拳”,去年5月,《广州市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正式出台,提出了重点目标、重点工作任务和保障措施,其中如统筹低空经济顶层设计、建设低空飞行服务站、拓展无人机物流应用场景等25项工作,分工至具体的部门。随后,7月又推出了《广州市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培育主体、建设基础设施、加大科技创新、拓展应用场景和加强要素保障5个方面提出了20条具体措施。今年2月28日,《广州市低空经济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作为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的低空经济领域地方性法规,这不仅是广州“向空图强”的里程碑,更是中国低空经济进行政策探索的破冰之举。为了让计划顺利实施,蓝图如愿绘就,产业快速发展与制度滞后的矛盾,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据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介绍,《条例》出台之前,广州相关部门开展立法调研时发现,低空经济存在“政府部门职责不清、飞行申办程序复杂、基础配套设施薄弱”等卡点堵点。例如,企业普遍反映适航审定周期长、空域划设不明确,导致商业化运营难以落地;无人机“黑飞”现象频发,急需统一监管平台。为此,广州历时近一年,听取企业和社会意见千余条,最终以法规形式系统性回应了产业痛点。
为了给低空经济发展铸就制度基石,《条例》围绕空域管理、基础设施、飞行服务、产业生态、安全保障五大核心领域,构建起了一套全链条、可复制的制度体系。空域是低空经济的“生命线”,如何充分释放空域资源,广州给出的方案是“分类管理+动态调整”,突破性地提出“分类划设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适飞空域和管制空域”,并通过市级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动态公布范围。例如,南沙区被划为“海陆空全空间无人体系试点”,允许物流无人机、载人飞行器在特定区域内开展商业化运营。同时,广州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探索空域分类管理和动态调整机制,满足企业差异化需求,这既保障了飞行安全,又为产业创新预留了弹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