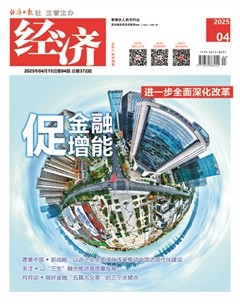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重要载体。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当前,县域承载了西部地区近六成的常住人口和接近半数的经济总量,广泛分布了大量生态资源和能源矿产资源,既是就地就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空间。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西部地区县域以产业升级为核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典型路径和存在问题,对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西部县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典型路径
一是资源能源开发:“技术攻关—数智赋能—全链重构”。西部地区县域资源能源富集,经济强县多以资源能源型产业为主导,通过构建“技术攻关—数智赋能—全链重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实现由“资源能源产地”向“产业高地”转变。2023年,西部地区神木市、仁怀市、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库尔勒市、府谷县6县(市、旗)GDP超千亿元,“千亿县”GDP总量达到8789.2亿元,均为资源能源型产业主导。该路径下县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低碳与清洁生产、新材料研发与高端化深加工、数字智能赋能等重点领域。调研显示,这类县域主要通过支持龙头企业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构建数字化平台提升过程管理和产出效率,牵引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和组织方式重构,实现产业示范引领与规模效应。例如,内蒙古准格尔旗构建“技术突围—成果产业化”示范链,针对联合中国矿业大学建成国内首个全维度碳监测试验基地,自主研发的高精度二氧化碳监测设备已在10个大型煤化工基地落地应用,助力传统煤化业碳排放显著下降。
二是生态价值转化:“价值识别—产品创新—价值转化”。西部县域生态功能区分布广泛,该路径下县域通过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双向突破,以构建生态价值转化链条为核心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价值识别—产品创新—价值转化”的正向循环。西部地区超过80%的县域生态功能责任重大,依托生态资源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强化底线思维,准确挖掘生态价值,以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赋能治理能力升维,逐步构建起生态价值实现闭环。调研显示,该路径下县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聚焦于推进生态治理与产业融合,加快生态资源市场化与资产化进程,推动碳汇等生态金融产品创新等特征。例如,四川平武县联合蚂蚁集团开发全球首个大熊猫栖息地生态资产核算系统,构建“无人机巡护—红外相机监测—区块链确权”技术链,实现1.2万平方公里生态资源数字化确权。依托生态大数据中心开发的碳汇储量动态模型,精准测算全县林草碳储量并在西部环境交易所完成价值数十亿元的碳汇质押融资。
三是富民产业引领:“成果转化—数字改造—产业融合”。西部地区有49.2%的县域GDP处在100亿元以下,以现代农业为代表的富民产业是西部地区县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阵地,通过构建“工艺革新—数字改造—产业融合”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体系,持续壮大富民产业。调研显示,该路径下县域依托地域特色和资源禀赋,深化特色农业种植养殖技术攻关与种业创新,以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加速现代农业产业链延链和供应链补链,逐步实现农业全流程数字化改造与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土地、资本、人才等要素配置效率。例如,贵州湄潭县通过建设茶叶“数智车间”,部署土壤墒情传感器、光谱分析仪等智能设备数千套,以深度学习算法建立施肥决策模型,大幅提升高端抹茶原料产出率。
四是应用场景创新:“场景挖掘—技术聚合—生态营造”。场景资源是西部地区县域新型劳动对象的集中体现,也是西部地区依托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途径之一。该路径下县域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通过“场景挖掘—技术聚合—生态营造”的创新路径,将特定场景转化为技术试验场、产业孵化器和价值倍增器,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重要的实验场所和应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