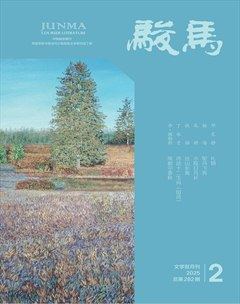1
小男孩满都呼晃着脑袋,他身后的小辫子跟着一甩一甩的。辫子细细长长,已经快到满都呼的腰上了。在巴音淖尔草原,男孩子的胎毛从出生起就一直留着,待十二岁生日的时候才可以剪掉。这个风俗已经保留上百年了。
满都呼想要一把弯刀,作为自己十二岁的生日礼物。
一把上好的弯刀,价格并不便宜。这个季节,又遇上大旱,草还没结籽,牛羊还没接羔,牧民们没有收入——尽管那一只只羊就是牧民们行走的钞票,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还要等一等。
2
一根火柴在满都呼的手里点着,小小的火苗扑闪着,燃着纸,燃着木屑,“噼里啪啦”像夜空中跳跃闪烁的星星。
满都呼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对着炉门慢慢地吹气。火燃起来了,填入一把细长的松枝,几块干牛粪,火上来了再劈柴加木块。
星星之火,燎原之势。满都呼在一本书上读到过,在印度古老的文字中,曾经描述火苗会越分越多,无穷无尽地分下去,可是火苗本身却没有减少。
火,越烧越旺。满都呼觉得火在房间里发出密语,它与自己有一句没一句地交谈着,和墙上的一幅画,一把椅子,乃至书架上的一本书打着招呼。一种超越物质的光芒从火中迸发出来,在毡房里流淌,无声无息,却香气袭人。
细细密密的汗珠顺着满都呼的脸颊滚落下来,他伸手擦拭了一把,红红的脸蛋上黑一道白一道,成了个“花脸猫”。
顾不得这些。锅中倒鲜奶再加水,撒适量的盐后放入砖茶,不一会儿香醇浓郁的奶茶翻滚着,香味四溢。
红红的火苗舔舐着黑黑的锅底,犹如一次跨越亘古的相遇。一种暖,氤氲了全身。
满都呼怕热。尤其是这个夏天,闷热、干燥。云朵干巴巴的,一滴雨水都拧不下来;空气里燥热的风,一遍又一遍地吹着。可是满都呼喜欢炉灶里慢慢生起来的火——温暖却不炙热,明媚又不夺目。
奶茶熬好了。满都呼取来一口锅,架在炉火上,转身打开水缸的盖子,水就要见底了。满都呼挠挠头,盛了一瓢,想了想,又倒回去一些。
只剩下这些水了。
毡房西侧的那口井,已经几天压不出水了。
大半瓢水填进锅里,再把羊肉一条子一条子地放进去,水开后,倒入大块的红萝卜和黄萝卜,然后撒下一把盛产在萨拉乌苏河畔的大粒盐。再无其他调味料。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这是满都呼一家的晚餐。牧民们的饭菜很简单,一来二去不过是那么几板斧:奶茶、炒米、手把肉……简简单单,没有太多的佐料和工艺,却很适合牧人们单纯而皮实的胃。大抵是因为熬得久了。这些来自大自然的赠予,成为孩子们日益长成的骨骼和肌肉。
热气腾腾的羊肉刚出锅,阿爸毕力格就回来了。毕力格高高瘦瘦,他的影子像一汪渠水缓缓地流进了自家的毡房里。
满都呼抬起头,看夕阳将天边的最后一抹云染红染透,预示着一天中白与黑的轮换。
放羊回来的毕力格,已经燃起了门口的火。每天这个时辰,牛羊入圈,倦鸟回巢,毕力格就会用鸡毛掸子拍拍长袍,抖落帽子上的土,拿白毛巾仔细地擦了手,点燃白色苏鲁锭下铜烛台里的蜡烛。蜡烛置于左右两侧,燃在五颜六色的经幡之下。烛火被风吹得悠长,恰似毕力格心中虔诚的祈祷。
苏鲁锭,是长矛。长矛是草原男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当他被腾格里召唤之后,灵魂就会寄托在他的长矛之上,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并给人以勇气和力量。
满都呼不过是个十一岁的孩子,却也渴望拥有这种力量。
如果再有一把弯刀佩戴在身上或是插在长靴子里,那就更符合自己的气质,更能匹配这种力量了。
小男孩满都呼想要一把弯刀,锋利坚硬,结实有力。几百年前,成吉思汗带领草原上的人们手持弯刀,驰骋战场,那马背上的绝杀,是何等的威风。
礼物像火苗,舔舐着满都呼的心。满都呼望着天边的红霞,把心里的小火苗按压下来。
伴着落日的余晖,阿妈娜仁花和妹妹格日勒也回来了,她们担回了萨拉乌苏河的水。
3
满满的两大木桶萨拉乌苏河水,清澈、凛冽。沉闷干燥的毡房里即刻有了生气。
这些水不能饮用,只能洗衣洗脸,喂给牛羊。水要怎么用,都得仔细地盘算好,一滴水都容不得浪费。洗衣服洗脸,差不多半桶水,一家人已经三天没有换洗衣服了,三头牛也得饮下半桶水,剩下的这一桶,先喂给小羊羔吧。明天,全家人拿上扁担木桶齐上阵,辛苦一些,多担几桶河水回来。
闷。
满都呼一个人走出毡房,看到落日的余晖投射到高高低低的雪山上,一瞬间,连绵起伏的山脉炽红如火,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它内部燃烧着,终又喷发出来。
草原使劲儿地铺展着绿色,尽管干旱折磨着它们,早早地黄了叶尖。几只鸟儿忽上忽下,反复跃动,它们的羽毛近似草色,一落下来就没了踪影,好像被草原吞噬了。
满都呼不知不觉走到了大门前,看着长矛般的苏鲁锭,双手合十,闭上了眼睛,长生天快快降下一场大雨吧!满都呼的虔诚不比阿爸少,他坚信自己的命运和行为与整个草原相连。
起床的时候,他总是先穿上左脚的靴子,然后才是右脚。左脚先落地,才能更清晰地听到大地的心跳声。
吃饭的时候,他和阿爸一起,用刀子切下几块牛羊肉,走出毡房远远地抛在草地上,嘴里念叨着:“感谢大自然!”
有星星的夜晚,他就去看枣红马“追风”的眼睛,据说,马的眼睛可以感知北斗七星的移动。北斗七星在哪里,马儿的眼睛就看向哪里。
北斗七星,给草原的生灵以方向,以希望。
满都呼记得,春天刚刚降临的时候,巴音淖尔草原离太阳很远。
天空,是长方形的。那时雨水丰沛,草木见风就长,把河水里的天都遮住了。萨拉乌苏,有着风的自由和草的颜色,以及太阳的味道。
暮春时节,萨拉乌苏已是塞上江南般的模样。萨拉乌苏河水清澈碧绿,迂回荡漾;两岸草儿碧绿,繁花盛开;飞鸟对着大柳树,“叽叽喳喳”地歌唱了一整个季节;小虫子从《诗经》中爬出来,在温暖的潜流中蠕动,爬行,振翅,飞翔……一瞬间,各种颜色各种形状各种声音在大地上膨胀扩张,将生命的样子慢慢勾勒在萨拉乌苏河畔。
这里,也是数万年前“河套人”的家园。满都呼的阿爸阿妈从小生活在这儿。
可是到了夏天,萨拉乌苏河说瘦就瘦了。巴音淖尔草原进入了旱季,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下雨了。
萨拉乌苏河段大部分河流变浅变细,部分河段有大块的石子被冲刷出来,裸露在外面。有的河段甚至干涸,只剩下离满都呼家五六公里的一段,以及更远的敖包村的一段,还有水流。
不过,这两段水流也在慢慢变细变窄。
这是几十年来,这片草原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
干旱、沙尘暴、暴风雪……面对自然灾害,草原一次次顽强地挺了过来。缓过劲儿来的草原,辽阔碧绿,牛羊肥壮,宛若新生。
今夏,是长生天对草原的又一次考验。
晚风袭来,几只白鸽扑棱着翅膀飞回自己温暖的巢穴,夕阳一头跌落进河水里,满都呼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在慢慢放大,像阿爸那张沮丧而忧郁的脸。
毕力格把从水缸里取出来的卧着少许细沙的半碗水端到嘴边又放下,取下挂在墙上的白毛巾,从木桶中倒出一个盆底的水,捏住毛巾的一角在水里蘸湿,细细地擦拭自己的脸。白毛巾染成了灰色——这是两天以来阿爸第一次洗脸。毛巾搭在肩上,阿爸一口气喝下碗里的水,舔了舔碗底,小心地拂去水缸盖子上的灰尘和细沙。缸里已经没有多少水,可陶利苏木的送水车还没有到来。
阿妈、满都呼和格日勒,也用毛巾擦了手,和阿爸的方式一样。他们笑起来的时候,弯弯的眉眼也是一样的。
阿爸切下几块羊肉,抛到草地上,嘴里说着:“感谢大自然!”然后端坐下来,一家人吃了晚饭。谁都没有说话,只有炉火忽明忽暗。
吃罢晚饭,阿妈和格日勒取出少许的水,简单擦拭了碗筷。洗碗水,泼在外面,滋润了干渴的小草。
满都呼拎起两只铁桶走出毡房,等待陶利苏木的送水车。
天就要黑了。四周空空寂寂,草原瘫痪在一片热浪里。侧起耳朵,满都呼分明听见风沙赶路的声音,沙丘仿佛正一点点吞噬着这片漠中草原。放眼南沙梁,鸟雀的羽毛覆盖了一层又一层,满都呼叹息着,知道那些鸟儿是飞不过这片草原的。
他抬起头来看天,又垂下,好像在恼着自己,却没个地方说理。那些来来往往的闲云,抖落不下一滴雨,眼看云里有了些许雨意,黑得像一块墨,却被一阵不明方向的风刮走,跑到荒无人烟的沙地里“稀里哗啦”下了几天雨。
满都呼把汗衫罩在头上,慢吞吞地挪到树荫下,那匹枣红色的老马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地躺着,鼻子里不断喷出一股股热气。一只蝗虫跳到老马身上,它连甩尾巴的力气都没有。远处,蝗虫密密麻麻,这些家伙啃噬过的地方寸草不生。满都呼把头贴在老马脸上,它睁开眼,伸出枯草般的舌头,舔着满都呼手心里的汗珠。满都呼的手上火辣辣地疼,他看到老马的瞳孔在渐渐放大——在它绿野长风般的眸子里,满都呼看到了往日青翠欲滴的草原。
老马已经几天没有喝水了!满都呼忽然想起来了,他猛地一拍大腿,跳起来返回毡房,从木桶中舀出一大瓢水,倒在老马面前的水槽里,抚摸着老马稻草般扎手的马鬃,轻声呼唤着它。老马用鼻子嗅了嗅,腾地站起来,扬起脖子朝着天空一阵嘶鸣,又转身朝着更远的方向,叫了一声。一匹枣红色小马应声跑过来,舔了舔老马的眼睛,低下头喝着槽子里的水。
满都呼怔怔地站着,眼前一片模糊,脸上的肌肉抖动不止。他拎出了一桶水,打开桶盖,蹲在旁边直伸舌头的猎狗大黑跑了过来,枣红色的小马跑了过来,栖歇在老榆树上的一只只麻雀冲了下来……
满都呼已经泪流满面。
拥着日落,喉咙里噙着一团火的满都呼昏昏入睡,他听到了风声,又像是雨声,更像是从远方放牧回来的牛羊的叫声。
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打破了草原的寂静,陶利苏木的水车来了!
满都呼一跃而起,抓起铁桶奔过去。踏着走一步暗一层的草色,满都呼呼喊着阿爸出来担水,自己先担着满满两大桶水往回走,一步一摇,尽管盖着盖子,水还是会不时地溢出来,惹得追在满都呼身后的那只麻雀,围着水桶一圈圈地飞,“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时而俯身下来汲取落在草叶上的水珠。满都呼没空驱赶它。
扁担把满都呼瘦弱的身子压低,他的小脸通红,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一步不停地向前走着。满都呼和这片草原一样,有着自己的倔强。
这片草原,已经生息了上万年。那些裸露的草皮,像伤疤一样,向人们诉说着她经历了多少次风霜雨雪、雷电冰雹。千百年来,很多动物,比如诺氏古菱齿象、王氏水牛、河套大角鹿、原始牛等,都在这片草原灭绝了。可是不久之后,新的生命就会来到草原,红狐、猞猁、狼、獾……在风中撒下一粒种子,就会在这片草原上发芽、长叶、抽枝、结籽……
缸里的水满了,盆里的水满了,碗里的水也满了——都要溢出来了!满都呼一家人的心,也满满当当的。这些水,可以抵挡一阵子了。
黑暗吞噬了一切,萨拉乌苏进入了梦乡。
满都呼睡不着,他手里握着一把弯刀——桃木的刀鞘,桃木的刀刃,有棱有角,这是满都呼自己打造的刀。一砍,一削,磨磨打打,雕雕刻刻,一截平平常常的桃木枝干,就成为一把手枪,一只飞鸟,一匹骏马……
满都呼用眼睛和心,把天上人间的好东西,收拢在自己眼前,栩栩如生。
阿妈和格日勒都赞叹不已。
还有另外一把刀,长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像小树一样,越长越高,越长越壮。
4
一阵嘈杂声,搅乱了平静的夜。
紧接着,猎狗大黑咆哮起来。
听到响动,阿爸毕力格匆忙披衣起身,顺手抄起立在门后的烧火棍,打开了门。
满都呼点亮一盏马灯,紧随其后。
借着马灯和月光,满都呼看到两只芦花鸡断了翅膀,左一下右一下,倒在地上胡乱地扑腾着。
一只大黑鸡被咬断了脖子,鸡毛散落,汩汩地流着鲜血。这只黑母鸡,体型肥硕,羽毛黑亮,全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像夜一样深邃神秘。黑母鸡来到满都呼家已经快两年了,满都呼最喜欢它,唤它“黑珍珠”。
“黑珍珠”受到了满都呼的偏爱与优待。春天和夏天,满都呼把它放出来兜风,任凭它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地捉小虫子吃;冬天,拾来干草和旧衣服,给它铺一个温暖舒适的窝。
当然,“黑珍珠”也从未辜负过满都呼。每天清晨和黄昏,它都会卧在干草上下一个蛋,然后扑打着翅膀,踱着小碎步,冲着毡房“喔喔”地叫几声,向满都呼邀功。
“黑珍珠”下的是双黄蛋。这样的鸡蛋,满都呼可是舍不得吃的。双黄蛋在陶利苏木的集市上很受欢迎,可以卖上一个好价钱。鸡蛋换了钱,满都呼买了一套四大名著,每天晚上睡觉前看上一小段,梦里都是铁马冰河的波澜壮阔。
鸡蛋再攒一段时间,自己采的甘草也卖了钱,或许可以买一把弯刀。
可是现在,“黑珍珠”死了,鸡蛋没有了。弯刀遥遥无期。
满都呼很伤心,更多的是愤怒。
是谁闯进了满都呼的家?
一只猞猁。
这只猞猁,毛发棕黄,身子和猎狗大黑一般长。远远地望去,猞猁酷似虎崽,但是不同的是,猞猁的耳端有一撮好看的簇毛,这让它优雅了许多。
往往,猞猁不和牧人打交道,它们轻易不会踏入牧人的领地。这一次,可能是耐不住饥饿和干渴了。
猞猁叼着一只芦花鸡,准备蹿到鸡舍旁的矮墙上,伺机逃走。
芦花鸡哀鸣不已,扑棱着翅膀奋力挣扎,却无济于事。
看到毕力格和满都呼,原本只是在原地咆哮的大黑,忽然有了底气。
大黑呲着牙,毛发竖立起来,把身子拱成了一弯弓。大黑已经做好了准备,战争一触即发。
大黑狂叫几声,冲了上去。
猞猁灵巧转身,躲过了。
四目相对。
突然,猞猁一个腾空跃起,向大黑的肋侧猛地一抓,大黑轻松闪开了。猞猁趁着大黑分神,又朝大黑扑来,大黑先是一个回旋,接着向前一阵小跑,当猞猁猛追上来时,大黑忽然一转身,照着猞猁的后腿狠狠地咬了下去。
大黑咬住猞猁不松口,毕力格赶紧上前,用烧火棍卡住了猞猁的脖子。
芦花鸡得救了。
满都呼抱着芦花鸡,用马灯照着亮,前前后后地检查了一下它的伤势,好在并无大碍。
鸡被猞猁咬死了一只,咬伤了两只。
满都呼朝着猞猁的肚子狠狠踢了一脚。猞猁“呜呜”地叫着,它自知理亏。满都呼还想再补一脚,被毕力格制止了。
你的命我的命,都是一条命。这是古人留下来的道理。
它实在是饿坏了——如果是只强壮的猞猁,大黑不一定是它的对手。
这是只雄猞猁,它两颊后方有相当长的颊毛,好像关公风度翩翩的髯。
这些颊毛,或许可以做成上好的毛笔。满都呼想。
阿妈和格日勒,隔着窗子目睹了这一切。不需要她们帮忙,满都呼已经是个小小的男子汉了。
猞猁被满都呼关进了大柳树下的铁笼子里。该怎么“处置”它,满都呼还要再想想。
笼子里的猞猁,把铁笼子挠得“咔嚓”作响,凄凄地叫了整个晚上。
第二天,还是没有雨,太阳毒辣辣地炙烤着大地。迎着耀眼的光芒,满都呼一阵眼晕,他忽然就想起了天上九个太阳的故事,一个太阳都这么毒辣,如果九个太阳,要人怎么活?
刀子泛着银光,同样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一身猞猁皮,应该很值钱的——或许,就是一把弯刀的价格。
想到这儿,满都呼竟有些兴奋。
举起手中的刀子,满都呼慢慢靠近猞猁。他看到猞猁正瘫坐在笼子里,有气无力地望着自己。
见到满都呼,猞猁忽然站起来,又跪下,像人一样作着揖,可怜巴巴的。
满都呼停下了脚步,刀子落在半空中。满都呼那颗绒毛般柔软的心颤抖不止。
“咣当”一声,满都呼手里的刀子掉在了地上。
每个动物的身上,都有一盏灯,神明一样地居住着。
满都呼叹息着,要怪就怪自己运气不好吧,只是可怜了那几只鸡。
这样说着,满都呼打开了铁笼子的门,做了个“走”的手势,说了句,走吧,可怜的!猞猁疑惑地看着满都呼,直起了身子,慢慢地探出了前爪,刚要走出笼子,又退了几步坐了下去。它伸出长着倒钩刺的舌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聪明的孩子立刻就明白了。
“哎,真是欠你的!”满都呼指着猞猁的脑袋说。
虽然说着,满都呼还是端来一碗水,放在猞猁面前。猞猁看了看满都呼,又看了看面前的水,喘息得更加厉害了。
满都呼又做了个“请”的手势,猞猁好像懂了,它低下头,飞快地将水舔舐干净,又抬起头,望着满都呼。满都呼会意了,又添了一碗水。
连喝了五大碗水,猞猁瘪瘪的肚子涨了起来,圆滚滚的,像个鼓足气的大气球。
看来,它渴坏了。
喝饱了的猞猁,抖了抖身上的毛发,“噌”的一声蹿了出去,像一团跳跃的花火,越跑越远,在隐没于草原深处之前,猞猁转过身来,向着天空长长地嚎叫了一声,渐渐地成为一个小黑点,消失不见了。
满都呼目送它跑远。
放走了猞猁,满都呼不后悔,它是草原的生灵啊!至于弯刀,那就以后再说吧。
如果天堂是留给那些善良的人的,那么满都呼,一定会有一席之地。
就在放走猞猁不久,雨忽然来了。
晌午刚过,一团团乌云就压了过来,天空阴沉沉的,几只鸟儿在微风里划了一个圈后,低低地飞过。大黑似乎也有一些烦躁,东一下西一下地乱窜,不时地“汪汪”叫上几声。草地上的蚂蚁大军也出来了,它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来来回回,把一粒粒米朝着自己的巢穴驮去。
一声响雷刚过去,天空又炸开了一道闪电。
雨来了!
这些雨,先是银丝、细线,后来就“哗啦哗啦”连成一片。天地间灰蒙蒙的,已分不清是晌午还是黄昏。
满都呼和妹妹格日勒趴在窗边,数着屋檐下的水滴。
雨越下越大,一滴一滴的,像是落进了满都呼的心里。
雨声那么大,敲得玻璃窗子噼啪作响,可是满都呼这晚睡得最踏实、最安心。
5
雨下了两天两夜。
太阳出来了,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小草的芳香——喝饱了水,草原活泛了起来,萨拉乌苏河醒了过来。
满都呼和格日勒跑出来,顾不得脚下的泥泞,一个往井里倒水,一个按压井把,那口水井里的水,就一汩一汩地冒了上来。
一家人都笑了,他们笑起来的样子,就是萨拉乌苏河水清澈流淌的样子。
水的问题解决了,不用再等陶利苏木的送水车,一家人也不用去河里担水了。每天,阿爸和阿妈去放牧,放学回来的满都呼和格日勒,负责把晚餐做好。
篝火燃起来了,松树枝的香味弥漫开来。大自然是辽阔的房屋,风为友,花做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着草垛捆了多少捆,母羊产下了多少只羔子,粗茶淡饭也吃得无比惬意。累了,倦了,往草地上一躺,看月亮,数星星。
牧人和草原,就像旧时光里的老友,一手敬天空,一手敬草原,撒下满满的人间情谊。
满都呼知道,生命中的每一个时辰,都是余烬追逐烟火的时辰。
花高一寸则风矮半截。风从花上吹过,是风的声音,还是花开的声音?无法分辨。
草从春天长到了秋天,就有了阳光的颜色。草原上的草,总是吃几口阳光,停几口;停几口,又攒几口,然后直挺挺地抬起头,看着太阳。即便是枯萎发黄了,太阳也是草永远感激的神明。
这年秋天,满都呼家的草堆了一捆又一捆,羊羔多了一只又一只……
踩着秋天的尾巴,跟着一朵流云,满都呼和格日勒绕到萨拉乌苏河北面的一片沙地旁玩耍,那里除了有各种各样的石头,还有大片大片的岩画。
在萨拉乌苏,岩画和花草树木一样,随处可见。岩画活在人们的生活中。读懂这些岩画,也就破解了萨拉乌苏的地质密码。这些岩画,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它们是最生动的画面和文字。马背上长大的孩子,从岩画中读懂了历史,也读到了属于一个人的别样风景。
满都呼和格日勒,常常来这里看岩画,讲故事。
在一片岩画的尽头,无意间,满都呼发现了一副动物骨架。它只露出一个头和一只爪子,大半个身子都埋在沙里。看着嶙峋的骨架,森森的骨头,满都呼没有恐惧和害怕,反而异常激动。早就听阿爸说过,几十万年前,萨拉乌苏曾是广袤的森林草原,出没着数也数不清的扁角鹿、羚羊、披毛犀、纳玛古象、虎豹豺狼、原始牛、野马、野驴等多种古动物——此刻,它们风沙也吹不散的骨架化石穿越时光,重新出现在眼前。
怀着兴奋与期待,满都呼呼喊着格日勒,让她小心地托着骨架化石,自己则慢慢地把沙子一层层扒开,这才发现,骨架完整结实,身子前倾,似乎还保持着动物生前奔跑的姿势。是谁让它停下了脚步,长眠于此?又是什么原因让它腐蚀了肉体也要保留一副硬骨头?答案只有萨拉乌苏河畔的风知道。
他们更加好奇的是——它是谁?没有皮毛、没有标签,仅凭一副骨架化石,很难辨认它的身份:如果没有耳朵,一只兔子看起来与猎豹没什么区别,猴子的头骨也只在大小上与人类有所不同。
可是这个“大家伙”,比满都呼还高出一个头,身长有一米多。两个小家伙欣喜若狂。尤其是满都呼,抚摸着嶙峋的骨架化石,眼睛里放着光,好像能喷出火来。
满都呼和妹妹,一前一后,抬着搬着,决定把这个大家伙带回家。
眼瞅着太阳就要落山了,回去的路上,满都呼和妹妹没有走大路,而是抄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近路。
“阿爸和阿妈会同意把骨架化石带回咱们家吗?”妹妹有些不放心地问道。
“会的。”满都呼拍拍胸脯。
一路上,几只不知名的大鸟飞过,惹得满都呼多看了几眼,若不是妹妹召唤,满都呼差点走到水沟里去了。几只野鸭子倏地飞出来,又把格日勒吓了一跳。
那场大雨之后,雨就一场连着一场,萨拉乌苏河的水涨起来了,大大小小的水泡子多起来了。有了水,草就绿了,牛羊就壮了。有了水,草原上的各种动物也出来了。
走到一处深草丛中,他们发现好像找不到家的方向了,满都呼说向南走,格日勒说向北走才对;满都呼说前面是东,可是格日勒说是西。
他们谁也无法说服谁,像两只无头苍蝇一般,向左手的方向走一会儿,又转身向右手的方向走去。走了很长一段路程,发现还置身于茫茫的草中,却看不到尽头。
满都呼急得直跺脚。
“我们这么久没有回去,阿爸和阿妈一定急坏了!”格日勒急得哭了出来。动物骨架化石也被晾在一旁。
哭声惊动了风。
从东边吹过来的风,路过这片草地。草丛中窸窸窣窣一阵响动,一条小花蛇披着落日的余晖立在满都呼和格日勒面前,看着迷茫不知所措的兄妹俩,昂起头,吐着信子,甩着尾巴慢慢靠近他们。
满都呼愣住了,本能地后退了几步,转身抓住了骨架化石防身,可转念一想又不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破坏!
格日勒揪了一把草,紧紧地握在手里。可是草又不长手,怎么能用来对付蛇呢!
蛇扭动着身子,越来越近了。格日勒吓得闭上了双眼,满都呼大喊一声,冲到妹妹面前,张开了双臂护住妹妹。
这一喊,小花蛇愣住了,它不再靠近,而是在离兄妹俩大约半米的地方停下来,晃了一下脑袋。
一切都安静下来。
突然,草丛中蹿出一只“大猫”,张开嘴就叼走了小花蛇。
满都呼张大了嘴巴,定定地看着这一切,半天没反应过来。
“是一只猞猁!”
格日勒指着“大猫”奔跑的方向,大声喊。
满都呼长出一口气。
“是我放走的那只!”满都呼骄傲地说。
“草原上的猞猁都长得一个模样,你怎么知道就是你放走的那只!”格日勒不服气地说。
“哎——总之,就是那只!我认得它那漂亮的颊毛!它还有着和我一样的善良和聪明——再说了,这草原上还有哪只猞猁,会在这么紧要的时候出现呢!”
“好像是这么回事!”格日勒觉得这个说法合理。
“哥哥,那只猞猁朝着那个方向走了,那里——会不会是咱们毡房的方向!”格日勒眨眨眼,突然说出了这个大胆的想法。
兄妹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视一笑,继而拖着骨架,朝着猞猁奔跑的方向走去。
约摸一炷香的工夫,兄妹俩回到了家。
拖着这么大的骨架化石,走了这么远的路,小格日勒累得满头大汗,呼呼地喘着气,一屁股就坐在了老榆树下。
满都呼顾不得擦拭额头上的汗珠,迫不及待地跑到书架前,抽出那本《远古时代的萨拉乌苏》,看了一遍又一遍,终于知道:这是一头王氏水牛的骨架化石,距离现在有上万年了。从大小来看,是只还未成年的王氏水牛。
“把它放在哪里才好呢?”
“就放在自己的房间吧。”满都呼把骨架慢慢地抱了进来,放在了书桌旁的角落里。那个位置,不大不小,好像是专门为它设计的。
阿爸和阿妈看到了这副骨架化石。他们默许了。他们很少干涉孩子们的喜好和自由。尽管是成年人,但是一直以来,他们都以一颗孩童之心,温柔地看待这个世界。
夜,深了。
远古,微风拂过萨拉乌苏河畔,吹得两头王氏水牛身上的毛发微微飘动。高大的王氏水牛站在河边低头喝水,浅浅的河水刚刚漫过脚踝。突然,远方传来诺氏古菱齿象的吼声,两头王氏水牛不约而同地抬起脑袋,头上两根粗壮的大角指向身后……
一个激灵,睡梦中的满都呼醒了。
满都呼赶忙起身下地,打开灯,看到王氏水牛的骨架化石还好好站在那里。
找到动物的骨架化石,这件事好像给满都呼的生活开了一条缝隙。这条缝隙里透出了月光,清风和草儿的清香,也透出一份活力和一股不可言说的力量。
满都呼好像明白了什么。有些东西,原本就不属于自己,就像有些书,永远都不会落在自己的手中。
摸摸小辫子,小男孩满都呼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满都呼找来平板车,把王氏水牛的骨架化石捐给了萨拉乌苏博物馆。
阿爸阿妈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妹妹也以哥哥为骄傲。
拉着这只王氏水牛的骨架,行走在萨拉乌苏金秋的河谷间,呼吸着温润的空气,望着蜿蜒流淌的河水,满都呼挺直了腰板,他找到这古动物骨架化石并捐献给博物馆的这件事情,值得子孙后代一直炫耀和传承下去。
6
一些素未谋面的事物,好像都长在了小男孩满都呼身上,比如,上天顾佑,健康成长。
这年冬天,雪花像庄稼一样,下了一茬又一茬。纷飞的大雪,白了毡房,白了草原,白了岁月。
很快到了年底。满都呼把墙上的日历翻得卷了边,掰着手指头数着日子——祭火节那天,就是自己的十二岁生日!
一年一度的祭火节来了。
祭火之于满都呼一家,是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一套繁琐的仪式下来,完成的是一次团聚,一次回归,一次对曾经亲近温暖生活方式的声势浩大的怀念。
这一习俗已经沿袭了几百年。
无独有偶。不仅是在这片草原,在遥远的国度西班牙,祭火节这一天,人们放火迎接春天。
在祭火这一天,满都呼一家除了要摆上一家人喜欢的奶酪、枣饼、牛羊肉等,还要准备胸叉肉和祭火饭。
阿爸和阿妈要在这一天大显身手。
腊月廿三,天刚蒙蒙亮,阿爸和阿妈就轻手轻脚地起了床,虚掩上满都呼和格日勒的房门,进厨房准备祭火用品。
羊胸骨和羊胸骨汤是必不可少的。
羊胸脯冷水下锅,再撒入一把大粒盐,煮熟后捞出。
阿爸拿起刀子,仔细地划过羊胸脯,不碰触胸腔内侧,刮去外部表面的全部肉质,只留下由基础骨体和周边软组织组成的完整胸脯骨架,胸腔内侧朝上安放在专用的祭品盘里。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看似简单,却是阿爸十几年来一次次练习后的熟稔,这里面有技术,更多的是对家人的爱,对生活的爱,以及对草原的爱。
阿妈取来五谷杂粮、五色布条、奶食品、香、杜松叶等,一一装饰在羊胸脯上,再用羊头顶的毛搓成毛绳,从胸脯骨架的胸骨柄开始缠绕到一对胸叉骨上,在上面放置掏空肉质的、只带薄膜的完整胫骨,两边对称放置一条同样刮掉肉质的长条排骨。这样精细的活计,自然由阿妈来完成。
还有一道程序。取来蓝色和白色的哈达盖住,上面点上奶油,用网状羊油盖住胸骨顶部,安放在祭祀的桌子上面,这样一个完整的羊胸骨祭祀品就准备好了。
阿爸和阿妈用一双灵巧的手,完成了一件“艺术品”。
接下来,就是准备“祭火饭”了。阿妈把煮熟的羊胸骨架的肉汤倒入锅内,再放入大米、黄米以及红枣、葡萄干等原料,用小火慢慢熬,香气腾腾的“祭火饭”就大功告成了。
一个钟头后,太阳升起来了,满都呼和格日勒,也在香气萦绕中起了床。
“真香呀!”满都呼吸着鼻子,使劲儿地嗅着。
阿妈拍拍他的肩膀,笑了。
一家人开始换衣服。阿爸和阿妈穿上了藏青色的蒙古袍,他们给对方系上了腰带,整理抚平褶皱的地方。满都呼选了一件深灰色的袍子,这样看起来更像个大孩子了。格日勒穿上了早就中意的粉红色袍子,蹦蹦跳跳的,像春天里翩然起舞的蝴蝶。
篝火燃起来了!就在白色苏鲁锭的前面。
红彤彤的篝火,青灰色的烟,像冬夜里的雾。烟流动着,像纱一样笼罩四周。
一家人围着篝火,火苗温暖着每个人。
阿爸阿妈也是生生不息的篝火,一直温暖着孩子们。
祭火后,阿爸给满都呼剪掉了养了十二年的小辫子。满都呼成为真正的小男子汉了。以后,这世上的风雨再袭来时,满都呼就可以把阿妈和妹妹护在身后了。
回到毡房,美食上了桌,阿妈笑盈盈地端来了生日蛋糕。
蜡烛燃起来了,火苗轻盈,跳动。阿爸和阿妈拿出了送给满都呼的生日礼物,是一把蒙古弯刀。
这把弯刀,月牙形,泛着明晃晃的光泽,刀柄和刀靴是用牛角和牛骨制成的,带扣镶嵌红色石头,内填珐琅,外套骆驼骨。
弯刀出鞘,长啸一声。曾几何时,草原的骑兵和沙漠的雄鹰被历史的洪流卷走,弯刀却保留下来,依然被人们讲述着,书写着无尽的传奇。
虽然不知道价格,但是满都呼知道,这把刀,和自己的气质很符合。
满都呼把刀紧紧地握在胸前,前前后后地摸了一遍又一遍,嘴里一个劲儿地说着谢谢阿爸阿妈,眼里已经泛起了泪花。
格日勒拥抱了满都呼,送给哥哥一本书,一本关于草原的书。
火光中,满都呼轻轻地闭上眼睛,许下了生日愿望:愿来年风调雨顺,牛羊肥壮,家人安康!
【作者简介】邓文静,80后。在《民族文学》《中国校园文学》《草原》《飞天》《四川文学》《山西文学》等发表小说散文六十万字,有小说被《长江文艺·好小说》《特别关注》选载。曾获第四届萨冈彻辰文学创作奖,内蒙古职工文学创作一等奖。
责任编辑 乌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