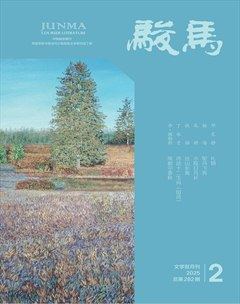站在小院,看天,看山,看星,看月,看花,看树……小院不大,心却很大。
一方小院,集天地之生息,纳四时之光泽。
一
我家院落始建于1963年。那年一场大水,冲毁了父母的老屋。于是,他们从河边搬迁到离水较远的村边,建起三间石头瓦屋,背靠一条街道,坐西朝东。
对于当时的灾情及灾后重建我一无所知,只知大姐是那年生的。父母和我们姐弟六个,最初便挤在西屋的石头瓦屋里。
石头很硬,屋里却是一团吵闹中的生气,温暖、柔软而有质感。
20世纪80年代初,我五六岁时,院落北面又起了四间石头房。
石头,在我们山里头到处都是,并不新鲜。我儿时,所见之处,院墙是石头垒的,房屋的围墙是石头垒的,就连一些梯田也是石头垒的埝墙。
那时盖房的很多细节都已模糊,只记得父亲让我拿着背筐捡小石头子。这些小石头子填槽的填槽,当眼石的当眼石,小石头子也派上大用场。我这小孩也似有了大用场,经父亲一表扬,更是干得欢。
工匠和小工多是本村人,那时还不兴工钱,只是管饭管酒。但能盖几间房,着实不易,无论是备料还是找人,都不是简单的事,何况父亲已五十多岁。
当时我毫不在意房子是如何起来的,渐渐大了,也帮过一些工,才大致了解盖房之序。先是打地基,按房子结构间数挖深沟,开始从沟底垒石头,约一米多高后往间空添土与碎石,地基打好后起木柱,上柁架檩,间架起来后继续用石头垒墙,叫打筒儿。打好筒儿后檩间钉椽,椽钉好后再上笆。笆多是用从山上割的荆条子编织而成的,整个一块铺上去,然后敷泥上瓦。之后便是安门窗及装饰性细节了。后墙、侧墙主搓沙灰,内墙是先抹层草泥,抹平后再抹白灰。前面的一些石墙,多用青灰着的墨线,书写联句,绘些梅兰松鹤及各种图案。
斯时,老家院落大体格局已定。北屋是父母和我住,西屋是5个姐姐住。看顶上露着的笆与泥都还是新的,有时我还担心泥会掉下来。大柁是曲的,檀是直的,墙是亮白亮白的。
北屋邻街最初预留了一间空地未建,或许是一时实力不允许。也因预留这一间,西屋让出了半间,三间改成了两间半。预留的空地,架起柴草棚。就因为是个棚子,这里便成了我和小伙伴们捉迷藏的好地方。
这一间是又过了几年建的,建好后四间房就成了五间房。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退休后,还和母亲在这间屋子里经营过两三年小卖部供我读高中。
生活在于营造,庄稼户的院子在于不断添加。前后几年间,在院里的犄角旮旯又盖起三四间小平房,或是放些杂物,或是当牲口圈。这些小平房都是父亲带着我们姐弟一个个建起来的。
到了过年时,屋里便不是四面白墙了,而是贴了年画。年画看起来不仅新,也似乎盈满喜气与生气。我记得有一年过年,父亲买回来骑着高头大马的元帅画像。一张一张,在墙上贴了长长一溜。看过来看过去,我最喜欢的是贺龙元帅的那一张。
渐渐的,墙上的画便有了改变。姐姐们有了自己的喜好,赶集买了很多明星画。有站在板柜上张贴的,有在下面指手划脚的,嬉笑间,一个个美人便上了墙。打眼一看,整个屋子都活色生香了。那时的美人,没有现在这么多脂粉气,纯美中各有味道。你看她时,她也在看你。
父亲对画风的改变并不在意,母亲却十分不满,并提出要求,无论怎样贴,不能少了她爱看的戏曲画。但因美人图实在太多,给母亲买的那张戏曲画便被挤到炕上的墙面上。其实,我也喜欢看戏曲画,一格一幅画,还有些配文,连环画一般,把故事讲得明明白白。那些画里,有才子佳人的传奇,也有将帅豪杰的故事,忠奸、美丑、善恶很是分明。
年画,一年年换些新的,屋里也常常是新的。
画下还有两个相框,多是老照片,有父母抱着五姐的合影,有姥姥、姥爷的合影,有石家庄的二舅一家的全家福……渐渐的,多了姐姐们的一些新照片,先是单身照或与朋友的合影,随后就是与爱人的结婚照,又不断添加了一些小宝宝的照片……相框后来实在摆不下了,也无人整理,一些照片索性被直接贴到墙上。
没通电前,大多是点煤油灯。那时觉得黑夜很黑,只有煤油灯是亮的。
灯光洒满房间,昏黄暗淡。有时炕上放个小桌子,母亲在桌旁做针线,姐姐在灯下写作业。有时,一盏灯下,一家人说笑着一起择花椒。为了比谁择得多,父亲还会用秤去称。
大约80年代中期,村里通了电,屋里有了电灯,我们感受到了从来没有感到过的通明。但屋外的夜大多时候还是黑的。黑的夜,我们就站在院里看天上的繁星,去找北斗七星,去识各种星星。皓月当空时,就看天,看地,看远山与树影。
二
我老家的大门,最早开在正南方向。门是哨门,其实就是用山上的皂角编织的大门,虽说皂角带刺,但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那时,村里的门或许就是个形式,是开,是关,是锁,也预示着此户人家某种状态。
出门向西,要走一条长长的胡同方能到街道。儿时,我觉得这个胡同很有趣。特别是夏日,胡同里很凉快,我和母亲经常在这里乘凉。
有一次,我在胡同里发现一条蛇,去邻居玉兰大嫂家,告诉她:“大宝(嫂),大宝(嫂),我家胡同发现一条大长弓(虫)。”我对此深有印象,主要还是因为玉兰大嫂后来的学舌。那时,我说话吐字不清,常常造成一种喜剧效果,大家也打趣着学我说话。
我刚上学时,村里有一家建起个小门楼,虽不大,但别致。我正想着我家什么时候也建起这样一个门楼,没多久,父亲就找人帮着改了我家大门。胡同没有全拆掉,在胡同之上加了顶,建了一个狭长的平房。大门直接从西南而出,建起一个尖顶盖瓦小门楼,门是木门。
这样的大门,村里并不太多,我很是欢喜,常常在门里门外玩耍。
父亲在七八里外的供销社上班,有时会回家种地,既有着扎根土地的坚守,又有着见过世面的开阔。
差不多隔段时间,父亲就回趟家。每次回家来,父亲便拿起扫把,门里门外打扫一通。那时只知父亲爱干净,此时想来,父亲打扫庭院渐成习惯,更是一种长久的情感。父亲有时打扫着庭院,还不断嘱咐着刚上班的姐姐,让她们干什么吆喝什么,要勤快、踏实、谦虚、好学。
我家的小门楼好像并没保持太久,父亲便把它拆掉了,门开得更大了些,用青砖建了两个简单的门垛,安了两个大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