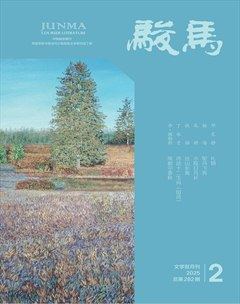这两年,每一次返京,都是爸爸送我。
我穿好鞋,在拉上羽绒服拉链前,张开双臂,转身,对妈妈说,来,抱抱。她会说,哎呀,我的大儿子又要走了……
这种袒露心扉,有别于中国传统含蓄表达亲情的方式,换在以前根本无法想象,却在最近几次离家前频频发生,而且我觉得妈妈似乎也越来越习惯了。
之后,我迈出家门,回头,一边招手,一边说,关门吧,妈,再见……别冻着,快关门吧……
告别的话总是简单的那几句,却反反复复地说了又说,直到正对着家门口的电梯门,像是一枚在静到极致的环境里掉在地上的一根针,“叮”的一声关上。
至此,对于我而言,一年一度的年,便也就过完了。
年岁渐长,现在愈发感慨,过年、过年,过的并非是年本身,而是妈,是爸,是团圆。
我拉着行李箱,背着双肩包,爸爸通常走在我的右边,父子俩步行去往不远处的公交车站等车来。
每当此时,他大都会点上一根烟,而我则坐在站牌旁的金属凳上,眼睛落在前面的一栋楼上,记忆自然涌现出它二三十年前的旧样子。
这栋七层高的楼房,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七截楼。
它是故乡赤峰火车站前的一幢旅店,在过去,是小城为数不多的高建筑之一。如今,它的主体依然被私人承包用来开旅馆,而一层几处小门脸儿的经营范围却在几十年里换了又换。你所能想到的一切适合开在火车站附近的快餐店、面馆、网吧、小超市、快递驿站……都曾被涉猎。
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我考上大学的那年,突然冒出了一家人气爆棚的小饭馆,而且名字还相当亲切、易记——崔师傅。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儿康师傅方便面的意思!
每逢寒暑假,我们考出家乡的这帮学子回来,今天他请客,明天她做东的,大都将聚餐的地点定在这儿。彼此都是穷学生,兜里没有什么钱,但“崔师傅”家的菜,着实是既便宜又好吃!我们当然常点家乡菜的老三样——锅包肉、对夹与铜火锅。
给你隆重地介绍一下,锅包肉可是东北咸口的;对夹呢,必须是独一无二的正宗赤(此处“赤”我们赤峰人都念三声)峰对夹;还有那大肚子形状的烧炭铜火锅,偶有碳星飘出,宴席即便将尽,热锅仍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儿。在我眼里,在北方,冬日围炉所围绕着的,就该是家家户户的这个铜火锅。
详细说来,锅包肉是炸得外焦里嫩的猪里脊肉,出锅前再大火爆炒一通,淋上一碗用蒜瓣儿、香醋与酱油调得恰到好处的汤汁,最后撒上一把香菜叶,那味道,真是香鲜无比!赤峰对夹,则是将烙得一层层脆得掉渣、宛若千层饼的馕,中间夹上肥瘦相间的肘子肉,咬上一口,唇齿留油。至于火锅嘛,可千万别想成是用来涮的!而是烧起炭火,锅圈儿内井然有序地码好酸菜、粉条、冻豆腐、丸子、扣肉、蘑菇、鸡腿……加好高汤,盖上锅盖,在锅中间的“大肚子”里点起炭火,待碳球一个个烧得通红,从烟囱口偶尔蹦出“噼噼啪啪”的两三个火星,锅盖儿缝四周开始冒出热气腾腾的香味儿,然后小心翼翼地一揭,那叫一个齐活——真可谓啥菜都有!
铜火锅热乎、齐全,代表喜庆与团圆。不但在饭店,在家里,每年除夕,它都是爸爸必做的一道年夜饭。
除了七截楼,马路对面,紧挨着火车站西侧,还有一家名为“光明旅社”的宾馆。迄今为止,我还未曾踏入过旅馆大门半步。
旅馆,让前来小城出差、游玩的旅客歇脚再适合不过。而我在站前出生、长大,我有家,我只回家住。
我与父亲等待的那辆公交车为K98路,首发站还是在我们家曾经居住过的工务小区附近,开到这里是第二站,也就是赤峰南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