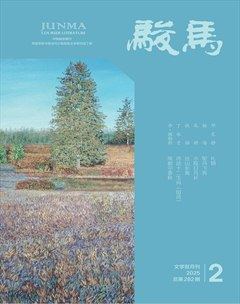瑞雪盈门,鞭炮声催。如期而至的中国年,似祥云,如淡烟,轻轻地飘进了人们心里;似甘醇,如歌声,伴随着醉人的旋律,把幸福载给劳顿一年的人们。红彤彤的灯笼挂满吉祥,白皑皑的冰雪映照璀璨,轰隆隆的鞭炮声传递喜庆……大江南北,黄河内外,华夏民族的各种年味,又一次带着传统年文化,与华夏儿女相偎相拥。
中国年的形成,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载:“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称为新年。……士大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家家饮宴,笑语喧哗。”这是古代民间过年的情景。而当时朝廷上还有圣驾坐大庆殿,百官齐集入宫,随班入贺的“朝会”,可谓歌舞升平,热闹非凡,这样的盛景也是最早的团拜活动。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为盛大隆重的传统节日,是一个象征希望、充满喜庆的节日,同时也是亲朋好友共聚、尽兴贺岁的良辰吉时。王安石在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元日》中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岁,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形象地再现了民间过年万象更新的景象。宋代著名诗人陆游,有一首诗《除夜雪》:“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通过这两首七言绝句,不难看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过春节的氛围非常喜庆祥和,年味是相当浓郁的。可以说,中国的年俗文化源远流长,南北迥异,各具特色。新春贺岁基本围绕祭祝祈年,以除旧布新、迎禧接福、拜神祭祖、庆贺新年等活动形式展开,内容丰富多彩,热闹喜庆,年味浓郁,凝聚着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精华。中国的年俗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喜庆,解不尽的风情。年俗里饱含着人们对吉祥如意的向往,对和谐美满的渴望,对至善至美的追求。无论习俗和传统如何随时代变迁,年,始终是让中国人最眷恋的味道。
小时候,我和弟弟妹妹都非常盼望着过年。那时家住辽西农村,每年一进腊月,我们就掰着手指头算着日子盼过年,盼望着能吃一顿饺子,盘算着父母能给买多少鞭炮,总觉得年前的几天过得太慢。大人们紧张而有序地准备着过年吃的和用的东西。杀猪,炸点心,蒸年糕,蒸馒头,蒸豆包,包饺子……样样准备充分,恨不得把一年的积蓄都拿出,用来过年。到了年底,年味也越来越浓了,大人们有些忙不过来,我们小孩子就给大人们当帮手,热火朝天地忙碌着,一点都不觉得累。腊八节刚过,父亲就把大黄米用水淘洗干净,捞出在盖帘上晾晒。几天后,又把半干的大黄米装进布袋子里,用自行车后架驮着来到村边的石碾坊。这是一个几乎全村人都使用过的多年的老碾坊,三面有墙,有房顶,上面长满了高高的茅草。破旧的碾坊里面有些阴冷,空气中飘散着一股粮米的馨香。靠西墙根停放着一口空棺材,那是碾坊的主人给家里八十多岁的老人准备的,停放了多年,已经落满灰尘,因为老人一直健在,所以这口紫红色的棺材成了摆设,晚上冷风吹拂,感觉有些瘆人,这也是我不敢独自来这里的原因。大人在还好些,如果晚上自己一个人,北风一刮起来,那树梢和房顶茅草发出的呜呜声,笼罩着眼前的景象,让我感觉有些压抑,甚至非常害怕。为了节省体力,父亲不知从哪里借来一头毛驴,用一块布把它的眼睛蒙严实,在脖颈处给它套上夹板,两面绳套牢牢拴系在推碾子的木杠上,这头毛驴就不知疲倦默默地开始了拉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