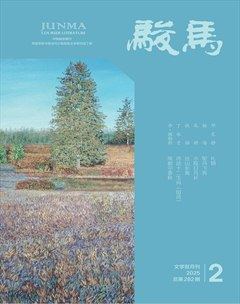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李白《夜泊牛渚怀古》
夏天的夜色浓重,仿佛舞动的乌黑面纱,罩住群山与林海,那云间偶尔闪出的点点星河,犹似隐隐约约的画布,勾勒多少有些不真实的存在。我走出林业局大院,沿着大街东行,1号楼下的民康大药房,6号楼下的回民肉店,街北的森茂广场上有广场大妈的喧闹,库都尔镇政府的办公楼隐入夜色,对面的金山家电商店的女主人正要关门落锁。又走了几步,我看到一栋砖瓦平房,屋顶沿街向北砌出三角立面,三角立面上浮雕出一颗红五星,横书“刻字·修表”,标有“1981”的字样,此房沿街的墙壁包有横竖相间的木板,透露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气息。其西侧,是相同风格与装潢样式的平房,蒙汉文的“牙克石库都尔商业公司五交化商店”牌匾甚是醒目。用手机拍下这两个门店的门脸儿,微信发给妻子维娜,她回复说:“一点没变,仍在老地方,老模样。”
我继续东行,桔黄色的路灯稀疏起来。有流水潺潺,已踏上库都尔河桥。多少次,在妻子的描述中,库都尔河桥与日月晨昏一道出现,库都尔河的波涛声成为妻子维娜成长的音韵,成为她故乡的底色。我凝望桥下的滔滔河水,想象上世纪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的库都尔景象,那时当然不会有温馨佳园小区,也不会有街北的新映山红旅店,但我可以推测出,如今街北的中国信合库都尔信用分社的位置,应是库都尔人民银行,而街南中国邮政库都尔支局的信号塔周边,肯定是库都尔邮电局的旧址。板夹泥的土屋隐去,代之以砖瓦平房,再到如今的高楼林立,便是我妻子维娜成长于斯又迁离于斯的漫漫时光。
我走过了中国联通,在忠发五金建材商店旁,南折,进入一条小街,路灯愈发少了,没有行人。街东是几家俄式木刻楞房,那外墙已涂抹一层水泥,木制的窗板虽饱经沧桑,却仍不失俄罗斯制作工艺与风格。街西南是一个四层楼房,我判断是铁路部门的所在地。小街折向东面,一盏银色的节能灯指引着我来到火车站。火车站位于一个坡地上,十余级台阶,立于火车站检票口外,举目东北望,几排砖瓦平房若隐若现于夜色中。按我妻子维娜的告知和我1990年夏天的记忆,岳父岳母当年居住的商业分局宿舍房,就在那寂静的夜色深处。不多的几扇窗户中间闪烁着灯火,似乎是那飞逝岁月的某种注解。往事随风而逝,那几排房屋当年的邻居都被生活带走,那几扇仍有灯火的窗户无法判断还有多少人家在此居住,我只能在脑海想象妻子维娜诉说的景象:大雪漫天,她走向火车站,一片开阔地的尽头,灯火明亮处就是站台,火车已进站,远远地,可以在下车的人群中辨识出自海拉尔一中放假归来的二姐萨仁格日乐。两个人说说笑笑着,通过那片开阔地,走向温暖的家……
如今,我就立在火车站的站台上,默默注视着东北方的夜色与夜色中寥落的灯火,努力复活库都尔的往昔岁月与春秋演化。
一
1988年春,我与维娜结婚,见到了维娜的二舅杨屹立。他与我聊了很多我们共同的故乡达尔罕亲王旗(今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往事,如历代达尔罕亲王、孝庄太后、全旗疆域与48个苏木、嘎达梅林等许多只有那个时代的人知道的往事。二舅曾就读于巴彦塔拉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后随老师特木尔巴根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在乌兰浩特度过了红旗如海激情飞扬的革命岁月。1952年秋,他随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由乌兰浩特来到扎兰屯。1953年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决定,中长路牙克石林业所与牙克石采工公司合并,成立了库都尔森工局,二舅来到了库都尔。那是一个天空飞雨的日子,二舅走下火车,周围都是身背行李的林区开发者,有人在大喊,“卫生队的人,集合”,许多人装在网兜中的搪瓷脸盆撞在一起,“叮叮当当”的,声音清脆悦耳。又一声带有蒙古调的汉语传来,“自治区森工局来的同志,这边来”,二舅缘声而去,几个身披雨衣的人热情地迎住了他。说到这里,面对着许多参加我婚礼的亲戚们,二舅仿佛在重复他当年的感觉,“那个下雨后的时刻,站在库都尔的土地上,我知道,今后的生活与工作,都离不开这片林海茫茫山岭纵横的天地了”,事实果真如此。
而且,何止是二舅安家于此,在他的带动与劝说下,我的岳父岳母,我妻子维娜的二姨杨金花、三姨杨淑兰以及后来随她们而来的小舅杨青龙也来到了库都尔,加入了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时代洪流中。后来,二姨调往鄂温克伊敏森工局,三姨调往工作的乌尔其汉林场升格为林业局,小舅杨青龙也调往鄂温克旗工作。
二舅在1953年当年就建起了库都尔林业局兽医站,是兽医站第一任站长,其工作受到林业局书记额木格图、组织部部长张恒泰、宣传部部长宝音何什格的多次肯定。二舅回忆道,1953年的时候,大兴安岭林区只有阿尔山、博克图、库都尔三个林务局与一个巴彦贮木场。那时山上作业场地称“采伐号”,仅靠有经验的现场踏查估测采伐出材量。采伐方式很粗放,为径级择伐,既无伐区调查设计,更无伐区验收管理。随着图里河、伊图里河、根河相继成立森工局,大兴安岭林区开始推行调查图面资料,选定年度采伐作业伐区,采伐许可证管理等工作流程,林区开发建设也从1950年代的手工采伐作业,逐步发展为机械作业。二舅动情地说:“采伐、集材、运材、检尺、造材、装车,说的是一道道工序,却凝聚着林区开发建设者的生命与希望,那一个个贮木场,那一条条运输的线路,那一辆辆奔波于运材路上的汽车,那一列列昼夜轰鸣的火车,都闪烁着林区开发建设者的青春光芒。冰峰雪岭间,‘爬山虎’拖拉机的纵横驰骋,木材自山岭间呼啸滑行,伴随的,都是林区人奔向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艰辛劳作。”落叶松遮天蔽日的壮丽山河渐行渐远,二舅的两个女儿明玉、梅花如今在鄂温克旗工作生活,儿子特木其勒留在了林区,二舅那一代人渐行渐远,那一代人创造的生活渐行渐远,那一代人守望着彼此成为我们记忆中无法抹去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