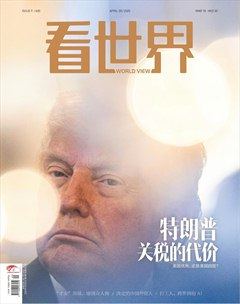六年级的课堂上,同桌拿圆规扎向张素的手臂,留下一个小坑。没有出血,但痛感真实。有一次放学,她被反锁在漆黑教室里半个小时,叫喊无人应答。12岁的她,以为男孩们是在“玩闹”,将遭遇埋在心里。
她进入市重点后,成绩位于班级中上游。而不错的成绩未能阻止欺凌的到来。
她觉得同学们故意忽略她,“基本上一个人坐在那一天没有一个人找我说话”。课堂上没人愿意和她组队完成任务,还有人对她投来意味深长的眼神,或几个人聚在一起,用她能听见的声音骂她。这样的经历,让她变得不知道怎么求助,甚至认为老师都不值得信任。
这样的“校园欺凌”,因隐蔽性强、难以取证等原因,长期被忽视,难以被发现,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欺凌行为无法得到及时干预,欺凌者也不会受到“惩罚”,如此共同构成治理“壁垒”。
近几年,多地试图以刚性政策扭转颓势。比如,今年3月,四川省德阳市推出一项中考招生新政,将校园欺凌纳入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学生一旦认定为“校园欺凌”,便无缘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德阳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该措施旨在让“学校深化学生的教育,引导学生遵纪守法,遵守行为底线”,并表示,欺凌认定和处理有一套复杂程序,遵守国家规范,具体不方便透露。
新政的出台,引来不少网友拍手叫好,“建议全国推广”。也有人提出疑问,担心“治标不治本”。争议背后,是校园欺凌事件频发,但在认定和处理等方面存在困难的现实。
当校园欺凌与升学机制直接挂钩,又能否真正触及校园暴力的核心症结?
求助无门
沉默,是张素遭受“欺凌”后的默认动作。
最初,她不知何为“欺凌”。到了初中,她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受到了“校园欺凌”,难过涌上心头。那种“类似抑郁的感觉”持续打击着她。
遭受欺凌后,她更习惯“接受”自己被欺负的处境,并从自己身上寻找“问题”,强化自身遭受欺凌的“合理性”。
六年级的寒假,张素“反思”认为“自己太懦弱”。高中阶段,她仍执着于找到自身的不足,如成绩不够优秀,容貌焦虑、说话口无遮拦,浑身充满负能量。这些想法阻断了她的行动。
校园欺凌中,这样的沉默并非特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课题组在2020年至2022年针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进行调研,结果显示,53.5%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面对校园欺凌,20.3%的学生要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才会向老师、校领导或家长报告。
但张素不是没有想过向老师求助。班里也有男生曾遭受欺凌。张素记得,男生将遭遇告诉老师后,反而遭到更严重的报复。她不清楚前因后果,但她认为,老师是不可信任的。
被孤立后,她成绩跌至班级倒数。连续迟到被批评后,她越发觉得自己这样的“弱势”学生不受教师喜爱。她认定“老师没有办法提供帮助”。
这不是张素独有的想法。友乐青春团队主理人钟馨乐在校园进行防欺凌科普时,总有学生反问:告诉老师有什么用?
学生不信任老师,认为求助后会被指责“敏感”,将其反馈的问题视为“人际摩擦”或“玩笑”。也有被欺凌者向老师报告后,处境变得更糟。
对成人系统的不信任,加固着沉默。有时候,教师们确实无力改变学生的处境。
山东师范大学校园欺凌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张文新在2018年进行了一次为期三年的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