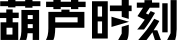卿云烂兮
糺缦缦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卿云歌
晋静公
我的父君死去了,我成了晋国的新君主。可是我这个君主仅仅是我父君的继承者。那么我继承了什么?他既没有给我留下财富,也没有给我留下土地,我所继承的,仅仅是捕捉到的他的最后的目光。即使是他的目光也是晦暗的。我从这目光中取出了幽暗的微光,将他晦暗的部分归还了晦暗。
我所继承的不仅是国君的名号,我还继承了虚无和仇怨。我不仅继承了我的父君的爵位,还继承了他的悲凉和苍茫。他给我起了一个悲伤的名字,我只有在酒中沉湎。在漫长的夜晚里,我的仆人点燃了黄豆一样的灯苗,我就在这灯苗的辉映下看着空空的墙壁。我的黑影在墙壁上孤独地停留,它被放大,它让我的面前更加幽暗。它就是我,就是我的悲伤和沉默,就是我的苦痛和无声的呼喊。
这呼喊没有人可以听见,只有我自己倾听着它。我看着它,只有一片黑暗,其中却藏有无数秘密。是的,这秘密我也不知道,别人也不会知道。它不仅是我的肉身的投射,也是我心灵的投射。我已经将自己的一切都放在了这个黑影上,一个模糊的、毫无细节的黑影,一个暗淡的、空洞的黑影。我举起了双臂,看见一株光秃秃的枯树,没有枝叶的枯树,它在我的面前晃动。它既是我的影子,也是我的绝望。它里面包含了我的心灵和目光,包含着我的寂寞和忧伤,也包含了我的呼吸、我的面容上的褶皱和充满仇恨的每一根发丝。
我没有光亮,所有的光亮都在我的外面。没有我的黑暗,这光亮还有什么意义?没有我的悲伤,别人的快乐又在哪里?我的黑影就放在了这墙壁上,这是我的最后的土地,最后的财产,最后的门。我不知道这墙壁的后面还有什么,只知道后面是无边的暗夜。
我乃是这通往暗夜的门,我将从这门中走出去。暗夜有着所有的事情,后面的灯光将会被彻底抛弃,或者它将永远抛弃我。它抛弃的不仅是我,不仅是我的名号,也不仅是我的肉体和灵魂,还有我所携带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开始和结束,一段我看见的和看不见的时光。
天下已经大乱,诸侯已经不是原来的诸侯,国家也不是原来的国家了。晋国不是原来的晋国,它已经是三个国家了。他们不断征伐,相互厮杀。它们不仅向着外面厮杀,自己也在厮杀。厮杀成了天下的景观,成为厮杀者的快乐。若是没有厮杀,这人间该有多么寂寞。就像我现在这样寂寞,就像我现在这样绝望。人间乃是用血来描画的,每一个人都在血中描画自己,也描画别人。血在燃烧,血在飞扬,血在喷涌。
唯有我是这血的观赏者,因为我也曾经在血中。我是这血的光焰里的幸存者。我的影子不是灯光投射的,而是地上的血将我的影子映照在墙壁上。因而我面前的门也是血的门。我将从这血的门中穿越,我将从这血中走入暗夜。我将在这暗夜里踩着血走向更深的暗夜。韩赵魏三国讨伐齐国到了桑丘,韩赵魏讨伐齐国到了灵丘。齐国也已经不是原来的齐国了,它已经是田氏的齐国了,田和也被天子册封为诸侯了,齐康公以及原来的王族被驱逐到海边,住在山洞里,只能依靠渔猎为生。他们煮鱼没有了鼎,只能用钭来替代,最后也一个个死去了。他们面对大海而死,只有汹涌的海涛伴随他们的死。他们的灵魂只能在大海上漂流,在波浪中起伏,在鱼鳖的背上栖息。
晋国的邻邦秦国也好不到哪里去。秦惠公死后,他的两岁的儿子即位,他的母亲成为这个国君朝政的执掌者。她所任用的都是宦官和外戚。为了收买众臣,只有不断赏赐,并加重了税赋,引发了民众的怨恨。在魏国寄居的秦国公子赵连回到了秦国,夺取了君主之位,杀掉了秦出公和他的母亲。秦国已经和魏国不断冲突,杀声四起,天下还有哪里是安宁的?即使是中原的诸侯们,也都蠢蠢欲动,不断彼此征讨和杀戮。天下还有哪里是安宁的?在一个不安宁的人间,我还会安宁吗?
不,我对安宁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期待。我只是希望我在这不安宁中望着不安宁的人间。我的父君曾对我说,一切都在观看之中。看是唯一活下去的理由。若是连看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人间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的父君带着我们不断迁移,在屯留停下来驻扎。但没有多久就被赵国攻打,我们还有什么力量抵御别人的攻打呢?只有遵从攻打者的命令,又迁移到了端氏。这是一个好地方,只有很少的人家,北面是低矮的山丘,南面乃是河谷和平地。由西而东的河流,缓缓流过,两岸是高大的树林,雾气在林梢飘动。
就在我们居住在这里的时候,也将宗庙迁到了高都。本来我们已经适应了这样既不是君主,又不是臣子的身份,也适应了山林间的日子,但即使这样的生活也维持不了多久。我的父君一开始是焦躁不安,渐渐地他安静下来了。这里的四季都是美好的,春天的时候,地气上升,整个地上就像着了火一样,遍地都是烟雾,这样的场景简直是太壮观了。我坐在田边,看着这一片苍茫的景象,既感到地上的生气,又感到眼前的梦境般的迷离恍惚,让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
我也陪伴着父君在河边垂钓,有时一整天都钓不到什么,但我们还是快乐的,因为这眼前的流水让我们忘掉了从前颠沛流离的日子。我们的面影在河水中飘摇,我们好像自己也在这流动之中。难道我们不是在流水中漂动吗?我们乃是这河水里的鱼,已经被别人的钓钩勾住了嘴唇,我们已经逃不脱了。他们就要将我们放入身边的鱼篓,然后投入烈火中烧烤。但我也看见那钓鱼者已经被烈火点燃了衣襟,这烈火也将会将他吞噬。
我的父君在这里享受了几年的好时光,他与我在林间漫步,在河边垂钓,在山间狩猎。我能够听见他的笑声了,但我还是听出这笑声中含有的苦涩。他还是在病苦中死去了。他说,我很想多看一眼这人间,因为你这一刻看见的不是前一刻看见的,你以后看见的也不是现在看见的。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最想看见的就是仇人的死去。
我草草掩埋了他,他已经无法得到诸侯的哀荣了。我只能将他身上的黄土堆得高一点,因为黄土是取之不尽的。我继承了国君的尊位,却没有什么尊荣,也没有什么国家的朝政,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到高都的宗庙奉祀先祖。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才可以和先祖说几句话,将我内心的烦闷和痛苦予以倾诉。更多的时候,只有和上天倾诉了。可是我不知道上天能不能听见我的祈祷。它若是听不见,我为什么还要向它祈祷?它若是听见了,为什么总是无动于衷?它看不见天下的混乱和不义吗?
可是没有过了多久,韩国和赵国就派使臣前来,告诉我,他们不再承认我以后还是晋国的君主,他们终于废黜了我的君位。魏武侯、韩哀侯和赵敬侯,把我仅剩的土地也分完了。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庶人,一个失去了国君身份的人,一个失去了所有土地的人。他们再也不允许我前往高都祭祀我的宗庙,我只能在端氏遥望我的先祖们。
他们的面目乃是一点点显露的。在先君晋幽公的时候,不得不反过来朝拜韩赵魏三家,臣子与主人已经颠倒了位置,只剩下了绛都和曲沃,其他的土地和城邑已经被他们分掉了。先君晋烈公的时候,只能为韩赵魏三家奔走,并朝见天子,让周天子册封三家的主人为诸侯。他们已经有了诸侯的名分,有了自己的国家,但在名分上仍然被晋国国君的阴影所笼罩。到了我的父君即位之后,不但失去了土地、财富和都城,连最后仅剩的国君名分也岌岌可危了。到了我即位之后不久,他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废黜了我的爵位和名分。他们以为,只有这样,他们的头顶就没有影子了。
可是,我还活着。他们虽然将我迁为庶人,但我仍然活着。只要我活着,即使他们不承认我,我仍然活着。我的活着也将让他们不安,因为他们的头顶上似乎失去了暗影,但无形的暗影仍然在它们的头顶上徘徊。我的影子已经不在他们的身上了,但我的影子还在他们的内心。我仍然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暗影,因为那暗影里有我的目光,有我的先祖的目光,有我的一个个先君的目光,也有他们的先祖的目光,有一个个曾为我的先君的臣子的无数死去的他们先祖的目光,有着无数死去了的灵魂的目光,也有着无数晋国民众的目光。在这么多的目光的审视中,他们的心能够安宁吗?
我注视着他们。我不仅在白天注视他们,也在暗夜的星辰下注视着他们。我不仅注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还注视着他们梦中的一切。我想,他们即使是在梦中也不是安宁的。他们会在梦中看见我,看见我的先祖,也看见他们的先祖。那么,面对那么多人的目光,他们能说什么呢?他们还是抬不起头来。因为他们可以掩盖一切,可以做一切违背天道的事情,却在梦中不能遮掩自己的本相。
在梦中,他们原本是牛马的,还是牛马,原本是野兽的,还是野兽,原本是虫子的,还是地上爬行的、在地穴中栖身的虫子。他们醒来的时候,似乎坐在了高高的座位上,但他们在睡梦中,又回到了自己的洞穴。那么,他们能不为这梦中的景象而感到恐惧吗?难道不为这梦中的景象而感到卑微吗?难道不为自己的卑劣而痛苦吗?是的,他们必定害怕我。不是仅仅害怕我,而是害怕我身上所放射出来的幽暗的光。因为我的幽光将刺穿他们虚假的面孔,刺穿他们卑弱的灵魂。我的利箭将从这贫瘠的地上射向他们,他们又怎能不感到这疼痛?他们想飞到天上,但我的箭射断了他们的翅膀,他们将掉落在污泥里。
我的名字是倶酒,我的父君已经给我斟满了酒。我就饮着美酒等待吧,实际上我在等待中看见了他们。几年过去了,他们一个个死去。赵敬侯死了,接着韩哀侯死了,又接着魏武侯也死了。他们都不会长久。他们得到的,将留在人世间,而他们将在死亡中失去所有的东西。赵敬侯是赵烈侯赵籍的儿子,他的父亲死了,他也死了。又接着,继位的赵成侯也死了。韩哀侯是韩文侯的儿子,他的父亲死了,他也死了。魏武侯是魏文侯的儿子,他的父亲死了,他也死了。我饮着美酒,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他们废黜了我的国君之位,他们一个个死了,我还活着,因为我还在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
我的酒樽里飘满了死者的影子,我一边饮酒,一边嘲笑着他们。我经常在梦中痛斥他们的亡灵,以至于他们再也不敢在我的梦中出现。我似乎变得快乐了,因为我已经看见了仇人们一个个死去。我想起了复仇者豫让。他是愚蠢的,他的复仇也是愚蠢的。所有的复仇需要等待,但他不愿意等待。若是在等待中看见了仇人的覆灭,就意味着上天已经替你复仇。豫让的复仇不仅是徒劳的,也是愚蠢的。
因为他乃是为了主人而复仇,为了主人曾经给过他的恩赐而复仇,却不是为了真正的仁义而复仇。因为智伯也不是仁义的,他乃是为了一个不仁者而向着另一个不仁者复仇,他怎么能得到仁义呢?他们都不是好人,你为一个坏人复仇,却得到了另一个坏人的宽恕,这样的复仇有什么意义?你乃是为了自己凉了的饭肴而复仇,这不过是对从前的不仁者的一次祭祀,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他的仁义不在他的心中,而在他失去了的饭肴里,这不过是为了曾喂养自己的主人显示忠诚而已,怎能谈得上仁义呢?他哪里知道,仁义从来不是喂养出来的,因而从复仇中得不到它。
我不需要复仇,因为这复仇已经在我的等待中。我也不需要别人为我复仇,因为别人的复仇将夺走我的仁义。我的仇恨既不在过去,也不在现在,而是在虚无的时光里。我的仇恨一旦被虚无的时光接收,它就转变为我感受不到的虚无。既然这仇恨也变得虚无,我又怎么愿意在无数的死尸上再堆放另一具死尸呢?因为死尸已经够多了,血已经足够淹没人间。没有仇恨,怎能有爱和光明?没有白天,又怎能有夜晚?没有春天,又怎会有秋天?是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伴而生,我又怎能将其中的一样单独取出来,放在这浑浊的人间?让我的仇人自己爬到这死尸中去吧,我只是看着他们从那里爬上去,又被另一具死尸压在下面。我还要看着蚂蚁怎样一点点用小小的螯子割下他们的肉,又放入它们幽深的地穴里。
老仆人
端氏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这里有着群山和河流,有着平川和好田地。我侍奉我的国君,和他朝夕相伴。我看见他总是忧心忡忡,他的脸上从来没有笑容。他的眉头紧紧皱着,以至于在眉宇之间有了两道深深的刻痕。那两道刻痕里,已经将自己所有的悲苦刻在了其中,它就像深深的沟壑,深邃的沟壑里有着奔腾的激流。实际上,韩赵魏三家已经不再承认他是国君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一个庶民,但在我的眼里,他永远是我的国君。这晋国乃是周天子封给他的先祖唐叔虞的,乃是他的先祖一代又一代继承的。可是他失去了晋国,失去了一切,六百多年的晋国,从他的手里失去了。他的手不够大,攥不住这庞大的晋国了。他的手也不够有力,攥不住这国君的名分了。
他的衣裳上披满了风雨,披满了星辰、阳光和晦暗的浓云,只有闪电和雷鸣在上面交织,我似乎从他的衣裳上看见一阵阵闪电一样的仇恨和雷鸣般的忧愁。在春天的时候,我陪着他到野外踏青,他会突然萌发孩子一样的好奇,他用手刨开土地,看看土地里埋藏的草根。他说,你看,它们开始发芽了。他看着地上刚刚露出来的草叶,他说,这多么好,我不知道它们是怎样用这么柔软的叶子顶破坚硬的土层的。柔软的力量要比坚硬的力量更强。
在农夫开始耕耘和播种的时候,他会默默地坐在地上,看着农夫播种的背影。他说,这是一年中真正的开始,岁月是从播种开始的,但所有的事物都在等待收割。我的土地上长出了太多的杂草,我的谷苗早早就被毁坏了。只有秋风能让野草干枯,然后严冬的冰雪将覆盖它们。我的田地里已经没有收成了,我的粮囤里也没有多少存粮。他羡慕地看着农夫沿着田垄走着,他又说,我不是一个好农夫。
夏天的时候,我陪着他在大树下乘凉。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看见他们,现在他们一个个死去了,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我所看的都没有了,剩下的时光我该看什么?向上的路就是向下的路,我已经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