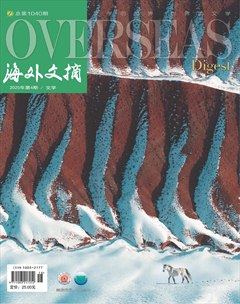1
中国历史上不乏著名的隐士,像竹林七贤、陶渊明、诸葛亮、孟浩然、王维等等,随便捋一捋就能毫不费力地列出一大串名单,稍微有点儿名气的文人学士或多或少都有远离尘嚣、寄情山水的情结,即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对隐居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赞美,形成中国特有的隐逸文化。
人,找个地方栖隐,就像鸟找个地方筑巢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但是,因为一些隐士的名气实在太大,他们自得其乐的蜗居之地即便再平常,也会被好事者阐释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诸葛亮的草庐,杜甫的草堂,早被风吹得不见一根草茎,不断有人复制出赝品,却成为无数游人向往、探究之所。
比较典型的是陶渊明,担任过不少基层职务,最后一次当官的职位是彭泽县令,仅仅当了八十多天,屁股焐了个半热,衙门里的公务员还没有混个脸熟,便弃职而去,自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桃花源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明知自己无法改变令人憎恶的现状,只能通过一番虚构来抒发情怀,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心仪的世外桃源。那种没有战争与剥削、丰衣足食、怡然自乐的“乌托邦”,不仅仅令士大夫神往,也迎合了广大底层人民的无限期望。
古人隐居的原因有很多种,有的是不愿在官场同流合污,有的是官场失利,有的是养精蓄锐,有的则把隐居当作一手好牌去打,借此抬高自身声望,在世人中形成影响,引起官府的关注。当假惺惺的隐居者遇到了虚伪的统治者,就不断上演一出出好戏。朝廷任用那些假意隐居的人,可以展现自己的胸怀,证明对人才的重视。唐朝的卢藏用,就是通过隐居取得了贤名,被唐中宗召入朝中做官,先后担任左拾遗、修文馆学士、工部侍郎等职。时人称卢藏用“随驾隐士”。中国人历来善于跟风,有许许多多的人效仿卢藏用,隐居在终南山,把自己的小诗工工整整地抄几首,请某位小吏喝喝酒,托他拿去京城上见皇帝,以此求得做官之路。大名鼎鼎的李白也在终南山玩过隐居的噱头,他心知肚明,按常规的科举路线参加考试,恐怕难以出头,所以剑走偏锋,最后皇帝还真请了他。仅凭“终南捷径”这个成语,终南山就足可以跻身中国隐士名山了。
那些名士选择隐居的地方,大多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用俗人的话说就是特别有灵气,而且常常出现名人扎堆隐居的现象。
素有“中国智慧化身”之称的诸葛亮,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山中做了十年的待业青年。以他的老谋深算,是没打算永久隐居的,他虽然过着躬耕苦读的生活,却“每晨夕从容,常抱膝长啸”。什么意思呢,每到凌晨和傍晚,他就坐在一块凸出的石头上,在空旷的山中朝天长啸,那是何等的不甘与自信?所以,他在隐居期间与友人交谈时常常自比管仲、乐毅。也就是说,他在隆中山隐居的十年里,虽然躺卧在草庐的木榻上,却从没有过彻底“躺平”的佛系心态,而是夜观天象,伺机出山。自然而然,他屁股坐过的那一大块石头被后人称为抱膝岩,旁边建了抱膝亭,他隐居的隆中已成为游人如织的5A 级景区。
颇有意味的是,在襄阳城东二十里也有一座文化名山,本名苏岭山。因为刘秀在重臣习郁的陪同下巡游至此,眯了一觉,梦见两只梅花鹿,命习郁立祠于山。有皇帝口谕,习郁当即以最快的速度动手建祠,并刻两只石鹿立在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遂以庙名山,苏岭山更多时候被叫作鹿门山。
习郁被封为襄阳侯,骨子里潜伏着的隐逸情结泛泡一样突突突地冒了出来,在襄阳城南十里的凤凰山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仿范蠡养鱼之法,掘水池,建园林。习郁后裔,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曾任荥阳太守,后因脚疾,解职返乡,隐居于此,唯大才不废,敕命编修国史。习凿齿是当时天花板级的大学问家,“锋辩天逸,笼罩当时”,著有《汉晋春秋》等。他的挚友是另一个天花板级的人物,即佛教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代宗师释道安。当时,习凿齿邀请释道安到襄阳弘法。释道安师徒一行四百余人被安置在习家池相邻的白马寺。释道安抵达襄阳,习凿齿见面后即言:“四海习凿齿。”释道安应声答曰:“弥天释道安。”两人隐居在凤凰山,常常通宵达旦促膝长谈。释道安在襄阳十五年,是他一生中从事佛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利用生活上的相对安定,整理佛典,阐发佛理,制定佛规,统一佛姓,是中国佛教史上订立寺院规则的第一人,使佛教徒以“释”为姓永成定式至今不变。苻丕攻下襄阳,将释道安与习凿齿一起“送”往长安。苻坚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人可以送走,习家池却搬不走,自汉晋以来一直是宴游名园,孟浩然、李白、杜甫、皮日休、欧阳修、贾岛等均临池赋诗。习家池距今已近两千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园林,被誉为“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
再回头说说鹿门山,先后有庞德公、孟浩然、皮日休等名士归隐。诸葛亮曾到鹿门山拜庞德公为师。当时荆州(即文学作品中常提及的“荆襄九郡”)的治所在襄阳,割据一方的大军阀荆州牧刘表数次邀请庞德公。庞德公压根不给他面子,携妻栖隐鹿门山,采药而终。庞德公是给人起外号的顶尖高手,他称诸葛亮为“卧龙”,其侄儿庞统为“凤雏”,司马徽为“水镜”,这些响当当的外号都盖过了当事人的本名,流传至今。庞德公老给别人起外号,自己总也得有一个,于是被后人送了一个“知人”,不够响亮,却是恰如其分的美誉。司马徽也是东汉末年著名的隐士,隐居在离襄阳不远的白马洞,拒绝了刘表的多次邀请,虽然后来迫不得已被曹操所得,却缄口不言,不久病死,才华始终未得施展。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创作田园诗的人物,算唐代田园诗的先行者,二十多岁已经诗名天下,却“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当时的襄州刺史韩朝宗,人称韩荆州,也是当世的一个笔杆子,搁在今天妥妥的一个省部级官员,一个玩票的文学爱好者,虽然文章写得一般般,却没有文人相轻见不得别人好的坏毛病,反而在任官时喜欢提拔后进,曾经推荐不少人到朝廷做了级别不低的官,在江湖上积得了好名声。李白曾经写过《与韩荆州书》,马屁拍得啪啪响:“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天真的李白拐弯抹角,低估了他人的智商,当别人是傻子,他识得韩荆州的目的,还不是想封万户侯,实现自己的“卿相梦”?这个韩荆州无论在官场,还是文坛,都是一个难得的热心肠,他推荐上瘾,执意要带孟浩然到京城去引荐给唐玄宗。到了约定出发的时间,却不见孟浩然的人影,就命人去叫孟浩然。差人提醒孟浩然:“君与韩公有期。”孟浩然斥曰:“业已饮,遑恤他。”一个白眼就把差人打发了。孟浩然比李白大十二岁,出名较早,加上他的诗确实写得好,人又豪爽,朋友圈里基本上都是当时一流的大诗人。相比自己眼巴巴地讨好韩荆州,李白自愧不如,所以写下《赠孟浩然》,对孟浩然骨子里超脱世俗、不慕荣华的隐逸人生观做了最好的阐释:“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这也印证了李白在他的代表作之一《将进酒》中所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