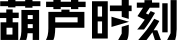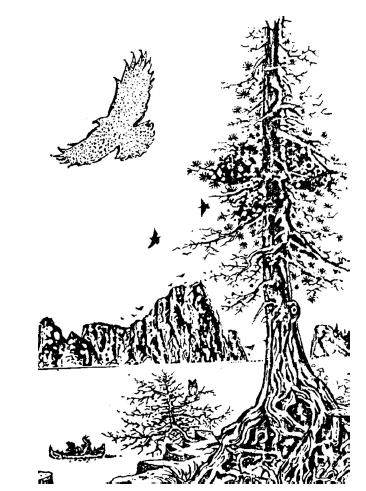
那个雪夜没有月亮,狂风在窗外嘶吼,卷着漫天飞雪,肆意拍打着被塑料布糊着的木窗。
我几回想出去上厕所,一推门见风大雪急,就忍了又忍。晚饭时父亲才到家,他从屋外进门时,顶着一身的雪,气呼呼地说:“这天要人命呢,真能冻死人!门口的鸡圈完了,让雪压塌了,估计鸡都冻死了!”一提到鸡,我和母亲偷偷相视一笑,还是母亲有远见啊,担心天冷鸡被冻死,前两天一口气都宰了,让我扔到屋顶冻着呢!
母亲见父亲回来,赶紧从厨房端出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鲤鱼。父亲好吃鱼,他也不挑鱼,只要新鲜就行。看见饭桌上有鱼有肉,他的酒虫子就钻出来了。他几杯下肚后,话匣子就打开了,那打鱼和伐木的故事就开始了。往往父亲讲到兴头时,母亲就泼上一盆冷水,好让父亲的话早点打住。那晚,母亲看父亲已经微醺兴奋了,就提醒说,快过年了,花钱地方多,最近牛羊价格太低,现在卖了赔钱,得另想点办法啊!父亲像是早有准备,爽快地说,早想好了,卖阵子煤挣点零花钱!母亲也同意,只是她劝父亲,卖煤时带上我,天冷路滑,万一遇上情况,我还能搭把手。父亲开始觉得我太小,最后看我也想去,勉强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天微微亮时,我听见父亲起床的声音。冬天起床比较费劲,睡觉时还有炉火,醒来时只剩火星,屋里凉飕飕的。父亲几乎不睡懒觉,无论春夏秋冬,母亲分析过原因,有烟虫子到点叫他起床呢。我观察了,还真是这样,父亲醒来时总会干咳两声,虽然他压着声怕吵醒我们,但是我睡觉轻还是会醒。他常常在昏暗中先坐一会,然后摸一摸棉衣兜里的烟在不在。只要确认烟在,起床就有劲头了。他穿好衣服,悄悄推开门,一股子寒气瞬间冲进屋里,冷得我赶紧掖了掖被子,随后,我就听见父亲在屋外毫不遮掩的咳嗽声。
父亲过完烟瘾,也不回屋,那时天还没亮透,他怕打扰我们。他一个人去厨房烧炭和开水,炭和开水是给车用的,这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发动机早都冻透了,不加点温根本启动不着。父亲把烧好的炭放在发动机下,再往水箱里倒满开水,大约半小时后,先试着摁电动马达,如果启动不了,他就喊母亲帮忙。母亲给我说过,她烦父亲喊她帮忙,因为父亲总说她跟不上趟。父亲拿出摇把子,撸起袖子使劲摇,然后指挥着母亲摁电马达。一看还是启动不着,父亲就气喘吁吁地埋怨母亲说,配合,配合!这个事得两个人配合起来,你看我摇得差不多了你得赶紧摁,不然我的劲就白费了。母亲本身也不太明白,被说得越来越紧张,绷着脸点头答应着,一句也不反驳,依然按照她的节奏摁马达。父亲有时实在受不了,就大声喊我过来帮忙,当然,我更紧张得一塌糊涂。看我过来了,母亲也不惯着父亲,甩了甩手说,我早说了我干不了,非让我干。
煤厂在加油站旁,离县城大路很近。煤厂老板和父亲之前都在渔场打鱼,多少有些交情,所以卖给父亲的煤价相对便宜。到煤厂时天刚微亮,父亲怕我冻着,不让我下车。于是,我蜷缩在车里望着父亲。父亲猫着腰爬上车斗先取铁锨,因为穿的皮袄厚,他往上爬时显得有点费劲。父亲的铁锨有点年头了,把是用白桦树做的,光溜溜的还有弹性,他中意这把铁锨,用了很多年舍不得换。父亲不紧不慢地一锨一锨往车上装煤,遇到大块煤,铁锨就铲不动了,他就弯腰抱到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