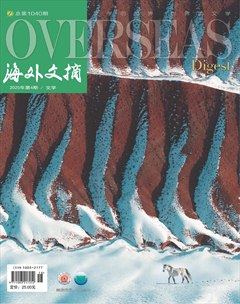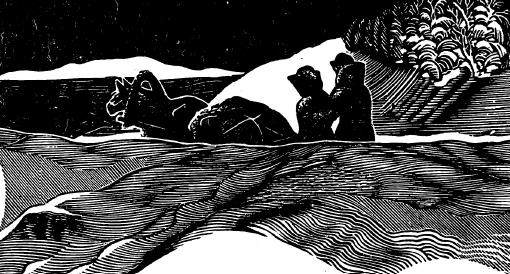
1
某年在江南遇见许多墓碑,它们卧在地上成为一条道路。那上面驻留的名讳和书法就像江南的花朵,有一片水土独有的气息。天南海北与古往今来中,会有很多人就在墓碑上走散了,就像一张张冰凉的票根,躺倒成失落的方向。这也没有太多悲伤可言,人们始终就在生死交替的路途。今天的脚步踩踏是过去的道路,过去的票根也可能是今世的证据。那些似乎还能听到呼吸的符号,让石头成为一种坚固的证据,生长成深藏悲欢离合的风景。
我们常常要去远方看风景。眼前与自己常常幻化成风景本身。没有人可以看清自己的肉身与心底。人们愿意奔赴远方,用物欲掺杂在光阴之中,去寻找见证自己正误与得失的风景。进入一处新的风景需要一道手续,这样你才有回头路可以走。验票的人把票根还给你,就是祝福人们顺利返程——所要抵达的地方其实只是你的出发之地。如果你愿意逃脱入口的检查,那么就可能找不到出口。就像一只鸟如果不衔着家乡的种子,它就会有不再能回家的险境。当然,不能回去的只是那或许怨恨了一生的故地,人也可以认贼作父地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发芽生长,把墓碑立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留下一张不再显示出任何依据的票根。
票根越来越多,积攒在家中的抽屉里。有时候需要和外人或者晚辈吹嘘一下过往曾经,它们可能成为一种提纲,也是一把带着密码的钥匙。那些印在票上面的风景依然在生长,虽然你的抽屉并没有提供阳光雨露。你不用担心被离开的风景会有忧伤或者险情,它们没有等待过你的到来,也不会对你记忆的抽屉有任何的期待。只有你自己,在意那些风景的票根,对自己讲完那些于外人并不重要的故事。
一起来去的还有那些没有登程就已问归期的车票。你一定是在出发之前对归程最有期待,却没有仔细问过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出发?从村口到城市的路口是那么遥远,人们义无反顾地离开,为的竟然仍是一个落叶归根的成语。因为他们知道,再遥远的地方,都无法安放自己思念故土的墓碑。千百年漫漶不清的墓志铭上,也一定刻着可能怨恨一生的籍贯。出生地才是那一张紧紧攥着的票根。人走得越远,就会把票根抓得更紧,让它变形在自己胆战心惊的手汗里,这样才能残余一些老家的温度。当你举目无亲或者身陷绝境时,一定想着把最后的一点财产和精力换一张回家的车票,回到那个你出发时就已经想好的目的地。
许多年后,再去看那些被印刷得方方正正的地名,是那般虚无与落寞。风景区的门票被打上了从此不再重逢的洞孔,证实着远方的陌生和失落——人和风景之间无非是一场冷漠的交易。车票上的箭头似乎有明确的方向,但被检票员撕掉附票之后,正票其实也是一场虚无。它们有些可能被归纳到单位永世不再见光的账册里,有些被遗忘在早就清洗干净的衣服里,蜷缩成一个带着岁月香味的谜团。
2
我总觉得自己对城市来说仍是外人。作为一个来自村庄的孩子,担心市井无以扎下我们野蛮的根。城里的生活充满各种缝隙。这就是市井的生机。偶见的野草都是长在水泥砖缝之中的。这显然不合乡下人如土地般的心意。但因为已经拿到进城的种种票证,我只有畏缩地伪装自己逃离的经历,用衣冠楚楚掩饰自己慌乱而潦草的过去。服饰也像是一种入场券,人们往往只看重外表的“尸皮”。以貌取人是市井生活的基本办法。
我喜欢往古旧的老街深处跑。我所在县城的老街有南北之分。北大街多是手工业者,南大街住的多是士绅。日后看来,子孙已经并没有什么区别,一切又都长成了黑白灰的色调和表情。古老的东西更有耐性,它们反而比新生的事物更牢靠而不易消失。这些是我在北门大街上周旋时,想到的一些道理。我那时候太喜欢去“三中队”了。三中队是个大杂院。院子里一切都是破旧的,包括从朽木窗户外面斜射进天井的阳光。
有力夫躺在门前板车上睡觉。板车倚着破旧的墙,象征了他们依靠着某种虚无。他们竟然一早就酣睡起来,呼噜声中有明确的酒味。可能他们睡着了,就与世界彼此少许多的尴尬。我以为他们在这种地方躲着,和我的逃避是一种共同的畏缩心理在作祟。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是这里的主人——他们的三中队竟有一个很文气的名字的:搬运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