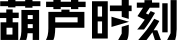一切未被说出来的,注定要消失。
——米沃什
报纸
熟悉她的人喜欢说,她被保护得太好了。当她还是个小女孩儿、生活在中国时,她的家人给予了她充分的保护。然后,她到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岛国新加坡,在青春时代初期,她完全沉浸在自己那个女学生的世界里。这并不是说她身边没有男性,而是这些人都被她以极其顽固的盾牌阻挡在亲密关系之外。二十六岁时,她突然改变心意,决定恋爱了。于是,她的一位好朋友成为她的男友,交往两年后就结婚了。看起来这好像是第一次恋爱就结婚的糊涂决定,但事实却证明她选择了一位理想的丈夫:他不仅对她忠心耿耿,还颇有照顾她的能力。婚后,她不再工作。她丈夫的事业也发展得不错。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住在靠近“海港城”的一栋高级公寓里。她偶尔出现在大学同学的聚会上,因为生活状态松弛而显得年轻些……所以,她的女友们(尤其那些情海浮沉、颇有心得的女友)喜欢说,她没有经历任何感情打击、没受过男人的伤害。
如此平安无事而又平淡无奇地,她度过了大半生。她四十多岁了。有一天,她在当地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文章谈论对女孩的早期性教育为何重要,缺失性教育的女孩在青春期、成年后容易遇到哪些问题……她平常不喜欢读关于教育孩子的文章,她的小儿子也已经初二了。但她把这篇文章来来回回读了三遍。她读得浑身莫名紧张,甚至背部都渗出汗来。它让她想起一些事情……房间里开着空调,她却把报纸折起来扇风。但过一会儿,她又把折起来的报纸展开,迫切地找到那篇短短的文章,盯住某一段看上半天。终于,她决定把那叠报纸扔进杂物篓里——那里堆放着她翻看过的杂志和过期报纸。她在沙发上呆坐了好一会儿,突然起身去抽屉里找纸和笔。最后,她从杂物筐里又找到那份报纸,从报纸里找到文章作者的名字、报社的读者来信专用邮箱,把这些信息都认真抄到纸上。
几天后,她从报社的编辑那里要到那篇短文作者的电子邮箱。作者是一位儿童心理医生。她想给他写一封信,并不是关于孩子,而是关于她自己。她记得,在“选择性遗忘”的理论中,人们会倾向于忘掉痛苦、耻辱、不愉快的回忆。但她不知道为什么,对于那两次可怕的遭遇始终记得那么清晰。而且,那种恶心污秽的感觉,也依然清晰、尖锐。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些,包括她最亲密的女友、她的姐姐、母亲,还有她丈夫。二十多年里,她一直守住这个污秽的秘密。当她准备把这些事讲述给一个陌生人时,她还能清晰地看到那两张面孔,一张东方的,一张西方的,一张麻木猥琐,一张怪异扭曲。那两张脸,就像她白日里的噩梦。
异物
那是大学的最后一年,她将满二十二岁,但还从未交过男朋友。如果她是个长得很不好看的女孩,在整个大学时期都没有交男朋友,可能会被人嘲笑,周围的同学会想当然地认为是无人肯选择她。但她并不难看,所以周围的人只是觉得她性格过分偏执、古怪。就她自己而言,她并非对男人有什么很高的、不切实际的标准,她还从未认真想过这些标准,因为她没有想要和男人在一起——那种亲密意义上的“在一起”(关于亲密关系,她想象力的限度就是拥抱接吻)。所以,直到那时,她从未和男人有身体上的亲密接触,甚至没有和亲属之外的男人拉过手。只有一次,她和几个同学一起去马来西亚旅游。一天傍晚,他们去马六甲附近的一个地方看萤火虫,那地方需坐上小木船悄悄驶进一条狭隘的河道,萤火虫们就住在小河道两旁的大树上。那是条很小的木船,停靠得不怎么稳。上船时,一个马来男孩在船上接应乘客。他必须拉住她的手,把她接上船,再扶她坐稳。当她的手被那陌生的、深肤色的年轻人握紧的时候,她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幸好是夜幕初降的时候,没有人看见她脸红发窘的样子。
她不是不和男生交往,相反,她还有几个很不错的男性朋友。只是,如果有熟悉的男孩试图碰一下她,那他肯定就上了她的黑名单,她就不再和他说话,甚至不再相见。惩罚的权力总是在她这一边。对她有好感的男生唯一能接近她的方式就是做她的朋友,而被她留下做朋友的都是些知书达理的好男人,也就是说,他们之中没有人会试图强行做她不喜欢的事。但这也使得她对男人的了解极为有限,也就是说,她不仅对男人的不同类别、不同危险程度缺乏了解,她对男人的身体更是一无所知。譬如,她知道男人身上长了个和女人不同的东西,这个东西会冲动、会侵犯女性、令她们怀孕,但她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它在受到刺激时会有怎样的变化,它会怎样侵入一个女人的身体、使她怀孕……她看过不少书,但那都是正正经经的书。她也看过不少电影,但都是正正经经的电影。所以,直到某个晚上,直到那件事发生之前,她对男人身上那个东西一无所知。
因为是大学最后一年,除了她那点儿奖学金外,她想多挣点儿钱,以便毕业后去一些地方旅游,不必急着找工作。所以,她接了两份家教课,其中一个学生的家教课时间是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学生家离她的大学宿舍坐公共汽车大约四十五分钟。
那个晚上如同岛上的任何一个夜晚,潮湿、溽热,几乎无风,空气里充满植物的气味,天空蓝得发黑,高大的棕榈树矗立道路两边,叶子低垂不动,像巨人的缕缕湿发。她那个初一的学生快要考试了,她主动给他多补了点儿内容,补习课结束得晚一些,她因此错过了平时乘坐的八点四十五左右那班公车。她要等的下一班车很久都没有来,几个和她一起在公交车站等车的人都陆续坐上别的车走了,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车站的空气里弥散着一股微微的焦味儿。她没有因为一个人在公交车站而害怕,因为这是个以安全著称的城市。
她等的那辆车终于来了,已经过了九点二十。出乎意料的是,车上乘客特别多,看起来是附近工厂区的夜班工人下班了。车上没有座位,站的空间也挤满了人。她上车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抓住扶手吊环的局促地方,站在那里。车子仿佛不堪重负,笨拙缓慢地启动了,车里热热闹闹,穿着制服的夜班工人用福建话、马来语彼此交谈。她有点儿沮丧地想,难道要站四十多分钟回家?
几分钟后,公车到了下一站。又上来几个人,其中一个微胖的男人,三十多岁的样子,面容疲倦,从人群中挤过来,最后站到了她旁边。过一会儿,她觉得这个人站得离她太近了,他的胳膊不时碰着她的胳膊,她能闻到他身上那种令人不悦的气味。她尽量不太明显地往旁边挪一挪,因为她不想显出嫌弃别人的样子。车子转弯,颠簸过后,他似乎又离她很近了。这一次,他没有站在她旁边,而是站到了她后面一点。她感到他的身体又时不时碰到她,她不喜欢这种接触,更不喜欢他身上的气味,但她想,也许是自己过于敏感了,毕竟公共汽车上太拥挤,某种肢体接触不可避免。她也没有多少空间可以挪动,所以,她忍受着这种不适。
可她逐渐感到哪里不正常,那似乎并非一般的身体接触引起的不适。她察觉到有什么硬物总碰到她的腰部和臀部之间的某个地方。她终于忍不住回头瞅了一眼,她看到那男人动了下他的背包,那背包就横在她和他之间。她稍稍松了口气,心想是他背包里装的什么硬物碰到她了,譬如一个眼镜盒、一个笔盒……有一会儿,那个东西不再碰她。可没过多久,她又感觉到了它,就在她右边臀部上面一点儿的地方。她想又是他的背包晃过来,里面的那个东西碰着她。她劝自己不要疑神疑鬼、胡乱猜疑别人,可那个东西越来越近,甚至紧贴住她。她又一次转身看,发现那人肩膀一歪,背包滑下来。“你的包一直碰到我。”她尽量礼貌地对他说。“对不起,人太多了。”那个人说,把包往胸前推推。她觉得他的表情有点儿怪,而且他脸上有很多汗。她感到哪里不太对,但又说不出究竟哪里不对。她只好再往坐着的乘客那儿挪一挪。
她还是隐隐感觉到,那个男人缠上了她,因为她往里稍稍移动一些,他过一会儿就会跟过来一些。她让自己尽量忽略这个讨厌的人。公车驶上一段坡道,转弯时颠簸得更厉害了。这时,她又感觉到那个东西在凑近她、碰触她。她无法消除那种直觉:那不像是什么包里的物件,而像是人身上的什么,它像个活物,有温度,但她确定它不是一只手,她不知道那会是什么,她找不到缘由,抓不住证据,也说不出抗议……那种不安、恶心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而且,她似乎在车的噪音中听到那个男人浊重的呼吸声。她猛地往旁边闪开一步,甚至碰到了坐在那儿的乘客的腿,然后,她看到那男人慌忙把背包一甩,挡在他俩之间。她现在可以确定了,刚才碰她的那个异物,并不在他的背包里,因为刚才背包并不在那儿。是他,或他身上的什么东西,在碰她。她突然有种晕车想吐的感觉,但她极力忍住了。她朝车门方向挤过去。车到下一站,她就赶紧冲下去。但下了车,她又是一阵剧烈的恐惧,怕那个男人会跟着她下车。如果他也下车,如果公车站没有别的人,她该怎么办?她又急忙朝车前门走去,决定只要看到那个人下车,她就赶紧从前门再次上车。但那个人没有下车。两个女工和一个男人下了车,然后车门迅速关上,车开走了……
刚下车的三个乘客走了。公车站有两个别的人在等别的车。她坐在最靠边的塑料椅子上,尽量把自己藏在阴影中。她现在约略猜到发生了什么,她想到常在本地报纸上读到的一个词:非礼。她刚刚被人非礼了。她在新加坡的四年里,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整个大学时期,生活都如她所愿,自由而单纯,她几乎只在宿舍和校园之间往来,她接触的男人除了老师就是她的男同学。非礼,在这里不是轻罪,可能导致鞭刑,但为什么仍然有男人铤而走险?她想到那个疲倦、面无表情、脸上流汗的中年男人,多么下流、险恶的男人!但她没想到报警,因为她没有当场抓住他,她没有证据也没有证人,而且,车已经走了……
下意识地,她把连衣裙下摆使劲儿往下拉,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的两条腿在打颤。她讨厌自己穿的这条有点儿紧身的连衣裙。她想,她不应该穿连衣裙坐公车,如果她穿了一条厚厚的牛仔裤、肥大的T恤衫,大概那个人就不会注意到她。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被涂上了脏东西,尤其是刚刚被碰到的地方……她跑到公车站后面干呕,吐不出来,却哭了起来。最后,她让自己平静下来,决定不再等公车,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
回到宿舍,她冲了半个小时的澡。从洗澡间出来,她把在公车上穿的那条连衣裙连同内衣一起装进塑料袋,扔进宿舍楼下面的垃圾箱。
猫
某一天,在热带岛屿午后两三点明晃晃的空旷时间里,她经过一片老组屋区,看见一只流浪猫。她跟随它到了其中一栋组屋楼下,在一楼的楼梯下面,她给这只猫倒了一大把猫粮,高兴地看着它吃完。平日里,她随身背的包里总放着一个原先装维他命的空塑料瓶,瓶子里装满猫粮。在外面偶遇流浪猫(这个城市有很多),她就尽量喂它们吃一顿,再陪它们玩儿一会儿。她想,不知道明天它们会怎么样呢,也许会被人打死,也许会病死,也许会给车撞死……对于流浪猫来说,这是个凶险的世界。今天,她在附近吃饭,吃过饭要走去公交车站。因为马路上暴晒,她就绕到阴凉的组屋下面,然后就遇到了这只猫。
这栋组屋楼下一个人都没有,连平时经常出现在组屋楼下娱乐休闲区、坐在石头小桌前发呆打盹的老人也没有。她想,也许这个时间年轻人都在工作,老人都在午睡。外面被阳光照得白炽虚幻,但组屋底下是阴凉的,楼道里有隐约的、忽而穿过的风。喂完猫,她在最下面的台阶上坐下,吃完干粮的猫在她脚下卧着,她不时挠挠它的头。这么热的午后,她也不急着赶回家(况且那也不算家,只有一个房间)。那猫很满足,还会偶尔兴起、来个全身翻滚,仿佛给她表演。她不禁笑了,心想这小家伙竟然懂得讨人欢心。
她看看猫,又看会儿手机,心想要是有杯咖啡就好了,坐在这里陪着小猫,也可以消磨大半个下午。就在她打算离开的时候,她听见有人从楼上走下来的声音。她怕自己坐在楼梯上挡路,就赶紧站起身。猫听到脚步声立即警觉地站起来,调转过身体盯住二楼和一楼的拐角处。当楼梯拐角处出现一个瘦长男人的身影时,小猫立即跑走了,一溜烟消失在组屋后边的矮灌木丛里,留下她一个人有点儿不知所措地站在楼下,还在想小猫为什么突然跑掉了、还会不会回来……
从上面下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洋人,不太高,很瘦。当他看到她,他仿佛很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然后,像很多注重礼节、爱打招呼的西方人一样,他满面笑容地对她说“嗨”。他笑得太用力,使他那张瘦脸上立刻挤满深刻的皱纹。但她注意到他不并难看,除了太瘦,瘦得皮包骨。他穿着牛仔裤,上面穿一件浅灰色的衬衫,样子像个老师。住在老组屋区的西方人并不多,她觉得他突然出现在这里有点儿奇怪。但她顾不得想太多,也对他说“嗨”。
“啊,”他语气热情地说,“我刚刚看到一只小猫,就在那儿,然后跑走了,是你养的猫吗?”
“不是我的猫,”她说,“是一只流浪猫,我也是刚看到它。”
“哦,是一只可爱的黄猫。”他说。
“对,它很可爱。”她笑着说。
“我看到它和你在一起,它好像和你很熟悉。”
“不,我也是刚刚看到它,我经过这里,顺便给它点儿吃的。”
“你真是太好了。”他说。
从他的英语口音,她猜他是英国人。
“你说你刚才喂了它,喂了它什么?”他仍然用热情和蔼的口气问,但他的语调里似乎有些怀疑,大概她看起来并不像是带着口粮来喂猫的善心人士。
她说她喂它猫粮,她包里就有一些干的猫粮。
“你真的太好了。”他用由衷赞叹的口气说,眼睛望着她,“我可以看看是什么样的猫粮吗?”
虽然这个要求在她听起来有点儿奇怪,但她还是好脾气地从包里拿出了那个塑料瓶。
“维他命。”他故作严肃地说,仿佛她是个顽皮、撒了谎的学生。
她打开盖子,他凑近过来看。
“哦!”他恍然大悟似的,然后笑起来。
她想最好趁机说“再见“,但她还没有开口,他又开始问她:“所以,你也住在这一带?为什么我从未见过你?”
“不,我只是路过这里,我要去坐公车……”
他不理会她的告别,说:“哦,那我太失望了。你这么好,而你不住在这里。如果你住在这里,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我是英国人,麦克,我在这里没有朋友。”他说着,向她伸出手。
出于礼貌,她只好也伸出手。
他使劲儿握了一下她的手。
她想,他可能只是想找个人说话,他可能只是个爱说话的、孤独的外国人……
就在她心里盘算着赶紧说一句礼貌的告别语时,他说:“你不介意吧?我觉得和你说说话很愉快。”
她想,和她想的一样,他只是想找个人说话。于是,她说:“当然,我不介意。但我……”
“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我听得出来,你没有他们那么重的口音,告诉我,你是哪里人?日本人?中国人?”他显得很愉快。
“我是中国人。”她老实回答。
“怪不得,你那么温柔。”他语气夸张地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小姑娘。”
“谢谢。”她脸红了,但她其实不喜欢“小姑娘”的叫法,她已经二十四五岁了,“很高兴认识你。我要去公车站了。”她紧接着说。她觉得她和他实在说太久了,而且他看起来没有告别的意思。
他看起来很失望,说:“我们刚认识……你赶着要去哪儿吗?”
“嗯,我得回家了。”
“如果我想请你喝一杯咖啡或是别的什么呢?你知道,我就住在楼上……”他说。
“不,不用了。谢谢。真的,我得走了。”她说。
“你住哪儿?我有车,我可以送你回家。我的车就停在那儿。”他说着,指了一下不远处的停车场。
她看了一眼烈日下空无一人的停车场,突然有点儿心慌,说:“不,真的不用了,我去坐公车。”
“我可以送你去公车站。”他说,“来吧,坐我的车。你可不应该被晒暴皮。”
“不,不用了。”她继续推辞。这午后的静寂和空荡,还有那只突然消失不见的猫,都让她心生不安。她的眼睛不由自主朝小猫消失的灌木丛看过去。在组屋区绿化带的矮灌木丛后,是一片浓密的雨林。
“哦,它钻进去了。”他立即注意到她的目光,说。
“是的。”她礼貌地笑笑,算是告别,“再见,我得走了。”
“难道它害怕我吗,那小东西?”他问,似乎没听见她说“再见”。
“猫都会有点儿怕人……陌生人。”她只好回答。
“你呢?你也怕陌生人?”他问,满脸堆笑地看着她。
他的语调、他盯住她看的目光,还有他那张极瘦的脸上仿佛小心翼翼的堆笑,都让她感觉异样。
“我要走了。”她转过身往前走。
“我也去停车场。”他说,走在她旁边。
他走得很近。她闻到他身上体味和古龙水混合的味道,有一丝酸涩,又有一股辛辣。
“你知道吗?”他在她旁边神秘兮兮地说,“在英语里,小猫还有另一个名字:Pussy。”
他的语调突然让她想到,她刚才那种异样的感觉可能因为他像一个病人,那种吸毒的人、精神有问题的人……
“Pussy。”他又低声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带着某种压抑的热情。
“Pussycat。”她说她听说过这个词,其实她只是想到一个女子乐队。她想,赶快走到停车场那儿吧……
“对,对,”他异常激动地说,“但是,只说Pussy,不要cat,哦,它还有一个意思,你可能不知道。它是指女孩子穿的内裤,就像你穿的那种……内裤。”
因为他说出了“underwear”这样的词,她愣了下。她确定了,他是一个病人。
“Pussy,小猫,女孩子的内裤,就像你穿的那种……”他越来越兴奋,“小小的,小东西,Pussy,这是不是很有趣?”
“不。”她极力挤出一个字。她想骂他,或者恶狠狠地说一句什么威胁的话,然后跑掉。但她发现她的语言系统完全瘫痪了。她现在只是害怕,内心充满恐惧,害怕这个疯子、变态接下来要说的话、要做的事……
“多遗憾,你不住在这里,不然我能经常见到你。哦,你身上很香,你用什么香水吗?你真好,喜欢小猫,柔软的小东西。坦白说,我没有那么喜欢猫,但我喜欢那种小猫,你知道我说的是那种小猫。”他说着,笑起来。
他“吃吃”吸气般的笑声让她浑身发冷。但她不敢甩开他跑走,她双腿发软,害怕自己一旦想逃走,就会被他一把抓住、拽回来。她确定他就是她在犯罪小说里看到过的那种变态白男,他们的扭曲一开始总是藏在普通人彬彬有礼的外表下,但他们这种人什么都做得出。她想,她现在不能流露出害怕、想逃跑的样子,如果她这样,他或许就会变成被刺激出捕猎热情的野兽,立即做出她难以想象的事。
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暗自加快脚步朝大路方向走,眼睛急速搜寻着四周:她想看到一个人!
他仍然在叽叽咕咕地低语,说的话越来越变态:“你刚才让我看你的猫粮时,我的胳膊肘碰到你的胸部了,你感觉到了吗?我立即喜欢上你了……太热了,到我的车上,我送你去车站……”
她脑子里“嗡嗡”作响,再也听不清他说什么。终于,在三四百米外的大路旁的人行道上,她看到一对年轻的情侣——高大的、穿着网球衫的男孩子,晒得黑黑的、穿着吊带背心和牛仔短裙的女孩子。
“哦!”她惊叫一声。
“什么?”他警觉地问。
“我看到我朋友了。”她指着那对情侣。
“你朋友?你没有提起你有朋友住在这儿。”他说,狐疑地看着她。
她注意到他眼里的光一下子变得又凶又冷,仿佛在说:你察觉到了?你想逃跑?……
“是我的同学。”她说完就开始狂奔。
她听到他在后面喊“嗨……嗨……”
她以短跑冲刺的速度向午后静寂的大路奔跑,不敢停,不敢回头看,只感到眼前跳动的白花花的光,还有耳边“呼呼”的气流以及她自己的喘气声、心脏“咚咚”狂跳的震动。她一刻不停地奔向大路、穿过大路,一直跑到那对情侣身边。“帮帮我”,她对他们说。直到这时,她才敢回头看一眼:停车场、组屋楼下、连接组屋之间的当顶棚的小路上,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
邮件
附件word文档写的是我在这个城市的两次遭遇,她在给那位报纸专栏作者、儿童心理医生的邮件里写道,“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二十多年后,我才决定把它讲给你,以故事的方式。我读了你的文章,它强烈地勾起我那些不好的记忆,也因为你不认识我。尤其,你是一位心理医生,我相信你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在眼神里暗藏评判和质疑:你是不是释放了什么错误信号?你当时为什么不?……有时候,在一个人受辱之后,这种质疑、不信任还会给她新的羞辱和痛苦。我相信你一定能理解:她当时可能太慌乱,根本想不出该如何反应;她可能太迷惑,不能确切地判断当时的情况;或者她只是太害怕,恐惧会让她失去力气甚至声音……什么都有可能让她无法做出大家所期望的理性、及时而正确的反应”。
我在中国度过的年少时代,也曾有过不止一次类似的遭遇:被给我看病的医生骚扰(那时我发高烧在病房里输液,他趁妈妈去厕所时走进来抚摸我的脸和手臂),被男同学堵在巷子里(他恳求抱我一下就放我走),晚自习课后回家路上被陌生男人跟踪……我不该扯这么远,我只是希望你知道,作为一个女孩,保护自己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年少时候,我总会想,等我长大了,这些烦扰、危险就会消失。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淡化了它们带给我的伤害。
在公车上的事发生后,我意识到作为单身女人的困境:一个年轻女人,单独行走在人世间,就像她独自走在深夜空寂的街上,她面临的危险肯定更大。我这么说希望你不会生气:在我们周围,总不缺乏那些不好的男人,他们在暗中窥伺。在这些坏猎人眼里,一个落单的女人就是最容易下手的猎物。
在第二个“故事”里,当我跑到那对情侣面前,虚弱地说“帮帮我”,我羡慕那个女孩——她很安全!在这个世界上,男人可以让你免于男人的伤害。这句话说出来可能会被误解,但从某种程度上,它却是事实。我记得晚自习放学回家路上被陌生男人跟踪后,我就让熟悉的男同学送我回家,然后我没有再遇到陌生人的跟踪。总之,在第二次的遭遇后,我卸下了我的独身主义“盾牌”。我过去所构想的成人世界的安全感因为这两件事而坍塌了。我发现我不会因成年而自动获得某种安全,也不会因生活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而获得安全。一个女人,在你彻底老去之前,你都不会自动获得这种安全。你当然可以极度谨慎小心,时刻警惕周围环境里可能存在的险恶,时刻不懈怠地自我保护,但我并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我知道夜里甚至光天化日下被一个男人跟踪的恐惧感,不管你过去多么自信多有安全感,那一刻,当那种丑恶、阴暗、绝对强大于你(体力上)的力量威胁着你,它绝对是碾压性的。直到你脱离危险之后,你还会吓得发抖、哭泣……我需要一个伴侣。后来,我和男友在一起后,我发现事实确实如此:当你身边有一个男性,来自其他男性的骚扰和威胁会少得多。
无论如何,我已经算是女人中很幸运的一个,没有遭到什么真的“毒手”。不过,以前的事不是没有后果,说起来你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在第一件事发生的两三年后,当我和我的男友关系到了最亲密阶段,我看到了男人身上的那个东西。它让我害怕!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住在一起,但我不愿意看见它,更不让它碰我,所以我们无法真正做爱。而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等我消除心理障碍。可能正是他的这种品质打动了我。可他不知道我的心理障碍从何而来,他以为那只是因为生疏和羞怯……
我想,每个人记忆中都有那么几块“污渍”,能够对你说出来,我感觉好多了。但我并不是把你当成一个“树洞”,我更希望它能让你对女性的处境多一些了解。这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遭遇,我相信许多女性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只是大部分将选择不说。作为一个男性,你可能永远无法感同身受那种自我保护的需要,那种忧虑、不安,它伴随一个女人整个的成长期、成熟期,而当某些伤害发生后,她只能默默吞咽那些恐惧、耻感、隐秘的痛苦,并且在日后小心地隐藏记忆的污渍……关于这些,你虽然无法感同身受,但你一定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