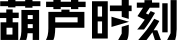古典文学专业的宛教授,在当下一众年富力强的博导中算个人物,在专业领域首屈一指。慕名而来想报考他博士生的,数量自然不少。宛教授性子倔,耿直坦率。前年教委主任考察中文系,主任是工科出身,却喜欢写格律诗,当场说了句附庸风雅的话:“古典文学么,我们都懂,把百来首唐诗宋词背熟了,一通百通……”坐在前排的宛教授听罢勃然变色,随即起身退席,嘴里还嘟囔着:“不懂装懂!”窘得陪同领导方寸大乱。这么一个有原则的教授,招收门生铁面无私,即使熟人相托,依旧严守标准,宁缺毋滥,不愿有所放松。如此这般,导致当下的宛门弟子,只有可怜巴巴三位。教授列出的标准,很显眼的一条,就是必须有自己的学术创见,擅长背资料的、掉书袋子的,他都不喜欢。曾有老朋友讽刺他,你搞的是古典文学啊,又不是文学创作和批评,都是几百上千年嚼下来的东西,哪里寻得出多少新鲜货?学术创见,从何谈起?宛教授振振有词,书本和资料是古人传下的,学术见解却不能抄袭前辈,依样画葫芦,那是工匠,费什么劲读博士?又有人善意劝过,说对年轻人要求别太高,眼下没有独立的学术见解,跟你宛教授几年,或许就可以培养出来。宛教授瞪大了双眼:“你以为我是神仙,有点石成金的本事?来读博士生的,不是少年郎,都到了二十五岁上下的年纪。二十五岁,孔子正以博学多才闻名于世,杜甫写出‘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名句。这岁数,若还没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我看,今后也没多大指望。”
他如此固执,中文系也奈何不得,于是只招了三位被他看上的学子。
来自安徽的李同学,年龄大些,硕士毕业后,工作了几年,不甘心在学术上止步不前,回过头来敲宛教授的门。考博士之前,他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曾引起宛教授的关注。那篇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古人的浪漫情怀》,论述中国文学开山之初,虽然不乏写实的内容,然而,想象力奇特的浪漫则是主调。宛教授关注此文,是察觉其中独到的见解。譬如《诗经》,说其浪漫情调,已经有相当论述,未必新鲜。李同学论文的重点,是由《诗经》溯源,追溯到远古的神话,比如“开天”,比如“射日”,比如“治水”,都生发出中华古人在荒蛮时期心胸的壮阔。李同学的论述,还进行了时空的横向比较,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同样面对大洪水,是登船逃避,还是上天入地抗争?中华祖先的气概,足以激励后人。宛教授在刊物上读到这篇论文时,拍案叫绝。等李同学登门报考,被宛教授欣然接纳,就是顺理成章的好事。另外两个门生,一男一女,比李同学小了几岁,均是修完硕士后直接报考,提交的硕士论文,在宛教授看来,都有前人未述之言,后来也就顺利地过了面试关。
皇甫是复姓,在“百家姓”五百多排序中,委屈末座。皇甫同学呢,也是宛门三杰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比李同学小六岁,比师姐花同学只差了五六个月。小一天也得谦称师弟,这是传统。何况皇甫天资聪颖,他愿意示弱,一口一个师哥师姐,和谐欢乐。李同学敦厚谦虚,花同学亭亭玉立,皇甫是帅哥一枚,给外人的观感,宛教授门下,汇集了金童玉女。不过,李同学在安徽时就成了家,这“金童玉女”的美感,就由花同学和皇甫来承接。
皇甫的聪颖,自幼显现。小学中学,从没让出前三的位置。进了大学,更是被师妹师弟们崇拜的学霸。可惜,进宛教授门下不久,他敏锐地察觉,花师姐并未把他放在眼里,经常叫他一声“小皇甫”,好像真把他看成小老弟。皇甫嘴上应承着师姐,心里却想,你有多大能耐,不就是仗着有几分姿色吗?读博士的女生,艳若桃花的,确实少见,花同学如她的姓,属于招蜂引蝶的级别,校内校外,不时有赶着来献殷勤的男生。皇甫不稀罕,也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念头。他在心底里暗自嘲笑师姐,是不是被众多追求者搞晕了,以为谁都是围住她旋转的工蜂?她那一声“小皇甫”的称呼,是警示自己安于师弟的位置,别存非分之想?皇甫心中“嘿嘿”,面子上不动声色,依旧“师姐师姐”叫得亲热。
读硕士的第二年,暑假里,皇甫和朋友去山西玩,主要是访问仰慕已久的云冈石窟。出行之前,做计划的时候,朋友的想法,是去敦煌。皇甫不同意,他说,写敦煌的文章,泛滥成灾了,做不出新的名堂。云冈石窟么,北魏时代修建的,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国人知道得不多,多多少少,还有新鲜感。当时,皇甫的硕士论文题目刚刚被推翻,正发愁没新的方向,暑期出游,带着明确的功利目标。
在云冈石窟逗留了两日,细细参观了十几个窟的雕塑壁画。面对栩栩如生的佛教故事,菩提树下佛陀如何降魔,观世音菩萨如何救苦救难,皇甫的灵感突然被打开了。在昏暗的旅店夜不能寐,一直清醒到天亮。失眠的收获,是抓住了一个精彩的论题。他曾经读过佛学的一些经典,与石窟中的艺术杰作互相印证,觉察到文学创作对宗教传播的价值。芸芸众生,除了简单明了的《心经》之类,其他复杂的经书,大体不会涉猎。佛学的传播,特别是能够渗透到缺少文化教育的底层,文学作品功不可没。像《大唐西域记》及其后的《西游记》,像戏剧《目连救母》等等,便是实证。
从云冈石窟归来,皇甫把硕士论文重新命题,确定为《经学的普及》,副题“文学创作对佛学传播的价值”,报告了导师,获得认可,才开始动手。一旦进入,便发现了任务的复杂艰巨,要阅读的文献典籍实在太多,皇甫不甘心把大好的年华全耗在故纸堆里。那天,他忧郁地站在宿舍窗前,看到一群花枝招展的女生,叽叽喳喳往食堂方向走,不由灵光乍现。本科生中,有他的几个小迷妹,本来,也就是闲得无聊时约了出去玩玩,现在,皇甫有了互利互通的新主意。他找到本科生中关系密切的三四位,当然不是召集小型会议,而是一个个单独谈,在咖啡馆或者小饭店里,每次几十元的成本,分别布置,谁读哪几本书,做点什么笔记摘要。皇甫聪明,不会让人家白做,总要给点儿劳务费。本科生们也并非在意那点劳务费,觉得为心仪甚久的帅哥做事,又是私下里相托,带些儿暧昧的味道,也就欣欣然接受。很快,尽心尽力的姑娘们完美交卷,让皇甫轻而易举掌握了写论文的资料。事前,皇甫关照过,凡是一般书上少见的观点想法,姑娘们一定要详细摘录。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女生们未必懂学术,却对新颖的感悟足够敏感,她们做了头道过滤,皇甫再沙里淘金,自然让论文别开生面。后来,考博士生,宛教授觉得那论文资料详实,观点别致,皇甫是做学问的料子。至于学问之外的招数,只怕宛教授想破脑袋也不得要领。
宛教授同样欣赏花同学的硕士论文,评价她的研究很别致,其主题是《宋代女词人的滥觞》。皇甫粗粗读过,觉得她就是下了苦工夫而已。花博士认为,宋代冒出百来位女词人,大大超过汉唐以来的女诗人,既要从词体与女性的契合度分析,更要关注宋代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由此发出了诸多宏论。有一日,三位同门闲聊,花同学对李师哥说,她写硕士论文,读了整整两年的书,才敢落笔。皇甫嘴上恭维,心里则是另一个念头:你这般熬夜费油地做学问,只怕是颜若桃花熬成一脸干枣,这辈子也做不成几件,傻妞!
师姐正是芳华岁月,无论走进什么样的女生群,都是最耀眼的那个。皇甫并非欣赏不了师姐的魅力,说真的,第一回在宛教授家见面,皇甫已经怦然心动,比起本科生中的那些迷妹,足可惊为天人了。假如师姐稍稍给皇甫一点温柔,他肯定鞍前马后不辞辛劳。他想不通的是,花师姐为啥总是低看自己。一个“小皇甫”的称呼也罢了,听顺耳了,或许可以当作昵称。关键是那眼神啊,看皇甫,很少正眼,斜刺里一扫,一副高冷的姿态。她若对谁都高冷,皇甫就认了,偏偏只对自己如此冷淡。外校有男生来访,明明是初次见面,花同学敢陪着在校园里慢悠悠地逛,肩并肩地,悠闲自如,毫不忌讳。至于面对李同学,那番亲热好感,丝毫不遮掩,半日里几十回,叫不尽的甜甜蜜蜜的“师哥”,小师妹的千种风情,白皙粉嫩的脸蛋,睫毛都颤抖着笑,整个鲜花盛开的模样,眼波粼粼,透露出压抑不住的敬服,比迷妹们瞧皇甫的神态,有过之而无不及,让皇甫瞧得牙根酸疼。本来,皇甫与李同学没有任何龃龉,李师哥温文尔雅,待他犹如兄长,学业和生活上,百般谦让。只是花师姐的冷热不均,厚此薄彼,让皇甫完全受不了,好像他俩是一对儿,皇甫压根儿属于弃子。皇甫心中恨恨地想,花某你昏头了吧,人家早就有了娇妻,你想夺人所爱?看吧,有你吃苦头的时候!
那天,宛教授给三位弟子讲课,聊的话题,是宋词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讲到结尾,宛教授话锋一转,提起他申请的一个项目。他说,按照学生们曾经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与各位合作来做,非常合适。课题名称:《风格位移》,副题“宋词豪放与婉约的难分难解”。宛教授说完名称,还把打印出来的课题说明给三位过目。宛教授解释道,历来的研究,是分类的,某某是豪放派代表,某某是婉约派代表。宛教授认为,那是把活生生的文化人格式化了。豪放派,哪个没有逍遥于花前月下,写几行浓情蜜语的句子?再说婉约派,即便常年生活在莺歌燕舞的楼阁,也免不了因为遭遇痛苦而振臂一呼,放肆地吼几声。宛教授设立这个研究项目,本意是打破偏见,让文学回归生活的本源与常识。他说,面前的三位学生,都具备善于辨析的思维。李同学研究远古的浪漫与现实,花同学探讨女词人与宋代社会的关联,皇甫论证文学创作对佛教传播的价值,看上去都是各自独立,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题材,不过,在由此及彼、左右互搏的思维逻辑方面,都能够突破呆板的线条,所以他想邀请三位弟子一起来完成这个项目。
宛教授素来不苟言笑,与弟子们交谈,眼光总是剑锋一般直视,让你无处逃遁,听得进还是听不进,同意或者反对一目了然。今天说到项目研究,他的语气是最温和的邀请状,学生们哪个不感动?赶紧一个劲地感谢老师提携。宛教授也就不再多问,直截了当说出打算。他会就此项目写出总论,约莫五万字,让三位弟子各做一个分论,就是按宛教授选出的三位词人,做分类研究,具体论证他们整体的创作生涯,着重体现他们词作的“位移”,就是在豪放与婉约之间的跨越变化,并且要分析其间的各种因素,包括社会影响、家庭问题、情感变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