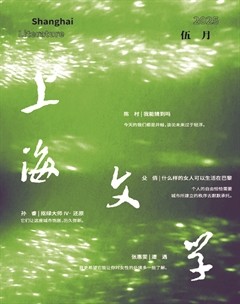一
窗外黑乎乎的,离天亮还早。陶光明看了一下表,才两点多钟,却再也睡不着了。但他必须睡着。他强迫自己这样做,闭上眼睛,开始在心里数数。据说,这样可以催眠。可数着数着便数乱了,心里更加烦躁,翻来覆去,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地又睡了一会儿,好像睡着了,又好像没睡着。醒来后,头脑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
终于,客厅有了响动。乔梅起床了。妻子乔梅每天清晨都要去小区跳广场舞,雷打不动。如果遇上下雨天,她们便会去雨棚下跳。
随着房门咔哒一响,陶光明知道乔梅已经出门了。他睁开眼睛,天已亮了。时间约莫是六点钟。乔梅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准时出门。陶光明不想动,他重新闭上眼睛,头脑发沉,嗓子发干,胸口发闷,有点喘不过气来。这种感觉已经有好多天了。可能与晚上没睡好有关系。到了白天,则浑身乏力,食欲不振,什么都不想吃,吃什么都不香。有时下楼散步时,腿也发软,迈动步子都费劲。
乔梅劝他去医院看看,他一口拒绝:“看啥看?有啥好看的!”他知道原因出在哪里。自从大老丁给搞倒后,他仿佛失去了目标,一下子没事做了。空虚!他想起专家们说的话:退休后必须尽快适应,找到新的目标,使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
这一点乔梅显然比他做得好。乔梅是普通工人,五十岁就退休了。按现代年龄划分,五十岁还属于中青年,还很“年轻”,有很多精力可挥洒。陶光明开始还为她担心,怕她适应不了。但他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乔梅很快就适应了退休生活。每天除了跳广场舞、买菜、烧饭,还在老年大学报名参加了书画班。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比上班时还忙。她还结识了一些新朋友,都是跳广场舞和上书画班认识的,时常结伴出去旅游。
这话倒也是。老陶夫妇只有一个女儿在国外,平时确实没什么事。老陶在职时,倒也不觉得,成天开会、出差、听取汇报、研究工作。在局里,他虽是个副调,好歹也是个副局级,平时大家也众星拱月般地敬着他,叫他局长,以示尊重。可退休后,情况大不同了。人们见到他虽然仍喊局长,但脸上早已写满了应付。有时他还寻摸点由头去机关看看,找点存在感,可大家都很忙,客气点的还让他坐坐,泡上一杯茶,大多数只是打个招呼,便把他晾在了一边。去了两次感到没趣,便再也不去了。机关不去了,食堂也没法去了。虽然他的饭卡还在,总不能为了吃顿饭跑去吧?再者说了,去了也尴尬,过去在职时总有人围着转,经常有人主动凑上来向他套近乎,现在倒好,人们躲他远远地。有时他打了饭菜,主动走到某人的桌边,人家也会找个理由避开。那神情好像是:理你不好,不理你也不好。乔梅说他太敏感了,可陶光明心里清楚,这不是什么敏感,而是世态炎凉。人一走茶就凉,这话说得一点没错。
相反,乔梅却没有他这些烦恼,每天过得开开心心,快快活活。乔梅退休时,陶光明曾支持她参加各种活动,现在反倒时常抱怨,尤其是对她结伴外出旅游尤为不快。因为她一走,家里冷冷清清,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了,吃饭也成了问题。
其实,陶光明会烧饭,厨艺远在乔梅之上。家里逢年过节,或来客,都是他亲自上灶,乔梅只有打下手的份儿。不过,平日家常饭菜都是乔梅买、乔梅烧,陶光明并不插手。特别是他荣升“副局”后,家里的事差不多全由乔梅包揽了。这已成为固定的模式。如果乔梅一出去,便全乱了。
乔梅好心提议道:“要不你和我们一起去玩吧?”陶光明听了鼻子一哼道:“你们那些人,不三不四的,我可不会去。”
乔梅知道他看不起人家。因为经常和她来往的,都是一些普通职工,地位不高。用陶光明的话说,没一个上档次的。乔梅对他的话很反感:“什么档次不档次的,退休了大家都一样,都是普通的老头老太。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不就是一个副调吗?退下来了,啥也不是,谁还悠你啊?”
乔梅的话说得难听,却是事实。陶光明也试图做出改变。有一次,乔梅拉他到老年大学书画班,想让他也参加。可他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都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啊!”他没好气地说。原因是他看到了机关食堂的老涂也在书画班上。老涂原是个临时工,在食堂里做大厨,还是陶光明当人事科长时批准招进来的。后来由于工作努力,转为正式工,并在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分管食堂工作。这种人陶光明压根儿看不上。老涂见到他倒是非常高兴,屁颠颠地跑过来,用那肥大的手巴掌紧紧地握住陶光明的手,连声叫道:“陶局长,你也来学画啊?”陶光明勉强笑了一下,心里满是厌恶,说看看,我来看看。老涂说太好了,欢迎欢迎。陶光明一肚子扫兴。“啥玩意儿?”他回去后便对乔梅说,“你们书画班,咋什么人都收啊?”
二
陶光明对级别特别看重,与人交往,总要把人家是什么级别搞清楚,同时也不忘亮一亮自己的身份——有时是暗示手下人介绍,有时身边没人,只好找机会故作轻描淡写地带出来——生怕别人不知道。有一次,省里有一批作家、记者来市里采风,他是陪同之一,谈话间又向人家说起自己的级别,结果却适得其反。事后有作家说,这家伙太可笑了,副调算个屁,省里一抓一大把。这话传进陶光明耳里,让他好一阵不自在。
陶光明家在农村,出身贫寒。自从大学毕业分到机关后,便苦苦奋斗,一门心思往上爬。好不容易熬到这一步,你说容易吗?其间不知经过多少周折,付出多少努力,虽说直到退休,“副”字也没有拿掉,让他引为憾事。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他的能力问题,而是他没有后台。为此,他一提起这事便大发牢骚。乔梅劝他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看关晓江、老杜他们,还不如你哩,连个副局都没干上。老舒资历多老啊,退休时不也是个副局吗?
乔梅这话是好意,可陶光明却不爱听。“他们算个屁啊,”他恼怒地说,“你老拿他们和我比?”
“怎么不能和你比了?”乔梅说,“关晓江、老杜都是研究生,学历比你高,老舒在你刚进机关时就是科长了。哪一个比你差?”
“得了吧,什么狗屁研究生,”陶光明说,“我是没考,我要考的话,能比他们差?”
“那你考啊,又没人不让你考。”
“我不是家里困难吗?”陶光明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要不我能不考吗?”说到这里,他突然光起火来:“乔梅,你怎么老说别人好,存心气我是吗?”
“我可没这个意思。这不是劝你嘛,心要放宽点。”
“算了吧,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陶光明沉下脸来,不再搭理乔梅。他最烦乔梅说别人比自己强,尤其是拿身边的人,如关晓江、老杜和他比。
陶光明比乔梅大两岁。他与乔梅认识是通过同班同学乔峰的介绍。乔梅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长得娇小可爱,人也很能干,原在部队当兵,退伍后到街道工作。陶光明虽是大学生,但家在农村,长相也不出众,皮肤黑黑的,瘦不拉几。乔梅开始根本看不上,后来陶光明毕业后进入机关工作,乔梅才同意和他好。陶光明当然求之不得,心里美滋滋的。可事后得知,乔峰原打算把乔梅介绍给关晓江,因为关晓江已有对象了才想起他,心里又很不是滋味,好像吃了一粒发霉豆子,一想起来就堵心得慌。关晓江与陶光明、乔峰是校友,不过比他们高两级,宿舍都在一个楼层,彼此熟悉。关晓江是干部子弟,能说会道,长相也很帅气,尽管陶光明不肯承认,事实上他的条件远不如关晓江。为此,他从心里嫉恨关晓江,尤其不愿乔梅提起他。
陶光明毕业后,关晓江又读了两年研究生,他们差不多前后分到机关工作,而且在一个科。由于关晓江是研究生毕业,无形中便压了陶光明一头。陶光明真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考研究生。其实,系主任当时很看好他,主动提议让他报考自己的研究生,可当时家里实在困难,三个弟妹都在读书,好不容易供他毕业,父母希望他尽早工作,接济家中。后来,他找机会考了一个党校在职研究生,但水分太大,还是比不了关晓江。
在科里的头几年,他和关晓江表面上关系还可以。那时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孙大明。孙大明是副科长,部队营级干部转业,作风狠辣,行事干练,平时管理严格,对关晓江、陶光明的散漫作风很是看不上,时常批评。关晓江不吃这一套,常和他当面顶撞。陶光明也讨厌孙大明,但他不敢公开撕破脸,只能在背后骂娘。
过了几年,科长到龄退休了,局里开始考察孙大明,要提他当科长。这一来关晓江急了。他找陶光明说:“这个鳖孙子要是上去了,我们没好日子过,咱得把他搞下来。”
“咋搞啊?”
“向上反映啊!”
说着就拉着陶光明一起去找局长。陶光明当然也不想孙大明当科长,不过他却不想出头,于是便说:“别啊,咱们还是分头去好,不要让局长以为我们是串通好的。”
关晓江觉得也对,便自己去了。后来,孙大明的科长果然没当上,调到另外一个科,仍是副科长。至于陶光明是否找过局长,他则含含糊糊。关晓江问起这事,他没说去,也没说没去,只是压低嗓门说,别声张,这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听这口气,好像是去了。关晓江也相信他去了。因为他后来听人事部的人说,孙大明没能提拔是因群众意见太大。如果只是他一个人去找局长,不可能是这样的结果。
实际上陶光明并没有去,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他自幼生活在底层,父亲打小就告诫他,别惹事,咱们陶姓是外来户,没根基,谁也惹不起。这种生存之道影响了他一辈子。凡事他不会像关晓江一样挺身而出,直抒胸臆,但他有自己的办法。早在农村上中学时,陶光明就知道了人民来信的力量。那时村里有个会计贪污公款,就被人民来信揭发了出来。这信是谁写的?一直无人知晓。有几个怀疑对象,死也不肯承认。这个会计虽有后台(村长是他的叔公),但人民来信写到了县里,县里派人下来查,村长也包不住。这事让陶光明记忆深刻。于是他回到家里,关上门便写起来。内容是说孙大明思想上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牢骚怪话多,业务水平低,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喜欢骂人,背后说领导坏话等等。这些内容有的是捕风捉影,添油加醋,有的是无中生有,刻意编造,但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全都有枝有蔓,有鼻子有眼,而且时间、地点俱在,不容你不信。陶光明是局里笔杆子之一,写起来并不费劲。不过,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电脑尚未普及,需要手写。况且为了产生效应,他不止写了一封,而是写了三四封。每封都用不同的口气,内容上也有变化,包括笔迹,不仅不能让人看出是他写的,还要避免让人看出是一个人写的。落款则写着“革命群众”,或“正义之声”“人民的声音”等等。为此,着实花了不少工夫。
不过,效果显而易见,孙大明的科长“黄了”,他的目的也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