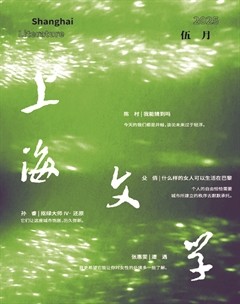闹完精神,吴亮余勇可贾,抓耳挠腮,无人陪他口角。中途出现过一个李陀,战了几个回合,看着不好玩就走了。寂寞中,吴亮开始手舞足蹈。有一阵,他的业余爱好就是每日从汪晖的书上撕下一页便开始质疑。汪教授学富五六车,话题遍及全球南方和北方,古代和现当代,还发明了著名的“通三统”理论,很神奇,这个那个与那那个刷的一通,就统一起来了。他的大作,我稍微一翻就两眼晕眩,总觉得教授说话怎么像是嘴巴里含着点什么,但我没本事也没兴致消炎。这种不好玩的事情只有吴亮能以毒攻毒。我将他的帖子置顶,谁爱看谁看。吴亮也是好精神,敲木鱼似的笃笃笃笃连续敲了八个月。这期间有过一个传说,真假未知,说是汪教授问跟吴亮相熟的同事,这个老吴要搞到什么时候?
一个被描绘成全球知名的学者,在东西方都很吃得开,著作至少等了半身,如此听任攻击,确有非常的雅量。未见同道和学生帮着开释两句,今天的学界交情太过寡淡。我想起民国时候的学人乱战,谁也不肯吃亏,现在真是另一番天地了。
汪教授的策略还是对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吴亮再有韧劲也输给了教授。
我花了不少篇幅写菜园的掐架,只因“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写起来很无味。其实论坛的主线跟我们日常民生一样,重在衣食住行,淡而有味。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看吵架。菜园点击最高的帖子是那个“请君牺牲色相”,各位菜农贴一点自拍,也有人贴自己的儿女。有个温婉的菜农叫秋心,她将“色相帖”中的一些图片做成两个视频,它曾长久在土豆网流传。菜园灭失后,我有时会点开它播放一下,看看那些曾朝夕相处的朋友。
另一个非常热心的网友是园外郎,网友称他员外,他是北京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文字不算太好,但喜欢文艺,乐于助人。我们去北京承他自费设局招待。他曾将迟子建的小说敲进电脑请大家共赏。更吃力的是,他愚公移山,将菜园迁居弄堂网时的不少帖子搬回菜园。见他太闲,我指引他去微博玩一玩,那里更可随心所欲,没人计较他写得好不好。他去了,果然乐此不疲。
很受欢迎的还有明珠写的“孔娘子厨房”。她是个热心人,烧得一手好菜,无偿指导大家。我们聚餐要等她来点菜,她能让大家所费不多却吃得很爽。我去她府上品尝过她的厨艺,中式加点日本料理的手势,十分美味。那时她家的猫咪还在。这只叫咪咪噜的漂亮猫咪后来作为主角被黄石画进一本彩铅绘本:《咪咪噜外滩迷失记》。更被她主人爱不释手地拍了无数照片,做了一本叫做《亲爱的咪咪噜》的小书。人在猫的面前再肉麻也只是常态。豆瓣网介绍说:“上海著名作家孔明珠通过描述咪咪噜的每一声喵叫、每一个眼神、每一种动作,展示猫与人真实的生活和故事,用她至纯至简的生活状态不断提醒着人生活的本来意义。探讨了当代人,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面对的禁锢、孤独、精神缺失等心灵层面的问题。”只可惜这猫身在福中不知福,自己出走了。
孔明珠眼疾手快地自号“明珠姐姐”,避免被叫成阿姨或外婆。她本是《交际与口才》杂志的老总,有著作多种,屈尊前来种菜,前去弄堂交友,令其先生看了好笑。她是大家闺秀,很不喜欢菜园闹哄哄的,好在这里闹起来时,她可以躲到弄堂网去,那里有她的姐妹们。
有些网友每日会来发帖,就像是日记。身在美国的陈茶(本名陈谦)便是这样,于是我们知道她常常爬山,山顶上有棵树。她曾在硅谷工作,后来好好的班不上了,辞职去写小说。她写的《特蕾莎的流氓犯》等小说很受好评。她在上海有房子,二〇〇八年曾请我们许多人去她家一聚。我找出照片看了下,那天在场的有扫舍、奕奕、孙未、毛友超、王雪瑛、右耳、老皮皮、一毛、卢新华、徐跃、查建渝、木叶、老鼠。人与人,原本相隔千山万水,就是这样忽然认识的。
同在美国的还有前面说过的哀牢山的老话梅,翩翩起舞的柔软的金刚钻,画家兼作家文取心(本名范迁,工油画,写长篇短篇小说),自称“哥哥我”的薛海翔(写多多电视剧)等。在日本的有陈骏、禅味等,在澳洲的有黄惟群等,在荷兰的有专心画画的海上鹭鹭,在法国的有很文艺的扫舍。作家谢宏在新西兰,他应我请求曾去探访顾城在岛上的旧居,拍回照片。树从废弃的汽车里长出,信箱还在。气氛诡异,他探头看了两眼,拍完照赶紧走。
除了在小酒馆“腐败”,偶尔也去谁的家中一聚。二〇〇六年看世界杯开幕时众人在小张家,玩着飞镖等待球赛。飞镖出界,将好好的墙上也砸出坑来。
我主张的兼收并蓄,并非包藏祸心。那些眼界很高的朋友有所不知,菜园每天都要开门迎客,如果只有那种脾气上来了才来大吃一顿的大侠,必然暴冷暴热,明天卖什么呢?再说,总是大鱼大肉也有损健康,还是要有汤汤水水。论坛上不以有名无名说事,许多好看是无名者做出来的。况且今天无名,还有明天呢。我眼看着管风琴、去年燕子渐渐被人们所熟知,看奕奕唱西洋美声唱成专业,甚至看着菜园的小娃娃们一个个出落得有模有样。再说,那些名不名的原本也是说着玩玩的,做人是否真的快乐跟这个无关。
我这里有个总的名册。我随手写下一些ID,他们常到菜园活动。除了文中提到的那些,还有竹怜新雨、小意、黄昱宁、塞壬歌声、龚静、央金、阿欠、坚白、刘晓萍、大老黄、winni、浮小沉、潘都、嵇启来、蝶衣君、烟视媚行;许德民、鲍不平、刘齐、刘苇、孟庆德、郭发财、寄居蟹、舒飞廉、沈胜衣、黄孝阳、菜园子、尾尾、老摇、孟昌明、玛特说、辛酉、八面来风、陶瓷了、三皮、猫主席等人。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姓。每个ID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看着这些姓名,我会想起他们的面容或发的帖子,想起我们去参加王寅的、王小龙的诗歌朗诵会,参观尔冬强的、潘曦的展览。我还知道有些朋友虽然不发帖,但每天会来看一眼,例如作家叶兆言。小众菜园犹如一个信息集散地。
菜园有不少奇人。像老鼠那种天才,教书教得好好的不干了,辞职画画,自号“半窗灵鼠斋”,网友怕麻烦,直接称他老鼠。他在租来的房子里燃灯造墨,灰烬弥屋,简直骇人听闻。有个小女友,有条大狗。他纠正我不能叫狗,要称作拉布拉多犬。他后来去南京住在朱府,跟定朱爷当学徒也是他的造化,只可叹朱爷寿短未能尽兴。他至今卖画为生,在网上续写他的本帮日记。
另一个奇人是古清生,他早先开一辆摩托,在网上做车的主题,参与过那本《中国可以说不》的热闹书。后来独自上神农架种茶,成了真的茶农菜农,贴图上的菜是他自己种的,伸出手来,是农人的粗手。舒飞廉在纸上怀念的农耕生活,他守着孤寂,做在大山里。老皮皮曾开车去看他。
提倡“拉筋”的童天一(本名钟健夫)也算一个。他是品牌文化的策划人,曾参与《南风窗》杂志的创办,文雅书生貌,喜欢网上说理。据他说,“读图时代”的说法是从他开始用的。我没考证,但可证明他曾身体力行。他曾开帖做实验,在一百天里每天拍照贴图。他的嗅觉很对头。同样题材的帖子,跟文字帖比较,图片帖的点击量是三倍以上。因网速和带宽之限,那时视频尚未推广,贴图也是限制像素的。尽管图像尚未动起来,童天一也玩得开心。我去广州时承蒙他和夫人招待。美丽的夫人钟洁玲也是老朋友了,当年榕树下丛书的责编。她在花城出版社,也是王小波文集的责编。
喜欢拍照的还有倾听远方,他构图严谨,横平竖直,不像我们歪歪斜斜一头乱发就出来见人。李娟的图片和江铸久芮迺伟拍的较为接近,自然而有气场。受到众口一词称赞的是何立伟,他原本是写诗的,写的小说十分空灵,《白色鸟》《花非花》,我跟他一起外出采风,他拍的照片比我好多了,可借用他小说的标题:大号叫人民。他用的相机我们多人都有,理光GRD,古文献硕士久久小姐给它起了外号,将它叫做“狗日的”,一下子就被人记住了。这相机可在非常近的距离对焦,我用它拍过不少微距,十分好玩。
菜园有个缺德的规矩:男人没有肖像权。拍了女人,她认为不好,马上就删除,无须理由。男人则无权抗议。男人拍男人,爱拍他嬉皮笑脸的,两眼发呆的,鼻孔喷气的。被拍下来了,只能让大家笑笑。男人这点牺牲都不肯做,如何解放全人类呢?
我拿女性没办法。我拍了照片,觉得蛮好看的,以为可以拍到马屁,贴图后,女主人公立刻不满意了。害我费力将图片做到指甲盖那么大小,将图片反转黑白颠倒成为示意图,有人依然不满意。拍了不让贴,我灵机一动转来一张外地报刊发表的照片,惹得小姐要跟我翻脸。你都让人拍了,让人登在报上,哪里还是隐私?有天,明珠姐姐说我当年拍的一张她和女儿的合影很珍贵,我听后百感交集。当年她觉得我太大胆了,要女同胞来砸我啊。我原本还以为自己可以报功呢。并非只有我遇到这样的无奈,有个叫嵇启来的摄影美女精心去拍另一个美女,我看照片很漂亮啊,图中人却嘤嘤地哭了一场。唉,这种叫照片的东西,太被期待了。一个人,不管长得好看不好看,都是自爱的。还是先存着,过五年不行就十年,等到二十年了拿出来,如同阿老开玩笑当面夸我摄影的用词:张张好!
有个年轻人比我狡猾,教我一招,拍照时焦距别对得太准。呵呵真是太聪明了!
这次的专栏文章,在杂志上发表无图,《上海文学》公众号发布时加了图片,顿时生动许多。现在的读者看到的老头老太,他们也有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小弟弟小妹妹。有多个朋友跟我说,图片很珍贵。谢谢他们。这些年我拍了不少照片,是希望大家看到他们的好样子的。但我确实不知道别人是否认为自己的样子足够好看了。现在的图片都有滤镜,不PS不见人。我拍照坚持不PS,除个别照片调整一下明暗,稍作剪裁,不瘦脸磨皮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