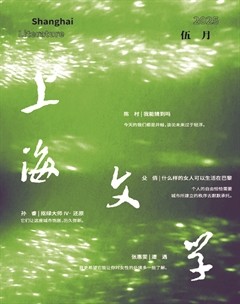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生活在巴黎,只要她在巴黎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间屋子,总结出自己平时去得最多的:邻近街区的几个小餐馆、一两家超市或菜市场,再加一个花店。
第一次在巴黎住一个月的时候,我搬进了算是朋友的女朋友Flora新租的蒙帕纳斯的小公寓,屋主是个老太太,小公寓位于一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筑的顶楼,有个种满花的小阳台,客厅里有个大玻璃柜,里面放满了银器。我看见这些漂亮的盘子碟子勺子的第一反应是,不怕丢吗?而老太太特地来和我们交接了一次,嘱托我们要一星期擦一次银器,连续干燥的季节则要一星期浇一次花,因为银器和花都是不能被冷落的。如果能做到这些,还能给减少一点租金。老太太临走时还给了一个她自己手画的附近的地图,告诉我们,可以在哪里买肉,在哪里买花,街角的小餐馆中看不中吃,但稍微再往车站走几步就有一个布列塔尼风味的煎饼店不错,诸如此类。回想起来,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老年女性,在不是特别担心钱的情况下,老太太们就很知道自己要什么,也会对人提特别具体的要求,这就特别好。
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老太太,朱莉亚·柴尔德算是最典型的代表。她是个身高一米八八的狮子座,熟悉巴黎的每一条大街小巷,深深了解自己喜欢的口味和爱的男人。但后来我看了电影《朱莉和朱莉亚》,却有点失望。因为里面只有一半的内容描写她在巴黎的生活,其余一半都是一个美国女白领在拼命模仿和致敬朱莉亚·柴尔德的心路历程。所有关于朱莉亚·柴尔德吃黄油煎鳎鱼、买菜、学厨,以及她妹妹来巴黎找到真爱的桥段我都很爱看,但到了美国朱莉的部分我就恨不得快进。因为她看上去真的又作又闹又想红,在厨房里干的一切都不是发自内心的爱,而近乎“我得混出个人样让你们瞧瞧”的执念,我真的有点不明白,拍个朱莉亚·柴尔德单独的个人传记片不好吗,为什么非得搭着卖这样一个人物。到影片结尾处,有一个细节是朱莉听闻朱莉亚本尊其实并不喜欢她模仿自己做菜,于是崩溃大哭,我却忽然在这个地方有点赞同编剧的心思。无论是什么人,只有活出真正的自己才会得到尊重,买菜做饭吃东西也一样,必须是发自内心,不要为了达成什么目标,或为了取悦什么人。而那位非常努力的女白领,明显是忙活了半天却仍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在巴黎居住过的女性据说都会比较容易找到自己,因为巴黎是繁杂而琐碎的,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太多的诱惑和太多的障眼法,刚来的时候不知道要去哪儿逛,到了服装店和食品店不知道要买什么,就连到餐馆要点瓶酒都会迷惑一阵子,因为很多家扔给你的酒单根本是《康熙字典》,厚得不知道从何读起,只看懂了侍者眼中的嘲弄。住一阵子之后,人就会逐渐从容,了解去哪儿吃喝去哪儿买蘑菇去哪儿买花去哪儿发呆,哪几个街区是自己的地盘可以闭着眼睛乱走,去哪几个街区又要怀着点敬畏和警惕,尽量低调行事。我在巴黎和Flora混了一个月后回国,一年后,曾经打算结婚的Flora恢复了单身,也结束任期离开了巴黎,她的下一站是纽约。这段旅居生活给Flora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她说:“住过巴黎的女人去哪儿都不会迷路,你看连巴黎的地铁都比纽约的复杂。”
二○一八年的夏天,我在巴黎约上了杰妮小姐,在离她家很近的名叫Automne的小餐馆相见。杰妮小姐是我在复旦的学妹,二十出头的时候我们在上海狠狠地过了几年精彩的单身生活。现在想起来,几个女生都在市中心上班,工作结束就约着一起晚餐,然后再去酒吧喝一杯,后面可能还连着夜店和卡拉OK,每天不过十二点不会甘心回到家躺床上。彼时最盛行的是美剧《欲望都市》,年轻的女生都觉得应该享受单身,不急着和某个男生确定恋爱关系,闺密才是最重要的人生伙伴。我们几个关系最密切的朋友里面,也确实和剧集里写的一样,有公关公司的白领,有坐写字楼的律师,有搞画廊和媒体的相对自由职业者,还有同声传译和HR。每晚我们都严格执行AA买单,说好工作第一,友情第二,爱情第三。但几年内,很快就有人叛变,说起来羞愧,那个人就是选择了闪婚的我。我还记得说出决定结婚的那一天很“抓马”,好几个姐妹都在饭桌上哭了出来,只有杰妮小姐淡淡地说:“我觉得不意外。”
有我带了个坏头,单身闺密组合里接二连三有人交往了固定男友,继而是结婚生子,在家给已经搬去北京的我打电话,讨论什么牌子的尿不湿不会让孩子屁股上长疹子。算起来,杰妮小姐是坚持单身的最后几个人之一。我不时回到上海,偶遇过迎面走来手抱一束花表情淡然的她,依然像二十出头的时候一样烫着大爆炸头。我对她挥手打招呼,不能免俗地问问感情生活,杰妮小姐一直是很淡淡地说话,中间加一点点语气词调味:“哎呀,我还是单身。”
后来听闻杰妮小姐去了巴黎工作,仍是单身,单身赴任。看杰妮小姐最初搬到巴黎的朋友圈,她一个人住在玛黑,楼下有间总是排长队的可丽饼店。她依然是个精彩而淡定的单身女郎,会拍一拍放在窗台上的鲜花、早餐时的面包、下班后随手拎回家的一瓶酒。这让当时已怀着老二的我心里有点淡淡的羡慕,毕竟生了孩子之后,个人空间被大大压缩。那时候老大已经开始学钢琴,老师在望京,我每星期都有几天要在北京交通最拥堵的时候,先到建外SOHO的幼儿园把老大接出来,然后在晚高峰的三环四环上慢慢挪动到望京,把女儿迅速交给老师之后,我为了占上一个车位,就只能在楼下车停得乱七八糟的老式小区里一圈一圈绕着,等有人驾车离开,若没有意外,十到十五分钟之后总能占上一个。这时候肚子里的婴儿在乱踢,我的脑子空茫一片,就想起杰妮小姐说的“我觉得不意外”,然后嗟叹:这人生到现在,已经没有意外了。
但二○一八年的夏天,我已经离婚。准备和杰妮小姐见面前夕,我去了百货公司给她初生的宝宝买礼物。站在粉嫩无比的婴儿服装柜台,看着那些浅蓝粉红的小袖子小裤管,几乎能感受到新生儿身上淡淡的香味,但这时候我的脑子忽然也空茫了。要知道现在我女儿已经在瑞士读初中,儿子也小学二年级了,小孩子baby的阶段已经离我太远,以至于完全不知道刚出生的婴儿得穿多大尺寸。要说老天还是懂得时不时给人点意外的:现在的我和杰妮,仿佛是各自人生的互换,如今的我已经恢复了单身,而杰妮小姐则即将生下她的第一个宝宝。
晚饭之前杰妮小姐顶着爆炸头穿着宽松的裙子从家散步到Automne,除了七八个月的肚子,她坐下来仍然是当年那个说话淡淡的女孩子,但时光流逝,风起云涌,一切看似没变但又变得太多,少女之间酷酷的淡然现在自然而然变成了中年人无声的感慨。就这么相对坐了几分钟,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处开始才好,直到老板娘笑眯眯出现,我们才想起来要点菜。说起来第一次杰妮小姐推荐给我这间小餐馆的时候还是名叫La Pulperia的阿根廷菜,吃了好几年这家出色的牛内脏料理后,在二○一七年,这里不知不觉被一对日本小夫妻接手,丈夫主厨,太太当服务员,忙前忙后就两个人,做的菜反而更好了。从Ceviche(南美腌辣生鱼片)到烤章鱼、鳌虾、阿根廷烤牛心和牛肋排,那种野趣十足的风格没变,菜品的味道反而更细致。当时我特别高兴地和小夫妻俩聊天,他们跟所有日本服务业者一样焦虑着,害怕未来能不能在巴黎站住脚,以至于不敢改掉餐馆原来的名字,因为怕老客人从此就不来了。但这个夏天,老板娘做主,已经给餐馆取了新名字:Automne(秋天)。杰妮小姐说这名字改得好,预示了我娃即将在秋天出生。老板娘哈哈大笑,已经爽朗得不像个日本人,她端上了酱烤的小牛胸腺和羊排,甜点则是牙买加胡椒和蜜柑味道的冰霜。吃得高兴了,又加上几杯酒和一些小型的俏皮话,填平了我们好几年没见的尴尬。孕妇是美丽的,我说她好似带着母性光环,杰妮小姐则自嘲说,是吃得满脸放光吧。她说我瘦了,我也自嘲说,离婚总会消耗一点脂肪的,是好的那部分。再到后来,两人都喝到酣然,不停说着,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俩会坐在巴黎的餐馆里,一个聊着育儿,另一个谈着要找谁约会。放下了少女的矜持,中年人总难免变得啰嗦,主要是内心的感慨在这十几年中积累了太多,层层叠叠的,好像徒手剥洋葱,还没到达内心就已经烦人地泪流满面了。
又过了五个月,在真正的巴黎秋天,我又来到这里去看刚出生的小麦克斯。虽然十一月天气已经阴冷,但温暖的房间里,爆炸头的妈妈像所有带孩子的母亲一样爱出汗,刚喂完奶,她一边给自己扇着风一边去给我倒杯白葡萄酒,小麦克斯躺在乳白色的小床上,歪着脑袋看从天花板上挂下来的一串会旋转的小玩具,不时发出轻柔的婴儿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