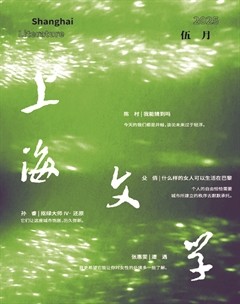听名家讲名著
一、冯骥才讲《海的沉默》
一九八○年在京参加《人民文学》笔会。有天晚上,同住一室的冯骥才绘声绘色讲起法国小说《海的沉默》:
法国在“二战”中沦陷,一个德军中尉住进了被征用的一间法国老人与侄女生活的房子。中尉尽可能不妨碍房主人的生活,只是晚上到起坐间说几句客套话,然后就靠在壁炉边侃侃独白:他的祖国、法国、音乐等等。
老人与侄女始终以沉默表达抵制,而中尉始终尊重他们的沉默,从不企图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回答、某种赞同,或者至少看他一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他的独白中,老人与侄女逐渐了解了他:一个生活在德国小城的音乐家,并不关心政治,也不喜欢国内的那些政治人物,对战争的理念与其他德国军官有着巨大的不同。在独白中,他表明了对法国的爱,也越来越清晰地流露出对那个美丽少女的情愫。
然后,他永远地消失了。
小说的主旋律就是两个字:沉默。
中尉出现的那天,侄女开了门,始终一声不吭……老人小口小口地啜着咖啡。
中尉略略点了点头。好像是在探测沉默的深度。
沉默变得越来越浓重,仿佛早晨的雾气,浓浓地纹丝不动……重得像是铅铸的。
老人和侄女默契着,丝毫不改变生活,即便是鸡毛蒜皮的小节也不改变,就像那军官并不存在,好像他只是一个幽灵。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情景:中尉敲门、进来、寒暄、独白、滔滔不绝。没有得到任何反应。然后,鞠躬,道晚安,走出去。
侄女机械地打着毛衣,并不瞅他一眼,一次也没有。老人则抽着烟,半躺在柔软的大安乐椅上。这种安如磐石的沉默似乎是不可动摇的。
中尉望着侄女,像在看一尊雕塑。而实际上,这也十足是一尊雕像。一尊有生命的雕像。
“我还曾为法国担心。而现在……我有幸遇上了一位严肃的老人。还有一位沉默的小姐。”
中尉带着一种庄重的执拗说:“一定要战胜这种沉默。一定要战胜法兰西的沉默。”
可是,好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中尉突然告知,第二天就要动身去战场。
他的……身体不再僵直。脸稍稍俯向地面。然后他抬起头来。
他更明确地说:
“奔赴地狱。”
中尉最后从内心发出凄厉的告白。老人报以默默的注目。
我以为他就要关上门走了。可是,不。他望着我侄女。他望着她。他说——他喃喃地说:
“再见。”
他一动不动地待着,而在他静止的、紧张的脸上,那双眼睛更加静止和紧张,它们凝视着我侄女的睁得太大、颜色太浅的眼睛。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姑娘终于启动了嘴唇。凡尔奈的双眸炯炯放光。
我听到了:
“再见。”
封·艾勃雷纳克也听到了,他挺了挺胸,而他的脸,他整个身子就像使人得到休息的浴后那样,仿佛变柔软了。
翌日,我下楼时,他已经走了。我侄女默默地伺候我用餐。我们默默地喝着。屋外,一个苍白的太阳透过雾霭闪烁着淡淡的光芒。我仿佛觉得天气很冷很冷。
小说结尾,少女那声终于给予中尉的回应,我听来惊心动魄。在“奔赴地狱”的前夜,中尉从少女微弱但清晰的回应中,感到了宽恕。作为国家的、民族的、战争的人,他们是对立的;作为人类的、人性的、艺术的人,他们是相通的。
小说以一种极为压抑的方式表达了战争对人性、情感、理想、文化的野蛮践踏,表达出作家强烈的反战理念和人道精神。
表现“沉默”,艺术家有过许多精彩的篇章。中国诗人白居易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成为成语;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有用十六只定音鼓表达沉默的豪言;法国小说家维尔高尔形容沉默,用的是海。广阔、深沉、撼动心灵。
这样的沉默,跟十六只定音鼓一样,是一种轰响。
而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不仅是认识到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更多少懂得了什么样的艺术才是真正有深度的艺术。
二、曹禺讲《阿芒得斯》
曹禺先生访问英国时看了歌剧《阿芒得斯》,回到北京后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讲这部歌剧的观感。
《阿芒得斯》主题是庸才对天才的扼杀。宫廷音乐家阿沙利瑞对音乐天才莫扎特,怀有浓烈而又深沉得仿佛爱情的嫉妒和恨意,演员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庸才和天才之间一场关于宽恕和嫉妒的斗争。
然而,如果仅止于此,那就只是一个表现嫉妒的平庸故事。高潮在于歌剧的结尾:阿沙利瑞临死时宣布——自己是莫扎特的“谋杀者”!更令人震惊的是,剧终前,主角阿沙利瑞走到台前,面对整个大厅的观众,大声问:
你们谁又不是扼杀天才的刽子手?
念出这句台词的时候,坐在讲台后面的曹禺先生“腾”地站起,模拟那位演员,声色俱厉,抬手指着前方。
这不是简单的技巧性的“反转”,而是对写作者的重要教益:主题的开掘不应浅尝辄止,要尽最大的可能进入深层。
《阿芒得斯》中,天才莫扎特陨落了,而“谋杀”天才的阿沙利瑞也不免让人同情。见证天才的辉煌,何其有幸;生活在天才的阴影下,又何其不幸。凡夫俗子的茫然、绝望和嫉妒撕咬着他的灵魂。作为同行,他其实是最懂也最爱莫扎特的人,可惜他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嫉妒也“扼杀”了他自己。这真是一个无解的悲哀。而正是这种悲哀,显示了作品和作家的深度。
三、贾大山讲《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我就学的那期中国作协文讲所,有贾大山。他是一群作家的中心。他们一有空就左右跟定了他,等着他口吐莲花。他则照例慢条斯理,一脸严肃,一本正经,忽然金口开启,一众前冲后仰,哄然大笑,所言不胫而走。
贾大山知道我对他的崇拜。文讲所快要结束的一个下午,没有课,他把我唤到宿舍后面的核桃园里。我们踩着树叶,踢着尘土在林子里走过来走过去,一直都是他在说话。
太阳若有若无地照耀在林子里,我的喉头老是涌动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时地抬眼看他。学习就要结束了,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他,我忽然说:想听他唱京剧《徐策跑城》。
“真喜欢?行,我给你唱。”
然后他就拉开架势,做一手捉刀、一手挽胡须状,一板一眼、一招一式地唱起来,那么投入,那么专业。完了,兴犹未尽,问我喜不喜欢《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我由衷说,你喜欢的我都喜欢。
“这是我在老家给作者讲课必讲的作品。”
贾大山说着,模仿着戏里的杜十娘一手抱着百宝箱,一手往水里一把一把扔珠宝,扔一把问一声渣男:“这值钱吗?”扔完了,纵身投水。
“真是荡气回肠!”
贾大山深深叹息。
“这是写刚烈,写抗争,写悲愤,写决绝。戏里的杜十娘绝望了,看戏人心里的杜十娘永生!”
四、邓刚讲《去看姐姐》
二○○五年,中国作协组团访美,一路上我与邓刚同住一室。因为老是更换住处,他睡不好。有天半夜睡过一个囫囵觉后,我听他还在翻来覆去,便起来拧亮床头灯,说:我不睡了,陪你说会儿话吧。他从床上一跃而起,站在两张床之间,给我复述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去看姐姐》。
邓刚说话充满了激情,有力地挥着手,语速越来越快,音量越来越高,脸和脖子涨得通红:
“我去看我的姐姐……”
这是小说每一个自然段的开头。在每一个自然段里,逐渐展开“我”去“看姐姐”的路上的一个个画面,逐渐展开“姐姐”的一个个侧面:她的美,她的善良,她的温情,她对“我”、对几乎所有人的各种好……我被小说、也被邓刚的激情牢牢抓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他,等待着“我”与“姐姐”见面的那个激情澎湃的时刻。
“姐姐的家就要到了,就在前面,就是那个看得见的村庄,我就要见到我的姐姐了……”
邓刚的手向远处指着,突然停住了叙述,静默了好几秒——我觉得那几秒是那么漫长——突然说:
“我没有姐姐。”
我一下怔住了。
泪水毫无出息地汹涌而出。
邓刚显然也被杰克·伦敦和自己感动了,以他惯常的幽默打趣说:你小子原来也会哭啊。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小说的中文译本。邓刚也记不清他当时看到的是哪本杂志。但他的复述已足以撼动我的心灵。那个夜晚,我明白了两个也许浅显也许简单却值得记住的道理:
1.叙事不必完整。意思讲清了,结局并不重要。
2.“姐姐”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姐姐”也许遥不可及,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你却一定会去看她。我相信,每一个认真的文学同行,心里都一定有一个这样的“姐姐”。
“姐姐”,是真、善、美的化身。
对我来说,文学的道路,就是去看“姐姐”的道路。
敬仰朴素
一、沈从文:《边城》
湘西边陲茶峒。“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常年作深翠颜色,迫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
一条小溪,溪边一座白色小塔,塔下一户人家:一位老人,一个花季少女,一只通人性的黄狗。
翠翠在青山绿水中长大,“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处处如一只小兽物”,“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野性清新脱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