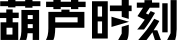一
有风习习,不知从何处而起。穿过苍苍的云,越过青翠的山,如一只无形的手,一把拂去江上的残雾,再一把,拂去时间的屏障。于是,天地万物裸露出清晰的轮廓和脉络,我看到那条著名的大江正与如水的长天对望。江边那几艘古老的渔舟,正与对岸的现代化摩天大厦对望。
我站在富春江畔空空的迎宾埠,面对一片辽阔的时空,与瞬间失去岁月遮掩的往事对望。江水汤汤,汪汪洋洋,泛着耀眼的银光,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也仿佛来自烟波浩渺的岁月深处。此时,在大地上流淌的河流与在时光中流淌的河流合而为一,激发起我钩沉这条大江历史的内心冲动。思绪如不系之舟,逆流而上,所及之处,竟有那么多深藏于浪峰波谷之间的故事,如一尾尾活泼的鱼儿,忽而向东,忽而向西,忽而向南,忽而向北。
有江鸥从江的上游迎面飞来,衔一尾银鱼,宛如信使,带来了远古的消息。让我在恍惚中隐约记起,这江,这水,原来正是我们的来处。亿万斯年我们告别了大海,告别了河流,告别了鱼龙竞渡的故乡,背对河流、水泽,向大陆深处疏散。渐行渐远矣!尽管我们一路上曾频频回首,却终于有一天彻底将河流淡忘于脑后。
然而,河流却一刻也没有放下她以慈爱、以血脉所滋养的众生,只为生命最原初的那次相遇,只为那一声从心底发出的称谓——“母亲河”。
于是,河流与大地携手,暗潜灵津,以慢慢泅洇的方式,以无声滋润的方式,不倦地追踪着生命的足迹,在大地深处悄然铺展开她广阔无边的恩泽,以解诸般生命之渴;河流与天空携手,高扬哺育之旗,云腾致雨,雾结为露,露结为霜,以雨露,以霜雪,以不同形态的情义,祝福着芸芸众生;河流也与水里的水族、鱼虾携手,以血,以肉,以生命滋养生命的方式,与人类保持着某种最直接的血脉关联。
太久啦,我们背离我们的出发之地。远离自然的城市生活,让我们不再有兴致去追溯生命之初的源泉,也不再追问我们的重量、我们的温度、我们的血流、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精神等等,从何而来。我们只知道吃了稻米和面粉,却不知道所有的粮食都来自于水,即便知道粮食来自于水,也不知道有些水是从河流里流淌出来直接进入粮食,有些水是从河流出发,在天空绕一个圈子后进入粮食的。也只有偶尔看到和吃到了水生的鱼虾,才恍然想起,原来,我们与河流之间还有着如此深切的关联。
在高楼林立、五光十色的桐庐,在飞架南北、车水马龙的现代化桥梁之侧,富春江边那几艘样式古旧的小船,看起来很像光阴匆匆流转过程中没来得及带走的遗落之物。
古渡无人,船上也无人,微波之中,它们不动也不摇,有如搁浅。岸上,固定缆绳的钢筋已经锈迹斑斑,尼龙质地的缆绳也毫无光泽,给人的感觉,那船从亘古以来就停在了那里,并且还要继续停泊下去,直到地老天荒。不过,插在船头的抄网和晾晒在木杆上的衣物却告诉我,它们只是睡着了。就在昨晚的夜色之中或今天凌晨的大雾之中,它们还在浪里穿梭,跟水里的鱼虾斗智斗勇,玩着人类童年时期每天都要玩的游戏。
突然就有了一种误入梦境的感觉。
那么,这些船有没有可能就是富春江遥远的记忆呢?大概,江在怀念往事的时候,不经意间将内心的情感就化作某种物像,浮出了水面。或者,它们只是富春江记忆的一个部分,最核心的内容是那些应该留在船上,而现在却不在船上的打渔人。可是,打渔人去了哪里?莫非这些船就是渔翁幻化的另一种形体,渔翁在疲惫中沉沉睡去,灵魂悄悄游离了躯壳,跑到岸上的某一个房间里,正与人说起昨夜的渔情或江上那些久远的往事?
二
我在江岸上一家鱼餐馆里找到了那条船的主人老钱。
见到老钱的那一刻,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江边的那些船,就是一些讲故事的人,确切地说,应该称“故事的讲述者”。事实上,它们就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载体,它们和驾驭它们的打渔人构成某种“灵魂组合”,停留于城市边缘,在我们的现实和记忆之间,往来穿梭,不断地为我们带来生命的滋养,以胃口的饱足,以味蕾的兴奋,以精神的愉悦,维持着我们对河流的感恩和怀念。
我不知道在我和老钱谈论富春江上的渔事时,江边上是否有一艘小船不见了,但我不能撇下眼前这个打渔人,跑到江边去求证我内心的幻觉。
老钱说,白天他是不打渔的,因为白天江对岸的高楼大厦和身边的喧闹嘈杂,让他不相信江水里会有鱼的存在。白日里,他内心烦乱,就如一张沉不到水底的网,捕捉不到任何真实、可靠的信息。只有到了夜晚,夜色遮挡了一切物像,也遮挡住了时代的影子,他才恢复了一个打渔人的自信和状态。
夕阳刚刚落山,他就坐不住了,早早地吃过饭,拎着补好的网,踩着世代打渔人的脚印,慢打逍遥地来到小船之上。爷爷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那套桨橹,早就让他当作纪念品挂在自家储藏室的墙上了,取而代之的是安装在船尾的那部柴油发动机。老钱是一个怀旧却不恋旧的人,否则他很可能就会像范蠡一样,消失在富春江上的烟波深处,一去不返了。
他可不想像父辈一样,笨笨的,仅凭一只老橹闯荡“江湖”。他害怕那欸乃声将自己带入岁月深处,再也回不到现实中来。江岸上还有他的家,还有开饭馆的漂亮妻子,还有需要他供养的生活,他必须沿着时间的路径回到现实。老钱是理性的、清醒的,他要做的不过是一种并不纯粹的交换,以鱼换钱,以江换岸,以一些鲜活的旧时光换一些现代人的期待、想象和隐约的怀念。
夜晚的富春江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星星们的耳语和风踏水面发出的足音。半个多世纪风里浪里跟鱼周旋,让老钱对富春江各类鱼的习性和活动规律了如指掌,哪个季节啥样的鱼群在什么时辰会出现自哪个水域,哪种鱼群会在水面上发出怎样的声音,全在他的心里记着。只要他站在船头侧耳倾听片刻,就能知道鱼群的具体位置。
夜色深沉,水下的生灵们以为没有了光,自己的大门就已经关得严严实实了,便大着胆子开始了成群结队的浪游、戏耍,为争抢一枚树上落下来的秋果忽聚忽散,却不知道水之外还有两种生灵在为一场猝不及防的捕猎而悄然夜行。一种是飞在半空的鸟儿,驾着风的车辇悄悄地在水面上逡巡;另一种是驾着小船的打渔人,早早息了船上的马达,一手轻轻地划动桨叶,一手频频抖动,向水里布下罗网。
入冬后,富春江里的鳊鱼群已经不再群聚于宽阔水域的表层,渐渐分散、潜伏至深水区的隐蔽处,成为这个季节很难捕捉的鱼。活跃了一春一夏的鳊鱼抓足了“膘”,为度过低温寒冷的冬季攒够了能量,进入了少动或不动的静养时段。一身饱满、鲜嫩的肉,使它们成为最好吃最可口的时令佳品。谁能在这个季节,吃上一条富春江里的大鳊鱼,那是幸运的,一定要因此而好好感谢一番幸运之神。据说,张大千有一年来富春江画画,为吃一条鳊鱼,足足在客栈里等了三天。清人徐鹄庭在《汉口竹枝词》里说:“不须考究食单方,冬月人家食品良。米酒汤圆宵夜好,鳊鱼肥美菜苔香。”如此,真不能怪张大千贪吃嘴馋,实在是诱惑太大。
这个季节是潮鱼的天下。它们仰仗着在富春江水域的“人多势众”,以压倒性的种群优势占领了大部分水域。在两米深的水层之内横冲直撞,不管天上掉下来什么,统统被它们抢食,其他鱼类还没等看到食物的影子,食物早已经被它们吞进肚子。老钱刚刚在他认定的水域停下船,就听小船左前方“嘭”的一声,根据这声响的特点,老钱立即断定那里有一群潮鱼,那是它们受到某种声音或不明扰动的刺激,突然改变运动状态,发出的“炸群”之声。还没过半分钟,在小船的左后方又是“嘭”的一声,还是潮鱼炸群。于是老钱明白,这是撞进潮鱼的老巢里了。如果不出意料,这一网上来,船舱里肯定不会有第二种鱼出现了。
类似的情况老钱毫不陌生。多年之前,富春江边还有渔业队时,这个季节也是这样。每到秋冬季节,富春江上的渔获只能以潮鱼为主,曾有人统计,不仅是秋冬季节,就富春江上全年的捕鱼总量,潮鱼可占到一半以上。
那时,网网打潮鱼真是一件让人犯愁的事情。因为潮鱼虽然存量很大,但并不是一个十分好吃的品种。潮鱼身体里的刺,细密而坚韧,这就使得它们在水里游泳、掠食的速度比其他鱼类快很多,相应,生长的速度也就比其他鱼类快很多。用于做食材的动植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生长越快的东西品质越差,吃起来营养、口感也都略逊一筹。潮鱼也是这样,特别是新鲜潮鱼,吃起来感觉满口的细刺,怎么择都择不净。在鱼类资源特别丰富的年代,这个季节的潮鱼基本没有人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