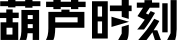漂流于瞬间的河
在橘园听嘉善田歌
置身于晚秋的橘园。
置身于熟果枝头。
置身于红碧相杂的软壳
或者业已红透的表皮。
直到攻破它的内部,看见
酸甜有致的所在:黄白
经络,橙红肌肤包裹于
透明的轻衣。用手指。用
嘴唇和牙齿。用喉与舌。
鼻子聚拢起了散落的清香。
然后,连耳朵也用上了。
歌声一阵阵传来。呜嗨嗨。
哦嗬嗬。置身于橘树的
某几片犹绿的叶子上,递送
歌声的风把上面的人们
顺带裹卷到了辽阔的半空
又坠落回来。就这样绕啊
绕,绕着橘园转了好几圈才
轻飘飘地着陆了。此时
就算你是本地人,也未必
分得清什么是滴落声,
什么是落秧歌,什么是
嗨罗调、羊骚头。你不过
随波逐流,在橘园
秋光盛大的午后,乘一叶
扁舟于节奏海中载沉载浮。
劫灰色
虹得七彩,雾都却难见,
管它爱丁堡、东京抑或重庆。
墨分五色,郭麐也曾说:
谢了梅花,才拓濛濛一面纱。
最近总想起,前年的八月
读夏可君《烟影与面纱》时,
用铅笔写下了若干批注并对他
戏称此即书上所言的劫灰色。
只不过是石墨芯划过纸面的
缕缕痕迹感谢了这番灵机一动。
从彼夏到此冬:面容在雨前,
影子在烟中,颜色在方外。
凿穿昆明池有赖一部《高僧传》,
洞烧黑白相间的奥义则要
求助于六经注我的奔腾烈焰。
从古典主义的山水花鸟到
当代艺术的锅碗瓢盆,理解力
钟情某种特殊的终末论:一切
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上海文学》2025年5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