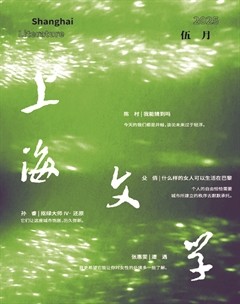走走:你给别的作家作品写过评论吗?
孙睿:很少写。被邀请过,写起来发现,小说评论,和小说创作完全不同。写小说是一种倾吐,写评论有点像翻弄别人吐出的食物残渣——当然也会有吐出的舍利。不太适应这种感觉,所以基本不再写小说评论,可能我自己需要吐出的未消化干净的生活残渣太多了。
走走:在你既往印象中,文学评论是怎样的文本?
孙睿:文学评论有点像教务主任,写小说像当个坏学生。我更喜欢做后者。
走走:请DeepSeek(以下简称DS)以文学批评的眼光解读作家孙睿的这个短篇《抠绿大师》(原刊《上海文学》二○二二年第八期)。
DS:首先,我需要通读整个故事,理解其主要情节、人物关系、主题思想以及艺术手法。这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几位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通过拍摄短视频的经历,展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挣扎与追求。故事中涉及了影视行业的艰辛、友情的支持、对梦想的坚持以及对生活的无奈。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和富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反映了当代青年在大城市中的生存状态。
在文学批评中,我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分析:探讨小说中“抠绿”这一行为的象征意义,以及其如何反映现代社会中真实与虚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2.人物塑造:分析主要人物(如“我”、宝弟、峰哥、阿双)的性格特点及其在故事中的发展,探讨他们如何体现特定群体的生活状态。
3.叙事结构:观察小说的叙事顺序、时间线和视角转换,评价其对故事表达的影响。
4.语言风格:注意作者使用的语言特点,如口语化表达、幽默感、意象运用等,分析其如何增强故事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5.象征与隐喻:识别并解读文中出现的象征元素(如吉普车、绿布、气球、雨水等),探讨其深层含义。
6.社会现实批判:结合当代中国社会背景,分析小说如何通过具体情节反映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体困境、物质与精神的矛盾等社会问题。
7.艺术与生活的辩证关系:探讨“抠绿”这一影视特效手法与人物生活状态的类比,以及艺术创作如何成为对抗“劣质生活”的方式。
(孙睿:看到这里,以上这七条,够一个文学硕士的水准了。)
在初步思考中,我发现“绿布”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影视道具,更象征着一种对现实的掩盖与重构。人物通过“抠绿”试图在虚拟世界中创造理想画面,但现实中却面临各种无法逃避的困境(如吉普车故障、经济压力、人际关系)。这种对比突显了现代人在追求梦想过程中的无奈与坚持。
此外,小说中的自然元素(如雨水、气球)和日常物品(如吉普车、泡面)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增强了文本的层次感。例如,雨水的突然降临既是对现实不可控的隐喻,也象征着净化与转折;气球则可能代表短暂的美好或虚无的希望。
(孙睿:雨水象征净化,写的时候没这样想过,只是情节需要,人物处境也需要更糟糕,所以写到了下雨。在描写下雨的时候,能感觉到有一种“洗刷净化”在发生,但这不是一开始就想给出的。气球那里,是一开始就想到了效果。)
(走走:DS的分析和传统评论者一样,无法推测写作者初心,但能通过有效训练赋予文本意义。)
在人物关系上,宝弟与阿双的互动展示了年轻人在都市中寻找情感依托的努力,而“我”与峰哥的友谊则体现了底层互助的温暖。然而,峰哥的突然离开和吉普车的困境暗示了这种互助在现实压力下的脆弱性。
叙事节奏方面,作者通过紧凑的情节推进和细节描写(如推车的体力消耗、拍摄过程的反复),生动再现了影视行业的艰辛,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角色的疲惫与坚持。
在语言风格上,孙睿使用了大量口语化的对话和黑色幽默,既符合人物身份,又缓解了沉重主题带来的压抑感。例如,宝弟用粗话激励推车的场景,既真实又富有喜剧效果,同时暗含对生活压力的无奈调侃。
最后,结尾处的开放式处理(吉普车被气球“拉住”的荒诞画面)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既是对现实困境的隐喻,也暗示了希望与坚持的可能性。
在进一步分析中,我需要结合具体文本细节,深入探讨上述各个层面,确保解读既有理论支撑,又紧密贴合作品本身。
(以上内容为DS的推理过程)
孙睿:它说的“进一步分析”,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常说的“细读”,它是会像人一样,再读一遍文本?
走走:我的理解是之前做的是推理工作,类似人类写评论时想好几个维度;“进一步”是将上述推理结构化成文,比如大概分几节,每一节讲几个要点,最后如何拔高。
DS:(以下为DS的正式回答)
文学批评视角下的《抠绿大师》:虚拟重构与现实困境的荒诞交响
孙睿的短篇小说《抠绿大师》以北京影视行业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为切口,通过一场荒诞的短视频拍摄事件,展现了当代青年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的挣扎与突围。小说以“抠绿”这一影视特效技术为核心隐喻,串联起技术时代的虚拟重构、底层生存的粗粝现实以及个体对“劣质生活”的抵抗,构成了一曲虚实交织的荒诞交响。
一、“抠绿”的象征:虚拟重构与现实的撕裂
“绿布”作为贯穿全文的核心意象,既是影视工业中遮蔽现实的工具,也是人物生存状态的隐喻。主人公们蒙在绿布下推动故障吉普车的场景,极具象征意味:他们以肉身之力对抗钢铁机械,试图通过“抠绿”技术让车辆“自动驾驶”,实则暗喻着底层群体在现实困境中强行制造理想假象的徒劳。这种“抠绿”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对现实的遮蔽与篡改——正如影视后期用虚拟背景覆盖绿布,小说中的角色也在用虚幻的希望覆盖生活的窘迫。然而,绿布下的汗水、膝盖的灼烧感、反复推车的挫败,无不提醒着“真实”的顽固存在。技术可以擦除画面中的绿布,却无法擦除生活的重负,这种撕裂构成了小说的悲剧底色。
二、人物群像:都市边缘人的生存寓言
小说中的人物均是被城市化浪潮裹挟的“失败者”:
“我”: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副美术”,靠囤积剧组破烂道具谋生,既渴望通过艺术突破“劣质生活”,又清醒地认识到“剧组是世界上最不靠谱的组织”。他的矛盾性正是当代文艺青年的缩影——在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间摇摆,用自嘲消解无力感。
宝弟:开小超市的北漂青年,以“剧组人设”追求阿双,用荒诞的拍摄计划维系脆弱的自尊。他的行为暴露了底层青年试图通过表演性身份跨越阶层鸿沟的虚妄。
峰哥:倒卖临期食品的“倒爷”,因经济纠纷入狱后选择逃离北京。他的经历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流动性生存”的代价——个体如同临期食品,在资本链条中被快速消耗、丢弃。
阿双:餐馆服务员,被宝弟邀请“客串司机”,口罩下的面孔始终模糊。她的存在象征着都市中无数匿名打工者,既是他人投射欲望的载体,也是自身命运沉默的承受者。
这群人物构成了一个“临时性共同体”:他们因一辆二手吉普车短暂联结,却终将被现实洪流冲散。峰哥的离开、吉普车的故障、拍摄计划的夭折,无不暗示着这种联结的脆弱性。
三、叙事策略:黑色幽默与细节的诗意
孙睿的叙事充满黑色幽默与反讽张力。例如,宝弟用“你妈”的粗话激励推车,将生理疼痛转化为荒诞笑料;导演用“一万搏十万”的赌徒逻辑拍摄短片,讽刺了艺术创作在资本逻辑下的异化。这些场景以戏谑消解沉重,却让现实的荒诞性更加刺目。
同时,小说通过密集的细节赋予平凡物象诗意:
吉普车“奋斗者”:既是峰哥谋生的工具,也是北漂精神的象征。它从土坡蹦跳而下的场景,宛如底层生存的笨拙舞蹈。
气球:作为短片中唯一的“魔幻元素”,气球在雨中爆裂、飘散,暗喻美好愿景的易碎。结尾吉普车被气球“拉住”的荒诞画面,则构成对“希望”的辩证追问——它究竟是救赎的绳索,还是自欺的幻觉?
雨水: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刷掉拍摄计划,却冲刷不掉生活的泥泞。雨水既是自然力的不可控象征,也暗合主人公内心淤积情绪的宣泄。
四、社会批判:技术时代的精神困局
小说通过“抠绿”与“劣质生活”的并置,批判了技术时代的精神困境。小艾因厌倦“伪饰现实”而逃离北京,指向现代人普遍的身份焦虑:当虚拟重构成为常态,真实反而成为需要被遮蔽的“瑕疵”。而“我”坚持留在北京,则暴露了艺术理想在消费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它既是抵抗“劣质生活”的武器,又是制造新幻觉的工具。
更深层的批判指向城市化进程中个体的原子化生存。峰哥的临期食品生意、宝弟的超市、阿双的服务员工作,均是被资本边缘化的“临时经济”。人物如同绿布前的道具,随时可能被替换、清除。而吉普车最终卡在山坡边缘的定格画面,正是对这一群体生存状态的精准隐喻:他们悬置于理想与现实、上升与坠落之间,唯有紧握虚无的绳索。
五、结语:荒诞中的微光
《抠绿大师》的结尾充满开放性:暴雨中的吉普车被气球“拉住”,既是对现实困境的荒诞写照,也暗藏着一丝悲壮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