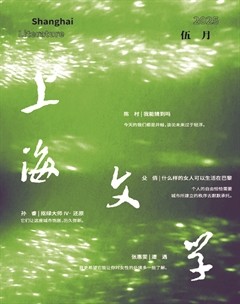零
在电影《坠落的审判》(二〇二三年)中,丈夫的坠楼死亡构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开场:荒无人烟的山间小屋;自杀、谋杀,还是意外坠楼的死因分析;妻子对于手上淤青来源的隐瞒;夫妻二人在婚姻中积蓄已久的矛盾;妻子小说里曾经出现过的“杀夫”情节……表面看起来,《坠落的审判》的核心故事是围绕一起死亡案件而展开,其中涉及到关于真相的调查、关于死因的推定、关于动机的剖析。但实际上,整部电影的真正用意却并非在此,片名中所谓要审判的“坠落”,不仅是丈夫“坠楼”的真相,更是关乎性别权力、婚姻关系等方面“失衡”与“崩塌”的真相。在这样一部电影中,对于案件真相的调查既作为整个故事的基本情节结构,同时又导向了作者真正想要探讨的核心主旨。换言之,“案件调查”在《坠落的审判》这部电影中,兼具了表达“题中之义”与连接“言外之意”的双重属性。
托多罗夫曾指出,传统侦探小说中一般包含有“犯罪的故事”与“侦破的故事”两个部分,前者通常只是一种“素材”(Fable),后者则作为“讲述”(Sujet)而存在,侦探小说通过后者的讲述来完成对前者的呈现和还原([法]茨维坦·托多罗夫《散文诗学:叙事研究论文选》,侯应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而在《坠落的审判》中,则还存在“第三个故事”,即日常婚姻生活的故事。伴随着“犯罪的故事”逐步浮出水面直至真相大白,“第三个故事”也慢慢展开其自身的细腻、微妙与复杂之处,同时还关联到性别、语言、移民、权力关系、道德与法律等一系列当下议题。
进一步来说,影片中“犯罪的故事”与“第三个故事”(日常婚姻生活的故事)彼此间还构成了一组互为表里的镜像式关系。薛超伟小说《同屋》(刊于《上海文学》二〇一七年第十二期)中的一处细节可以视为关于这方面的精彩暗示和绝佳隐喻:
林远把脑袋塞到水龙头下面,冲洗完,直起身擦头发,有一瞬间,他在镜子里看到了两个字:杀人。
仔细看,是徐坤新买的衣物除菌液。瓶身上写着“2.5L+1.5L”,下面是广告词:深入杀灭细菌。
故事里林远表面上看到的好像是充满惊悚感的“杀人”二字,但实际情况却是镜像中的衣物除菌液的广告词“深入杀灭细菌”,这个隐喻构成了我们理解很多小说之所以喜欢采取案件形式与查案结构的一个有效入口。在这些小说中,“案件”与“查案”更多是作为一种叙述装置,一种关于日常生活的呈现方式与镜像表达,作者真正的写作意图则隐藏在案件之外的生活缝隙或人性深处。而采用“案件”与“查案”框架的好处则在于,其可以赋予复杂生活以某种自我展开的结构,让读者和观众能够层层深入其中;通过家访调查、询问口供与庭审论辩等形式,令不可见者被看见,令沉默者被倾听;最终在案件真相揭露的时刻,同时揭示出生活或历史本身的真相;又或者借此告诉读者,和具体案件不同的地方在于,生活或历史可能根本就没有真相。
`一
海飞的小说《苏州河》(刊于《人民文学》二〇二一年第七期)同样开始于主人公陈宝山调查一起谋杀案:
宝山在苏州河边他家的屋顶平台上专心地喂鸽子时,赫德路五十五弄的一间出租房里,有个女人被割开喉咙倒在了血泊中。那天下午两点四十分光景,接警的徒弟炳坤开车来接他,顺便在路上给他捎了一只他喜欢吃的葱油饼。(海飞《苏州河》)
从小说后面的情节内容中我们可以知道,这起杀人事件不过是后来一系列连环杀人案的起点,接下来还有“理发店杀人案”和“汤团太太被杀案”将陆续发生。虽然陈宝山已经足够努力地在调查真相,并最终将目光准确聚焦到“三个死者都曾经在同一支部队”——国民党的七十二军这一关键点上,但他始终还是无法揭破笼罩于案情上方的最后一层迷雾。与此同时,这部小说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其在查案的基本结构之外,还铺设了谍战—反特斗争与日常生活两条情节线索。甚至就在本文所引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中,除了“被割开喉咙倒在了血泊中”的女人(查案),就还包括“专心地喂鸽子”和“喜欢吃的葱油饼”两个重要的信息提示,而这两个提示在后面的故事中分别暗示了整部小说的谍战情报传递(飞鸽传书)与日常生活趣味(所谓“过老百姓的日脚”)这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并行的重要面向。
作为《旗袍》《麻雀》《谍战深海之惊蛰》等几部知名“谍战剧”的编剧,海飞作品的谍战标签已然深入人心。与此同时,经常被忽略的是,海飞的创作范围并非只有谍战,其中还包括大量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比如其刚刚文学出道时,就曾于二〇〇三年凭短篇小说《闪光的胡琴》获得“《上海文学》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一等奖。而在海飞于二〇二三年出版的四卷本《海飞自选集》中,竟然没有收录一篇谍战小说。
说回《苏州河》,在这篇小说中,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变幻与反特斗争,作为民国警察系统一员的陈宝山——仅凭借其对政治、党派“这些基本不管”,只是专心于查案、破案,尽到警察本分的为人处事态度来说——是没有办法彻底查清这起连环杀人案背后的真相的。因为那本质上并非是一起简单的社会犯罪与杀人事件,而是一桩为安插间谍扫清障碍的政治阴谋。与此同时,小说中的反间谍故事(抓住张胜利)之所以能够和连环杀人案故事完美衔接,还在于两类小说本质上的相通性。即如John G. Cawelti等人所指出,“反间谍小说这个类型中‘逮捕间谍’是在形式上最接近侦探小说的一种”([美]John G. Cawelti、Bruce A. Rosenberg:《间谍小说的形式》,王蒇真译,《中外文学》二〇〇〇年第三期)。由此,小说《苏州河》中的追查凶手与抓捕特务前后两个故事才能顺利地合二为一。谍战叙事作为一般刑事案件故事的“政治升级”版本,将个别的谋杀案与社会历史变化的大趋势相互关联了起来,并由此引入了更为复杂的政治、立场、情感与人性维度。
另一方面,除了案件框架与悬疑设计之外,海飞的小说还有着扎实的故事情节作为基础。这一点仅从作为《苏州河》“番外”故事的《走马灯》(刊于《上海文学》二〇二四年第九期)中就可见一斑。在小说《走马灯》中,海飞剔除了小说中所有的类型装置,而把故事按照时间自然延伸的顺序与节奏慢慢地铺排开来。就像《苏州河》中来喜所感受到的:“日子像苏州河的河水,就这样不分昼夜地流淌着,从来也不会感觉到疲倦。”小说《走马灯》则将这样一种时间感受具像化为小说的形式结构,各色人物与事件在小说中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更重要的是,在抛却了悬疑、闪回、多线叙事、情节隐藏与显露等技巧之后,我们反而能更清楚地看到《苏州河》与《走马灯》在故事底层逻辑上的细致与耐心。
此外,即使在描写案件情节时——正如陈宝山随口抱怨的那句“杀人还挑落雨天”——海飞所要书写的,不仅是“杀人案”,还有“落雨天”。而其所展露出的绵密笔法,就如同案发现场上空“飘飞着缠绵的雨”一般。比如读者借助小说中陈宝山查案的脚步,进入到死者张静秋的房间,看到房间中央的尸体、凶手留下的痕迹、死者房间的布局以及由此可以推演和想象出来的死者生前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这些都是传统侦探小说与案件故事的基本情节套路。但海飞在这里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借助小说人物陈宝山的目光与强大的共情能力,体验到了死者临死之前一刻的微妙感受:
他想象着被凶手一把割开喉管时,张静秋的脖子一定痛得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