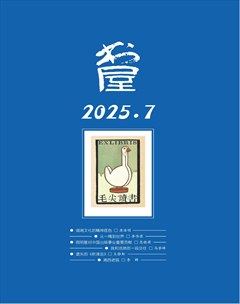我是1990年6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调入岳麓书社工作的,但初次认识唐浩明先生(那时称邓云生)却是在1987年7月21日上午。因我于1986年底从桑植县挂职副县长两年回社后,即被任命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党支部副书记,协助社长戴超伦同志分管党支部、人事和办公室的工作。那时的湖南出版是“多事之秋”,为配合党风整顿,我曾受省出版局党委派遣,分别到岳麓、科技、美术等社去听取党内外有关同志的意见,了解社领导班子成员的党风情况。那天上午,我到同一办公楼的岳麓书社分别找了四位同志(其中三名党员),各人都谈得有些激动,甚至有点火药味,唯有邓云生的谈话令我有些刮目相看。他温文尔雅,说岳麓社领导班子大问题还没有,行贿受贿的事更不存在。但小的问题还是不少,如“班子不团结,以身作则和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都不够”,认为有些是个人意气,并声明“我个人不介入”。他比我小一岁,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此人气量不小,豁达大度,似有点晚清岳麓书院学子、“收拾洪杨一役”曾国藩的影子。此时他正在编校《曾国藩全集》,我相信他定是一位能成大事的编辑,因而有点肃然起敬。
我被调任岳麓书社副社长后,协助潘运告社长抓图书选题和编辑工作。当时的岳麓书社已名声很大,有“社小名气大,人少好书多”的美誉。而且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三大全集出版的文化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但由于当时三大全集分别由杨坚、唐浩明、李润英三人负责组织编校,人手少,进度慢。编校一本印行一本,每册付印多少都不好确定,读者买书也心存疑虑,我觉得必须根据市场和读者的需求,改单本付印为全套推出,才能改变那种尴尬状况且可望产生较大的影响。于是与潘社长商量后,便分别找三位责编商量,决定暂时停止单本付印,集中力量,加大投入,加快进度,改单本付印为全套推出三大全集。
浩明先生是主动请缨担任《曾国藩全集》责任编辑的,当时不仅已做好全集的资料收集和复印工作,还亲自在做曾氏家书的整理标点,而且一边编校,一边潜心于近代史和曾国藩的研究,已发表了一篇《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和知人善用》的鸿文,反响很大。他非常赞同我的建议,说要请湘大历史系校点的团队帮忙加快进度,集中力量点校。不久,我还承蒙杨坚同志相邀,参与编校《船山全集》第十二册“子部”哲学著作八种,曾就幸遇船山手稿抄本《张子正蒙注》的深藏复出,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及《求索》等报刊发表了《王夫子〈张子正蒙注〉的版本新发现》一文,扩大了《船山全书》的影响。1993年3月我接任岳麓书社社长职务之后,三大全集更受到局社领导的高度重视,于是在1994年底一次性地推出三十册一千五百万字的《曾国藩全集》,首次付印八千套,半年后又加印五百套,创造了大型古籍图书罕见的畅销“双效”奇迹,同时引发了为时二三十年的“曾国藩热”。应该肯定,这一奇迹的出现,主要得益于浩明先生从文献整理到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功,即他的三部曲小说《曾国藩》畅销的影响。历史上毁誉参半的曾国藩,幸遇浩明先生这位学者型编辑、作家的艰苦努力而出现了“曾国藩热”,而唐浩明编辑生涯的巨大成功,也多亏遇到曾国藩这位富藏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杰出历史人物。可以说,倘若岳麓书社当初不是确定由唐浩明负责编校《曾国藩全集》,其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是不一定能达到“曾国藩热”的高度的。所以,唐先生不愧是曾国藩的异代知己。
我任社长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总结岳麓社前十二年出书的成功经验,确立了“坚持‘二为’方向,整理地方文丛,普及古典名著,弘扬古代文明;出版学术著作,致力文化积累;保持岳麓特色,继承发展创新”的办社宗旨,并将这一出书理念提炼为十六个字——“道承湘学,言纳百家,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作为出版社的文化追求,镌刻在书社新办公楼门厅的正面墙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