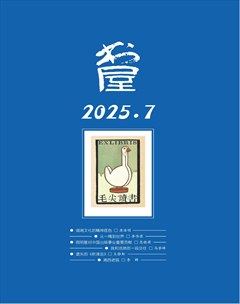从严格意义上讲,西方汉学肇端于十五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地理大发现时代也称大航海时代,在那个时期,欧洲航海者开辟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发展海外贸易,拓展海外市场。当时的海上霸主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随着适用于航海的帆船的发明,欧亚大陆有了更为便捷的交通,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由此,欧洲人才能航行到亚洲,进而到达中国。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海路更为便捷,装载货物更多。贸易往来需要语言支持,欧洲各国遂涌现出懂汉语的商人,进而培养出懂汉语的学者,从而促进了欧洲各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跟欧洲其他国家的汉学一样,荷兰汉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因为自身的历史条件,荷兰汉学的发展与欧洲其他国家汉学的发展又不完全一样。
一、荷兰汉学的滥觞
早在1592年,荷兰地理学家瓦格赫纳(Lucas Jansz Waghenaer,约1533—1606)出版的《航海宝鉴》(Thresoor der Zeevaert)一书就已描述航行在南中国海的事情,包括荷兰第一位到过中国的水手庞普有关中国的叙述。庞普是林斯霍顿船上的水手,关于他的叙述,瓦格赫纳是从林斯霍顿那里听来的。1596年,林斯霍顿在旅行日记《巡游记:水手林斯霍顿航行到葡属东印度》中记述了庞普的有关事迹,他还撰写了《葡萄牙人航海东方旅行纪事》。
这一类作品说明荷兰开始跟亚洲乃至中国有了联系,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学研究。真正的荷兰汉学发端于1602年在雅加达成立的荷属东印度公司,荷兰政府因此必须派驻管理人员,从此与当地人有了直接接触。当地有很多福建和广东华侨,这就直接跟中国语言文化(闽南语和粤语)和中国人打上了交道。荷兰汉学与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不同,因为它并没有与中国发生直接联系,如设立领事,从事传教活动、商业贸易,或进行学术交流等,而是始于为荷属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培训汉语翻译,他们希望培养“华侨通”,以方便他们与当地大量的福建和广东侨民沟通。这些翻译所从事的工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研究,但它为中荷沟通的方方面面奠定了“第三方”基础。1628年,赫尔尼俄斯成为荷兰第一位在雅加达传教的新教教士,他编撰了便于传教的《基督教纲要》。这部手稿可能是第一部荷汉和汉拉字典,荷兰汉学名家戴闻达和高柏都将其称为“荷兰汉学研究的第一座丰碑”。从发生学意义上看,荷兰汉学另辟蹊径,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观照华侨社会及风俗、商业社会及法规文化、非主流社会和地区生产活动方式、非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意识形态、地域性民间文化习俗等的独特视野和研究传统。
同时,阿姆斯特丹作为当时的国际出版中心,使荷兰成了彼时欧洲收集和传播中国知识的中心之一。1665年出版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节出使鞑靼可汗,即今中华帝国》,成了当时荷兰最有影响的出版物。它其实是荷兰首任驻京大使约翰·纽霍夫的调研报告。即便如此,荷兰汉学彼时也并未真正得到发展。
二、荷兰汉学的全面发展
荷兰汉学真正起步始于十九世纪。由于汉语翻译的培训并未取得理想效果,荷兰政府决定将其转移到荷兰本土进行,从而开启了荷兰汉学第二阶段:全面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荷兰一些大学内汉学教授席位的设立。1876年,莱顿大学首先设立汉语与中国文学教授席位。1877年10月,施古德荣任首位教授。这一席位后来依次由高延、戴闻达和何四维等人接任。施古德撰有一部四卷本荷兰语—厦门话词典《荷华文语类参》(Nederlangsch-Chineesh Woordenbuek met de Transcritie der Chineeshe Karac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ct),他在国际汉学界的最大贡献是1890年与高第一道创办了日后享誉学界的国际汉学研究学术期刊《通报》。施古德过世后,他的学生高延于1903年继任汉语与中国文学教授。高延的学术兴趣是研究中国宗教,他著有六卷本《中国宗教系统》。高延于1912年离开莱顿大学,转赴德国柏林大学执教,莱顿大学汉语与中国文学教授一职因而空缺多年。1919年,戴闻达受聘担任莱顿大学中国语文讲师。此前,荷兰汉学研究的主体都曾在荷属东印度公司任过职,而戴闻达则未在荷属东印度公司任职,由此可以说戴闻达之于荷兰汉学具有开创先河的意义。1930年,戴闻达就任汉语与中国文学教授。同年,在他的努力下,汉学研究院宣告成立,戴闻达出任首任院长,并编撰《莱顿汉学丛书》。这一丛书至今仍在持续出版,集中体现了荷兰汉学和莱顿汉学的学术成就和权威地位。其中,中国古代法律经典《商君书》和中国先秦哲学经典《道德经》两部译著,出自戴闻达之手,前者让他擢升为正教授,后者的荷兰语版于1942年出版,法语版和英语版也分别于1953年、1954年面世,在国际汉学研究界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