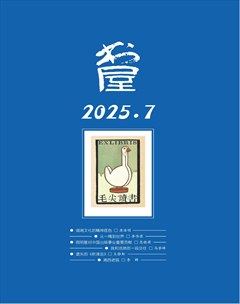我和浩然的一段交往
从小读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他笔下那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故事、活灵活现的人物令人难忘,所以,我一直很崇敬浩然。有幸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曾经和浩然先生有过一段交往。
1996年6月5日,在廊坊三河市,我见到了这位一生致力于“写农民,为农民写”的著名作家。那时我在省委组织部组织员办公室任正处级组织员,按照省委领导要求,率领由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省总工会、团省委和省工商局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到三河市调研民营企业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建设情况。这天下午,我们在三河泃阳宾馆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结束后,得知浩然居住的“泥土巢”就在宾馆一隅,于是,我决定去拜访浩然。敲开“泥土巢”小院的门,他的一个亲戚说浩然老师不在家,让我们把所住房间号和姓名留下,回来一定告诉他。晚餐后,八点左右,浩然打来电话,说马上到我的房间。见到崇敬已久的作家,我们都很激动。那天,浩然说了很多,六十四岁的他慈眉善目,诚厚朴实,颇为健谈。
浩然祖籍天津宝坻,1932年出生于唐山开滦赵各庄,早年曾当过《河北日报》记者。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之后,晚年的浩然舍弃了京城的安逸与舒适,扎根基层,定居河北三河,致力于培养农村青年和乡土文学作者,称这是一项“文艺绿化工程”。1986年11月,他携老伴来三河县长期深入生活,先在段甲岭镇挂职副镇长,后任段甲岭镇名誉镇长。1988年,三河的领导在政府招待所院内(今泃阳宾馆)僻静处为浩然夫妇建了一所新居。于是,浩然长期在此定居下来,并为居室题名为“泥土巢”,亲笔书写于小院门侧,寓意“下蛋”(写作品)、“孵雏”(扶持文学作者)的窝。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书屋》2025年7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