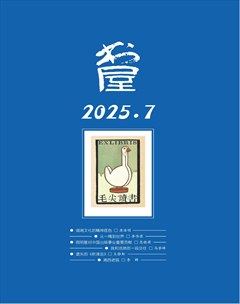翻阅丁利刚编《陈翰笙书信集》(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宋庆龄于1976年7月7日致陈翰笙的一通信函及随后的《陈翰笙为宋庆龄代拟〈追忆鲁迅先生〉》(1976年8月),引起了我的注意。函文不长,照录如下:
亲爱的朋友:
我于6月30日给你寄出一包特制的叉烧肉、素火腿和一罐花生酱,可以夹在三明治里。听说北京买不到花生酱,其他食品也很难买到。因你妹妹不在家,我就把包裹航空邮寄给了我北京的服务员张友,请他收到后立即送到你家。希望你能喜欢这些食品,我自己是非常爱吃的。
至于我胸部的疼痛,每天都有医生和护士来为我治疗,情况似乎有所好转。朋友告诉我北京眼下连花生酱都买不到。甚至连裘也找不到你的妹妹,而订购的食物是会变质的,所以我用航空邮寄,并打长途电话给我所信任的服务员张友,请他去机场取回后立即送到你家。希望你能喜欢。
随信附上《人民中国》的来信,请你看一下我写的文章,并将你认为应补充的关于鲁迅的内容添上。请先看一下茅盾写的文章(阅后请还我)。我认为茅盾写的内容太单薄,因为他肯定比一般人更了解鲁迅。根据我的回忆,有一天晚上,勃加莫洛夫大使和雷帮将军(他俩后来被召回莫斯科,被政敌无端指责与托洛斯基有牵连,在大清洗中被秘密警察枪毙)设宴邀请左翼人士,宴会后又招待大家观看了苏联的最新影片《夏伯阳》。夏伯阳是游击队队长。当勃加莫洛夫问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时,鲁迅回答说:“中国也有很多夏伯阳!”
当萧伯纳(在上海)短暂停留时,来参加在我寓所设的午餐会,在场的客人还有鲁迅、蔡元培、林语堂、伊罗生(Harold Issacs)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次聚会本应有很有意义的谈话,但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大声“耳语”对伊罗生说“激怒他!”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尤其是萧伯纳,因为他看了她一眼。只有林语堂随便闲谈了几句。这次聚会没有什么成果。以上是我能回忆到的一些事情。《中国建设》也许有这次午餐会的照片,但我在自己的照片收藏中没有找到。这篇短文是约稿,请根据我的回忆写一篇中文稿,并连同茅盾的文章一起送还给我。
非常感谢你的协助。
感激你的
SCL
又及:请原谅我字迹潦草。我的胸部和手因最近一次摔跤仍然疼痛不已。
(陈宇慧翻译)
陈翰笙(1897—2004),江苏无锡人,1915年赴美留学。1924年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1925年由李大钊介绍,陈翰笙加入国共合作中的中国国民党。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大师级社会科学家,在社会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诸多领域贡献卓著。1927年,陈翰笙在莫斯科认识宋庆龄,两人成为一生的挚友。那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绞杀,一心探寻救国道路的宋庆龄于9月抵达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