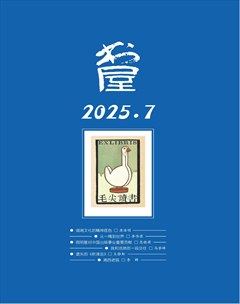1910年11月2日,也即中国辛亥革命前一年的农历十月初一,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一个姓费的书香人家喜添新丁,他就是未来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
这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因为,这一天乃是家喻户晓的所谓“鬼节”。传说,农历九月三十是阴曹地府准许亡魂返归阳间度假的日子,十月初一,五更天,鸡啼时,便要将阴魂收回。费家这娃娃降生于此刻,岂不是阎王爷没有回收的“小鬼”?
费孝通是费家的第五个孩子,最小,当然受到老奶奶和父母的格外疼爱。然而他身上似乎“鬼气”多多,据费孝通后来回忆,他“从小性情恶劣,经常寻事哭闹”,曾“从堂户满地滚过天井”,成为家人指责他顽皮的把柄。
这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于是经常怀疑,自己这个“小鬼”,到底“能不能划在‘人’的圈子里”。
后来,他一个男孩子上小学时入过女校;大学时数度转学转科;走入社会后,什么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乡村工业和小城镇研究,政治、经济等也统统涉猎;为人处世,“迂阔的性子,随处不能迎合他人,颇招社会的忌刻,小小的人,已蒙了社会的毒刺”,至老犹叹,“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曾高居于“庙堂”,也曾长期沦落成“罪人”;做文章天上地下,古今中外,国事家事,吃喝拉撒,无所不论,又纵横捭阖,不循章法,一挥而就;老来仍像年轻人一样,东闯西撞,事事关心,似乎有释放不尽的能量,如此之与“正道”格格不入,不甘心在别人画下的框框里做一个令人家“顺眼”的角色……于是他自我调侃是“圈外人物”“漏网的小鬼”。他将这些一概归因于“阎王的疏忽”。
他的父亲费璞安,虽然中过清末秀才,却是个新派人物,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即从事“新学”,因与南通大实业家张謇过从甚密,便到那里教书。小儿子名字费孝通中的“通”字,即由此得来。费璞安还做过江苏省“视学”,是一个小小的教育督导官员,也热衷于社会活动。孝通之母杨纫兰,出身名镇同里大家,是一名留日的新派知识女性,回国后创办了一家与现在的幼儿园性质一样的“蒙养院”,还办了一个“红十字会”。
费家保存着一张孝通与妈妈和几个哥哥姐姐的合影。八个月大的他,依偎于母亲怀抱,稚气可爱。妈妈梳着日式发型,颇显洋气时髦。二哥费青和三哥费霍,穿着蒙养院的新式制服,手中各持一面“红十字会”的小会旗。有趣的是,大哥振东却穿长袍,留着清朝的辫子。
费孝通一家,上有祖母和她守寡的妹妹,下有子女五人。一家九口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度日。但母亲的理财持家原则,却是教育第一。
生于这样的家庭,费孝通没有了接受诸如“人之初,性本善”之类“旧学”训练的机会。他先上蒙养院,再入新式小学、中学,初学乃是“人手足刀尺”,乃至数、理、化、音、体、美这些新学科了。
这样的出身和启蒙教育,使费孝通一生之知识结构,虽然在所谓“国学”领域略显单薄,但在促使他融入新时代、新学科和世界新思想潮流方面,却起到一个“基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