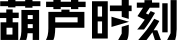1
这几天,一位自由记者出五千信用点的高价,请我写份战争回忆录。我憋了整个上午,只写出一句话:“战场是人类经验中最接近梦的一种形式。”还有很多话我不知如何说出口,比如准将在台子上讲:“军队会输,会死人,都是因为感情丰沛,胆小怕事。”比如军士长教给我冲锋的秘诀:“双目聚焦看光标,沉入回忆走一遭。”这话怎么理解呢?就是冲锋时,只要盯紧头盔里的光标就行了,让它引导你前进,自有比你强大得多的人在操纵着方向。你的自主意识可以放在黑暗里,随波逐流,最好沉浸于往昔的回忆,让自己变成机械,凭本能跟随双腿前进。这会让你忘记恐惧,安心当一个“不在场”的执行者。
起初,我和所有士兵一样,紧张到无法自控,经常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站住不动。长官假装没看到,依然把我排在队首,甚至为我提供了音乐。习惯之后,我放松多了,在多次的冲锋中,我都是念着军士长的秘诀,听着心爱的音乐,头也不回地奔向未知的阵地,有时甚至产生飞翔的错觉。我逐渐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只是旁观自己的奔跑,冲锋才是沉静的休憩,这具肉体能否生存和我没多大关系,它仅仅是赌局上的彩头和筹码。最后,我麻木到可以毫不迟疑地跟随光标踏足死亡陷阱,也可以看着别人在身边死去而没有任何感觉。日复一日,在黑暗的意识深处,我处于极度的抑制状态,奔跑时的幻觉中,除了邻家姐姐的一颦一笑,什么都想不起来。
那位姐姐比我大两到三岁,我们最初因为巴莉之死被联系在一起。巴莉是个女孩,是我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好朋友,我们在放学路上相识,在夏日的草地上并肩躺倒看天,在风和冰雪的花园里唱歌。她是我每日的期待和对生活最初的眷恋。但她的心脏不好,最终在一个寒冷的下午裂成了两瓣。我大喊大叫的时候,邻居姐姐跑了出来,大人们也赶过来,可谁也摇不醒她。她倒下后,院子里的黄叶依然在下落,落在她的身上和嘴里,秋日的枯草味道遮盖住了她的气味,树冠的尘土降落在她微睁的眼睛上,它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世界依然在不懈地运行。此后,我很多次在公园树下哭泣。那位毫无血缘关系的姐姐便抱起我,把我带到她家里,她妈妈用果汁招待我,仿佛失去最多的不是巴莉的家人,而是我这个爱哭鼻子的男孩。巴莉下葬的时候,我和姐姐没有去。她领我躲在院子的阴影里,第一次学人猿泰山在高高的木头上啸叫,终于逗得我咯咯笑起来。那天傍晚,她在树上站着,闪闪发光。
所以,当炸弹在我身边爆破的时候,我依然在回忆着她。我被飓风般的气流顶飞,头部先着地,她一下子从脑子里蹦了出来,占据了我整个视野。她冲我笑,以反常识的极快语速说着过去的笑话,学树杈上的人猿泰山。我的疼痛似乎减轻了一点。临终的回旋曲响起,我发现自己身处并不存在的大雨和雾中,漆黑一片中有暗紫色的图形,播放着小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光,以及成年后擦肩而过的生活。很多事模糊极了,可能只是我的幻想而已。人们常说濒死体验都是白光、大门和一辈子的走马灯,比如罗纳德·里根临终前开门,看到一生中的许多天使,荣格则见到了通往辉煌地球全景的旅程。而我不是,我看到的只有姐姐。
几秒钟后,光标竟然找到了我,我很快被勤务队带回救护中心,保住了一条命。住院期间,我生不如死,被TBIS慢慢吞噬掉——这是创伤性脑损伤的一种,我大脑的内嗅皮层和海马体失去了联系,无法通过自动交流巩固新的记忆,也很难检索保存旧记忆的神经元。于是大批记忆就像封存在板条箱里的故事,再也无法读取。在箱子彻底锁死之前,他们想了个办法拯救我。由于我立功不小,长官为我申请到一级特殊保障待遇。他们把一块实验性移植体嵌入我的脑子,代替内嗅皮层发挥作用。这生化怪物机灵得很,能阅读并解释脑信号,迅速做出反应,刺激检索记忆的神经元。这样,我就成了一本活的百科全书,你问我过去发生的事情,我都能想得起来,甚至比正常人反应还快。在一次战术会议上,刚刚出院的我坐在上尉和军士长身边,接受全营同袍致敬的掌声。我之所以得到这些礼遇,全是因为碰巧活了下来,至于那些盖上旗子掩埋进地狱的死者,却没有谁会想起。大家都逃避那些事情,仿佛不把桃子剥开,里边的虫子就不存在。
会议上,上尉强调,新的设备要运送过来了,大家务必掌握第十五版战术手册新增加的三十项内容。现在,有谁能复述一下两个月前战术培训的内容吗?
大家面面相觑,几个倒霉的士兵尝试了一下,全部被罚做力量练习。全营没有人能完成这个任务。
“我记得这个!”我举起手,随后面向大家,开始复述整本战术手册的内容,扉页、人名、注释,事无巨细,倒背如流。
全营听得目瞪口呆,如痴如醉。最后,上尉受伤半瞎的眼睛透过护目镜蒙上一层雾气。他小声说:“散会。”
可最终,我还是被军队除名,遣送回了家。因为据记录员所讲,我对战术文件的解释纯属妄想,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这结局让我感到意外,所以,我现在也拿不准什么是真实了。我决定今后小心翼翼地生活,所以离开军营之前,我闭上眼,什么都不看,也不往脑子里记,避免在这里留下任何自己的痕迹。最后一次回到营房收拾东西,我看到枕头侧面有一行小字,那是我特意缝在枕头侧面的口诀——“双目聚焦看光标,沉入回忆走一遭。”我曾经每天枕着它入睡,现在,我再也不需要它了。我慢慢整理好自己的东西,把枕头翻过来,扔进了垃圾桶。
2
家乡的风依然很大,卷起灰尘和纸屑铺天盖地,活像过度商业化的古代遗迹。街道更换了秋冬期的发光路面,在白天闪烁着温和的微光。我坐在大巴车中段,往窗外看去,除了“全民提升”的社会福利广告外,没发现任何新鲜的东西。等候漫长红灯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扫地的老头晃晃悠悠、愁眉苦脸地走到车旁,在地上扒拉半天,把一张碎掉的卫生纸拨到簸箕里,但他走了几步,风一吹,纸片又飞走了,老头就像看不见一样,抬着头慢慢离开。
车子里的电视正在播放访谈节目,宣扬“全民提升”计划的重要意义。坐在右前方的一个女人总是回头看我。于是我把军队的荣誉勋章摘下来,揣进口袋里。
“近三年来,也就是执行提升计划之前,只有富翁们能接受医学改造疗法。”节目嘉宾侃侃而谈,“他们免疫了大多数疾病,延长寿命,健康快乐,而普罗大众依然挣扎在病痛的深渊里,社会不平等性进一步拉大。所以,我们把医学增强纳入全民社会保障,尽量为大家提供平等提升的机会。”
“是的,先生。但提升计划执行一年多了,还是有许多抗议活动和负面意见。”女主持人说,“比如,有人认为全民提升强行剥夺了他们主导自己身体的权利。还有人说,照这么改造和增强下去,人类将彻底改变,成为连自己都不认识的物种。您对这些观点怎么看?”
“这些阻力只是长期生活习惯引起的反弹。”嘉宾答道,“任何创新性的政策,执行中都会存在波动。但我们坚信,以社会保障为主导的提升计划,会让最广泛的受众免费享受公共医疗改造,使大家增强各方面身体机能,延长寿命,获得更丰富、更健康的人生。人们会慢慢习惯这些疗法,就像习惯每年注射疫苗一样。自豪地说,通过全民提升,目前我们已基本攻克了囊包性纤维症、脊髓性肌萎缩症、终末期肾病……”
这时,大巴车突然像撞到死狗一样停了下来,人们的脑袋一致向前甩动了十厘米。是换乘站到了。我拿起自己的包裹,随大半乘客走下车,一眼就看到了站牌下的姐姐。我们已多年未见,姐姐还是那么美丽,只是长发扎成了马尾,眼袋微微鼓出,皮肤发红,像刚哭过一样。但我知道她没有哭,脑袋里的移植体从记忆库中检索出,那可能只是风吹过中年人皮肤引发的表象。
“姐姐。”我喊她。
“你终于想起我了。”她说,“可惜为时已晚,来找我也没用,以前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请原谅我吧。那年我除了参军,真的没有别的出路。”
“好吧,你在参军和拥有一个家庭之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她抚摸着肚子说,“但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的孩子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什么东西会再为你诞生,会把你的基因传承下去了。”
她讲的是多年前的故事。那时我刚工作不久,姐姐因我的轻举妄动怀上了一个不健康的胎儿。我们违反了基因选择法,双双被罚,丢掉了各自的工作,孩子也未能成活。羞愧之下,我选择了逃避,远离家乡,当了一名开疆拓土的义务兵。从根本上讲,是我抛弃了被痛苦折磨的她,是我给了她双倍的痛苦。我永远欠这个温柔安慰我的人一辈子和一条命。
我坐上了她的车,她发动引擎,看都没看我一眼。
“请让我补偿你吧。”我说。
“怎么补偿?”
“一切可以效劳的事。”
“别把自己当骑士,”她说,“你要做的就是老实住在自己家里,少往我这里跑。”
“可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劳动力过剩了。我可以帮助你干一些……家务什么的。或者接送孩子。”
姐姐撇撇嘴,“好的,有需要我会叫你。但你还是离我那一大家子人远点,他们就像群未开化的动物。”
她说的那一家子,包括一个昵称史蒂夫的丈夫、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还有个上岁数的老人,那是史蒂夫的父亲。尽管她警告了我,但我去她家吃饭的时候,那家人还是打了我个措手不及。当时史蒂夫坐在我对面,一直看着我,冲我笑。两个孩子趴在桌子上,吃得满脸都是食物。老头子自始至终在一边打瞌睡。
我们吃完了一套巨型的人造肉餐,还有姐姐做的三种馅饼。酒足饭饱后,女主人去弄甜点。然后,史蒂夫开腔了。
“老兄,你知道我是个航海家。”史蒂夫说,“让我给你讲一个波利尼西亚的故事吧。”
我想说我并不知道他是航海家,但还是礼貌地点了点头。脑子里突然有个精灵开了口:“波利尼西亚是太平洋上的群岛,位于南北纬30°之间,是复活节岛人的故乡。”这是八年级的地理知识,移植体开始事无巨细地把课本内容罗列在我的脑海里。这湛蓝温和的大海和姐姐昨日的一举一动、城市铺上崭新路面的街道、无所事事的扫垃圾的老人、汽车上观望我的妇女,每一秒钟的镜头叠加在一起,通过不断复习使我的记忆愈发深刻了。
我想喊停,但精灵根本不听使唤。现在,太平洋的波涛正在史蒂夫脸上荡漾。
“我三十岁时去过波利尼西亚,”史蒂夫说,“待了一个月,每天像酋长一样光着身子,当地的妇女很崇拜我,现在某个小岛的村子里还有我的雕像。”
“石像吗?”
“稻草编织的。”
“南太平洋上没有稻草。”我说。精灵迅速检索了九年级课本的记忆。
史蒂夫撇撇嘴,“随便好了,反正那里有我的雕像,我是他们生殖崇拜的一部分。”
我担心地望了一眼两个孩子。他们正可怜巴巴地盯着自己的老爸。
“放松点,”史蒂夫说,“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两个寄养的婴儿,他们是在玻璃容器中长大的。”
“为什么跟我说这些?”我问。
“因为难得有人见证啊。”史蒂夫说,“我打听过,配偶是精神病的情况下,公证离婚签字需要第三方人物在场。”
他说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表格,迅速签完自己的名字,把它拍在桌子上。附近一个闪烁微光的浮空摄像机正在录下我们的一举一动。
“市立第二公证处,预付款公证。”我读道。
“现在我和你姐姐没有任何关系了。她精神问题不小,会经常在晚上哭,你知道吗?要么就好几天不讲话。我受够她了,我要回群岛,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几百个日日夜夜。而且,我要把我父亲带走,这该死的人造肉餐配不上他。”
旁边那位瞌睡的老头突然像屁股装了助推器般从沙发上弹射起来,然后去摸索自己的手包和拐杖。
“再见。”史蒂夫说,“你来了,有人照顾她,使我分外放心。”他说完,拉着老人,推门而去,只剩我坐在那里目瞪口呆。身旁的小男孩继续埋头吃饭,小女孩却号啕大哭,哭声把姐姐从厨房里引了出来。
“史蒂夫走了!”我说,“他提出离婚,然后立刻签了字,带着那个老头走了。要我把他追回来吗?”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无限制追击型飞弹。”精灵检索道。
“等等……”她说,“是我先提出来的。”
“你说什么……为什么要离婚呢?”
“和你有关系吗?”她说。
“可是你会难过。”
“你怎么知道我难过?”她说,“他已经把财产分割给我了。我骗他结婚,只是为了这几年的生活。”
我觉得头晕目眩。
“那么……今天你叫我来,也只是为了见证这个啰?”我失望地说。
她点点头,浮现一抹痛苦的神色,然后抱起自己的宝宝,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移植体在脑子里沉默着,我想说点什么,但检索不到任何关于安慰人的记忆。
我真是个地地道道的、自私的失败者。
3
我在自己家里住了下来,间或帮姐姐做一些力气活儿。几天后,我去看了一次巴莉的墓碑,那块墓碑位于一座无人照管的公墓角落,表面绿油油的,还挂着昨夜的雨滴。没有人给她摆娃娃,因为会被别人拿走,甚至还会顺手在墓碑上涂鸦。我带了一小丛花放在那里,希望它们在被人拿走之前,自己就已经枯萎腐烂了。
姐姐并没有去,她坐在车里等我。一个小女孩,墓碑就这样死板和寡淡——我上车后对她说——甚至连一点儿装饰都没有。于是姐姐下了车,从后备箱找出做手工的电动雕刻笔,到墓园里去了。我跟过去,发现她在巴莉墓碑上,雕刻了一个粗粗浅浅的并不明显的树叶子。
“能再雕一个小人儿吗?”我问她。
她把笔交给了我。于是我在一片粉尘中画了两个歪扭的小人。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关于往日的纪念。巴莉,我那死去的女孩……从此之后,我再也没去过巴莉的埋骨之地,在梦中,她化为一片落叶,已经离现世的人间远去了。
11月到了,这是本年度第五个“全民提升”执行月。2日一早,我就得带着姐姐和两个孩子去登记点排队。此次提升的内容是镜像神经元改造,由于没有相关记忆,脑中的移植物不能告诉我镜像神经元是什么,我只好认真观看了1日晚上的新闻访谈节目。主持人换成了一位漂亮的长腿变性者,嘉宾仍是那位专家。两人神情放松,仿佛在酒店大堂来了场爱的邂逅。
“老师,明天就要开始执行了。大家都非常关心,这次咱们提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是脑子吗?”
“这个啊,是增强大脑前额叶皮质中的一个神经元系统,一般我们叫它镜像神经元。”
“好复杂的名字,我还是喜欢后面的描述——像照镜子那样?”
“是的。”专家笑了笑,“这些神经元的功能就是赋予大家模仿的能力。有了它,我们才能认识并重复别人的动作,通过这种能力学习知识、掌握技能。还可以把别人的动作和自己的感受关联在一起,理解别人要表达的情绪,产生‘共情’。正是镜像神经元使我们成了会学习、有情感的高级生物,它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互相理解,形成牢不可破的社区。”
“真厉害。那继续提升它们,有什么作用呢?”
“更高效地学习、更快速地感受、更高级的理解力!”专家说,“一直以来,人类文化、艺术、科技方面的进步都仰赖于它来传播。增强镜像神经元之后,我们会更好地理解别人、传播文化、模仿潮流,让优秀的东西更加迅速地扩展开来,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哇,真好,这种神经元是人类专属的吗?天呐,做人可太棒了!”
“不,猴子也有镜像神经元。”专家笑着说,“但它们的功能要弱一些,比如,看见我们举手吃香蕉,它也会抬起爪子,流出口水。”
两人一起大笑起来。变性美女换了一个坐姿,看向摄影机方向,两腿交叠,朝镜头后的广大观众露出大白牙,仿佛增强镜像神经元之后,大家也能拥有她这样修长美丽的双腿。
“最后,再次通报一下执行区域吧。”她说。
“本次仍是分区执行。C1—D15这三十个区的居民在明日率先执行,其他区域仍需等待。”
“为什么选择这三十个区,是因为抗议活动比较频密吗?”主持人打趣道。
专家笑了起来。不得不说,他虽然是个中老年男子,但笑起来还挺好看。“我们的政策首先照顾低收入群体,”他说,“所以这三十区的人率先享受。”
“这就是绝对公平咯?”主持人笑盈盈地问。
“绝对公平。”专家笑着,斩钉截铁地说。
这时,如果我爸爸还活着,他会揶揄道:“老头这妆画得不错,快进一段殡葬广告吧!”但他已经死了,没有赶上“全民提升”的好时代。而如今,如果没有姐姐的话,我希望自己也快点去死——家庭不在了,感情也无以为继,在没有任何希望、任何目的的世界上,最好像田野的枯木般寂如死灰。
4
11月2日的大提升让我从沉沦的情绪中走了出去,因为那天我根本没有时间惆怅。我切身体会到,世上原来还存在这么多活人。上午,我驾车带着姐姐和两个孩子去登记,路过了漫长的隔离带,又经过河流一样的抗议人群,才到达目的地。抗议人员大多数都是外区过来的,他们的老家还没有进行本轮提升,所以今天有时间过来,把散发恶心气味的硝烟弹散布在本区的空气中。在户外排队登记时,我和一个戴绒线帽子的老人站在一起,他看到远处崩来一颗粗大的石子,竟敏捷地低下头躲了过去。然后直起腰来,骂了一句。
“这帮该死的蟊贼。”他冲我抱怨道。
“他们为什么聚集抗议?”我问,“不同意接受提升?”
他侧过头,用被老皱脸皮包裹的大眼睛看了看我。“我也不同意啊,”他说,“我们都不同意。”
“那大伙儿为什么自愿排队?”
“你不是傻子吧,或者找麻烦的记者?”
“我是刚退役的士兵。”
“是被骗的蠢蛋啊。”他说,“我告诉你,好让你死了好奇心。现在,社会保障中排除了那些被‘全民提升’攻克的疾病,如果你不参加提升的话,患那些病将求医无门。此外,如果你不提升的话,所有保险公司都不再向你提供人寿保险,因为你得病、早死的概率是别人的几倍。你看那些抗议的人,轮到他们区提升的话,他们也会乖乖接受,照样老老实实地排队。”
“那他们来打搅咱们,影响我们的效率,怎么解决呢?”
“没关系的,”他说,“我们也会去他们那里抗议。”
姐姐的儿子在我身后扑哧笑了出来。
“自由嘛,”老人咧嘴微笑,“这就是自由。”
等轮到我们时,我把四个人的表格一起交给年轻的登记员。她很快在姐姐和两个孩子的表格上盖了黑色印章,但拿着我的表格研究了好半天,直到后边的队伍有些不安起来。
“有什么问题吗?”我说。
登记员点点头,她摸了一下眉毛,左边的眼睛亮了起来,发出淡淡的蓝光。她抬眼看看我,又看看表格,扫描上传了我的个人资料,再次核对了社会保障登记信息。
“对不起,”她说,“你享受的是军队的一级特殊保障待遇,与平民没有关系,不能接受提升。”
“可是……”
“快走吧。”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问。
“自己和军队联系。”她不耐烦地冲我摆摆手。
后面的人已经开始抱怨了。我只好拿起表格,拉着姐姐和孩子们,进入医院大门。
“我倒觉得你很幸运。”姐姐抓紧我的胳膊,小声对我说。每次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她对我的态度就会好一点。这让我有些难受。这不是亲人甚至好朋友本应有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就像本来被拴在一起的小船,却被时间的潮水不断地互相推离。
医院里人很多,我们挤在大家中间,拿着登记的号码,排队进入增强室。我帮姐姐把女儿抱起来,她自己搂着男孩子。女孩把头放在我肩膀上,一只手拨弄着我的耳朵。
“为什么少了一块呀?”她问。
“是战场上……不,是节日烟花炸的。”我说。
“烟花在你手里爆炸了吗?”
“是啊,所以不要玩火,也不要一个人放烟花。”
“喂!”男孩说,“那你的手疼不疼?”
我把左手举起来,向他展示手心里长长的伤疤。
“已经好了。”我说,“你看,像什么动物?”
“像双头蜈蚣。”他说。
“还真像哎。”我又仔细看了看,说,“晚上说不定会动起来喔。”我没有骗他,皮下破裂的肌肉有时会一跳一跳的,里边的金属渣滓还令我隐隐作痛。
姐姐笑了,把男孩搂在怀里。
我们跟随队伍慢慢前进,穿过第二道门后,走廊被隔离线切成两半,变得非常狭窄,大伙依次进入一侧,仿佛这不是一条排队接受改造的人流,而是自动投喂怪兽的生产线。已完成增强的人们在我们身边的隔离线外走过,面色轻松地奔向出口。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表情都十分喜悦。
姐姐低声咕哝了点什么,她的表情越来越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