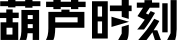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干掉他,我才能活。
于是我拿步枪瞄了五分钟,仍旧觉得不够保险,最终还是掏出了压箱底的杀器—— 一支2H铅笔。只需要按一下嵌在铅笔尾部的一小块橡皮,这个眼角耷拉的男人就会变成一地的碎屑。随后三千信用点将会进账,而我将靠这笔钱再活上两年。
男人就在这时候仰起了头,怔怔地望着暗粉色的夜空。
好家伙,果然好事成双。
所以我改了主意——我收起铅笔,小心翼翼地为它套上笔帽。按照业内的经验,此时此刻,他正在接收来自同类的信号,并将动身与之会合。我只需要跟紧他,找到另一个目标再动手,至少能赚双倍。
现在是凌晨三点二十七分,时间还来得及。
男人正踉跄着走上板条街。
唯一的风险从这家伙的脚步里冒了出来。眼下,他正在前往那条哪怕半夜都人声鼎沸的街巷,这单生意可能随时会被人群里的某个同行截和。毕竟,即使是一个菜鸟也能看出,这家伙不折不扣的死人身份。不过,除了同行以外,绝大部分人其实都死活不分。这主要是因为,如果一个人要活得舒坦,就得默认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只有咱们这一行是例外,每时每刻,我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处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鬼把戏——虚拟世界、元宇宙、赛博空间……总之是诸如此类的玄之又玄的词儿。咱们则心甘情愿把自己的意识从肉身里抠出来,塞进这个鬼地方,从此变成了由一大堆字节拼出来的数字生命。在这里,一辆坦克可能只是一份人畜无害的贴图文件,一枚硬币反倒是毁天灭地的数据核弹。人当然也一样。既然抛却了沉重的肉身,那么每个数字生命都能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男人、女人、超人、骷髅……怎么样都行。但无论现实的物理法则如何颠覆,死亡仍旧是每个数字生命必须面对的结局——
在这里,一呼一吸、一颦一笑都需要算力。
而算力是有限的。
这倒不完全是坏消息。既然寿命和算力挂钩,那么每个数字生命都能花钱买到寿命。虽然我的人生还剩下半个多小时,但只要干成这一票,拿到的赏金就够我再续上两年的命。但如果我失手了,我就会在半个多小时之后死掉。迄今为止,还没人能搞明白赛博空间里的死亡机制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人说这事儿有点像把文件扔进回收站,也有人说所有死于赛博空间的数字生命都会被赛博空间吸收。按理说,数字生命一旦死掉,就会彻底消失,但总有些家伙明明死了,却仍旧残留在这儿。第一个这样的活死人被发现于赛博空间诞生的第十三个年头,其外表看起来和活人没有任何区别,但透过其数据本质,便能发现这家伙几乎失去了所有记忆和人格,并且自身的数据结构也发生了全面的异变。当然,绝大多数人并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耐,并且为了追求虚拟世界的沉浸感也压根不愿意这么干。
一个新的行业应运而生。我们这些识别、清除活死人的人,叫清道夫。我入行的头两年,年景还相当不错,但随着涌入这行的人越来越多,业界也就变得僧多粥少。虽然活死人的数量始终没发生多大变化,但架不住同行太多,我已经有大半年没见过哪怕一个活死人了。没本行可干的时候,我就为企业打点零工,干点漏洞评估、渗透测试之类的杂活儿,能赚点,但始终入不敷出。我只能眼瞅着自己的算力越来越少。死亡没日没夜地朝我逼近,当我意识到自己哪怕再省吃俭用也活不过一年的时候,我觉得余生应该换一种活法。
在青叶酒吧,我消磨了两天两夜。离开的时候,余生还剩下半个多小时。
现在我又回来了。我倚靠在二楼的栏杆旁,手里握着一杯黑啤酒。往下俯瞰,视野中央是被炫目LED光束笼罩的舞池,那个活死人就站在其中。这家伙从石墨街一路走到穆可大道,然后又拐进珥东路,抄了一条连我都不知道的无名小路后,径直走进了青叶酒吧的舞池。这种情况很少见。一般来说,活死人都会避着人多的地方,几乎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紧贴着活人。与那些不断扭动身躯的舞者相比,几乎纹丝不动的他显得格格不入。但没人在乎。有几个胆大的姑娘甚至还把嘴唇凑向了这个家伙,然后假装捂嘴干呕,嘻嘻哈哈地转过身去。但她们全是活人。整个舞池,整个酒吧,找不出第二个活死人。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成双的好运——迄今为止,有关活死人会寻找自己同类的消息,都来自道听途说。这就意味着我很有可能错过了最佳的动手机会——此刻,他混在活人堆里,我完全没有命中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