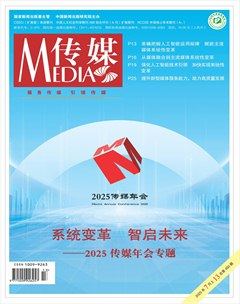网络虚拟主播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AR、VR等信息技术创造的,并在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等平台,面向多元化受众群体进行个性化、平等化社交互动的虚拟形象。2020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虚拟主播凭借深度陪伴的强关系优势,广泛进入受众日常生活。本质上来讲,网络虚拟主播的崛起,主要取决于其独特的拟社交互动机制,使得富有想象力的受众与肉身虚拟化的“他者”主播形成深层次、多维度交互,在虚拟与真实的强关系联结中全面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艾瑞咨询《2022年中国虚拟偶像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虚拟人带动产业市场规模和核心市场规模分别为1866.1亿元和120.8亿元,预计2025年将分别达到6402.7亿元和480.6亿元,其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充分彰显了虚拟偶像拟社会互动的价值地位。
所谓的拟社会互动(Para-socialinteraction),又称为“类社会交往”“拟社会交往”,最早是1956年由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霍尔顿·唐纳德和理查德·沃尔在《精神病学:人际关系与治疗》中提出的,是指现实情感在网络世界的虚拟转化,而这种转化后的情感会让个体产生单向依恋的心理感受。某种程度上讲,网络虚拟主播颠覆了社会互动中真实的概念,底层逻辑被改写,主播生产趋向虚拟化。在网络虚拟主播拟社会互动机制作用下,虚拟主播与受众之间形成了双向互惠的关系,在身体虚拟化背后的情感回归、符号消费下的双向创造、场景规则参与中的精神意义强化下,逐步由依附关系转向共生关系,借此促进虚拟主播的圈层扩展,充分体现了拟社会互动吸引、联结、同在的“显现机制”,对现实人际传播的范式流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吸引:身体虚拟化背后的情感回归
虚拟主播不同于现实中的人际交往主体,属于人际欲望虚拟化的载体存在,扮演着与受众人际交互理想化的符号角色。全媒体时代,个体焦虑、情感缺失问题愈加突出,人们的精神追求日益多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受众开始在虚拟世界寻求安慰,而虚拟主播就成为重要选择。虚拟主播通过身体虚拟化背后的情感回归,可以为受众提供超脱性消费体验,满足脱离生活的精神互动需求,借此实现对受众的有效吸引,由此夯实拟社会互动的基础,成为拟社会互动显现机制的起点。
1.身体虚拟化拓宽时空范围。不同于传统主播的真实在场,网络虚拟主播通过虚拟符号完成身体表达,打破了传统人类的生理局限,能够长期保持受众喜爱的特定形象。同时,网络虚拟主播能够在虚拟空间、现实空间自由转换,是个体身体高度虚拟化、媒介化的存在。拟社会互动理论认为,受众借由拟社会互动与媒介角色建立一种“幻觉式亲密关系”,然后满足其相关的目的性需求。对于虚拟主播来讲,身体虚拟化带来主播形象人格化,并为受众创造了具有较强开放性的想象空间,并围绕虚拟主播进行文化创造和深层交流,借此获取更多的情感满足。以虚拟主播柳叶熙为例,为了使柳夜熙的IP故事更能吸引受众,作者通过IP故事及其社会角色线索,并在技术赋能和文化加持下,形成具有较强张力的角色特质,借此打破时空的限制,有效拓宽了其拟社会互动的时空范围。
2.虚幻式亲密关系增强情感张力。本质上来讲,虚拟主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始终控制在既定情感范围内运作,以劳伦斯·克罗斯伯格“感受力”的界定来讲,就是“可将任何语动理论来讲,个人动机的使用和满足是影响双方关系的核心因素,也就是说,在两者关系达成的初始阶段,受众具有更多的主动权,而在关系稳定阶段,则会出于目的性需求进行多向度的符号消费,进而激活彼此双向创造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