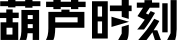善刚抱起孩子,递一只玩具狗到孩子手里。孩子捏一下,推掉,善刚就自己拿着,然后跟着备芳跨出门。没走几步,备芳却让善刚等一等,她觉得头上像是缺了啥,就返回屋里,把一条素方巾裹上。
一歇后,备芳和善刚差不多并排走在了东市街上。街两旁开着好多“踏板窗”——窗子上方有一块木板,白天可以用木棍撑开,晚上收起棍子,放下木板。不少房子的顶上,也开着老虎窗,窗外晒着的一些衣片被风一吹,像是大鸟的翅膀。两人一路走过酱菜园、南货店、槽坊(酒店)、小茶馆、混堂浜(浴室),走到“何氏门诊”门口时,备芳从善刚手里接过孩子,想进去。尽管孩子耳朵边的黄水疮已结痂,她还是想让本地中医名家何承志再给孩子看看。可何承志出诊了。何的徒弟看出,备芳与许多跨进这个门口的人一样,不想让他看病,只想让何承志看,就宽厚地笑笑,让备芳和善刚在一条黑漆长凳上坐下。
何的徒弟手拿竹夹,开始往一只布满折线纹的陶罐里放中药,淡淡的中药味飘过来。望着何的徒弟,善刚想,他一定以为我们是一家人。这么一想,善刚的鼻头就一酸。刚刚去备芳爷娘(父母)家时,备芳爷娘对他这个备芳新处的“男朋友”也很亲热。其实,假使一定要从男女方面说关系,他目前只是备芳一个锲而不舍的追求者。他也晓得,他的追求很无望,但是,有一种追求,时间长了,就为了追求而追求了。不过,善刚的追求很难讲一无所获,除了没有得到备芳结婚的承诺和关键的那种东西外,备芳把他从一名司机提拔成办公室主任,就不一定与他那种不弃不舍的追求没有关系了,而且,对善刚,备芳也已经时有亲昵举动,挽一下他的胳膊,牵一下他的手,抚摸一下他的脸,如此等等。备芳的亲昵动作一多,不知怎地,善刚得到的不再是甜蜜,而是委屈。特别是最近,有一趟,善刚去备芳的住所,当备芳叹息着抚摸他的脸颊时,他都想把脸转开了。可他忍着。备芳似乎望到了那种忍,望到了他压在心里的委屈,目光里露出一份怜惜,心里涌上一股愧疚——自己一直没有割舍一个男人固执的迷恋,却至今没让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想要的,不是办公室主任这一职位。他想要的,不是她不想给,是不能给。每次她想给时,大哥的脸就会出现在她眼门前。她晓得,幻觉中的大哥并不是要阻挡她做啥,现实中的大哥也不是这样的人,可为啥每当她想要对善刚“进一步”时,大哥的脸总要在她眼前出现呢?而且,备芳对善刚也不再瞒瞒藏藏,就是他想把脸转开的这次,备芳开口说,大哥是座山呢,隔在我和你当中。
备芳心里也清楚,她嘴里的大哥或许是另一个大哥,虽有着大哥的面目,却是另一个只存在于她心里的大哥。可不管哪能,心里的大哥终究还是来源于现实中的大哥,山一样耸着,挡隔在她的肉体和另一个男人的肉体之间。确实,优秀的男人是山,大哥是黄山——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她心中的这座“黄山”,似乎没有哪个男人有本事搬了去。可大哥却鼓励备芳去寻别的男人,说我要吃你的喜糖、红蛋呢!备芳开玩笑说,照这样说,你要经常送我喜糖吃,送我红蛋吃。备芳说罢,鼻头却一酸,双目潮湿,大哥则哈哈大笑起来。
善刚尽管平时不接触大哥,可也认得大哥。他喃喃回话,大哥这座山不是快要塌了吗?他的回话让备芳的身体一抖,她的手也从他的脸颊上移开。善刚说的是大哥失踪了三天的事。备芳对自己说,她心里的这座大山永远不会塌。
善刚从长凳上站起来,走到“何氏门诊”的门口,目光落在木柱下的支磉石上,想,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支磉石自然不会回答他,他就抬头,又转脸,见备芳正在低头亲怀里的孩子。他重新走进了店门,轻声对备芳说,不要拖了。
备芳抬头,目光有点诧异。这几日,变故多,连善刚这个平时对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的“好和头”也变了,会对她说不同意见了。可他说错了吗?没有,可以说是说到了备芳的心里。她是在拖。孩子耳朵边的黄水疮已好了,她却还把她抱进这个门诊店里,她这不是在拖,是在干吗?
善刚上前一步,又说,我们不是都觉得赚了吗?还多想啥?
善刚觉得自己说得很幽默,想笑,可望着备芳的脸色,只是牵了一下嘴角。两人都觉得赚了的感觉是在备芳爷娘家产生的。中午前,也就是备芳在告诉善刚她决定的、现在正拖着的这件事时,她突然提议,先去一下她爷娘家,让她爷娘看看这孩子。
当备芳抱着孩子,与善刚一前一后走在她爷娘家的场角上时,一种特别的感觉涌上心头,让她心暖,也让她心酸。见到父亲杨水根和弟弟备力时,她竟把头往善刚肩头上靠了靠。
杨水根和备力的表情一样,先是呆了呆,马上自然了,似乎还带上了一丝想掩饰的欣喜。见到备芳这个有过短暂婚姻的亲人,身边又有了一个人,两人立刻忙碌起来,又不晓得忙啥,就不停地搬凳,还把竹壳热水瓶拎来拎去。对于备芳怀抱里的孩子,他们已有心理准备,不过他们现在还是高兴,他们这时想做的,就是把这消息告诉备芳娘——她常年瘫在西厢房里的床上,可他们拖延着进西厢房。长久以来,他们已经有了个习惯,喜欢把高兴的事尽量在心里藏得久一点,再告诉别人。
那段短暂的婚姻结束后,备芳曾对她爷娘说,她想去抱养一个孩子。为啥要抱养?因为她很有可能不会再婚了。在说这话时,大哥的面庞却出现在她的脑子里,她委屈得想流泪。
乍一听她的话,杨水根、备力,包括瘫在床上的备芳娘,都很惊诧。不过,备芳当时已当上了一家国有公司的头儿,而且,她那样子,即便在娘家,都时不时地像领导了,她爷娘和备力都对她有点怯。他们还认为,备芳能当上领导,肯定在各方面有过人之处,这样,尽管他们在心里一时难以接受她的想法,可也没说出啥反对的话。
备力去了村头,没一歇,就拎回一条淀山湖白水鱼和几只河蚌,杨水根也从自留地上摘了一大把板叶荠菜,采了几只洋红番茄。在杨水根和备力准备中饭的时候,备芳抱着孩子去了她娘的床边,她代表孩子,对老人叫了一声“奶奶”,老人和孩子同时笑了,可备芳的嘴角一扭,像是要哭。她心里确实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是她娘枯瘦的脸上开心的表情让她想哭。后来吃饭的辰光,备芳想让备力把她娘抱到台子边一道吃。备力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备芳也不再说啥。
三个男人都不太会吃酒,可杨水根还是拿出了一瓶积满灰尘的特加饭,开了后,男人们都喝了一点。中饭临近结束时,备力用手背揩揩嘴巴,眼神突然凝住,望着客堂门外。见状,备芳也转脸,望到两个警察正走在门前的场地上。她猛地转回头来,脸上露出微笑,像是要宽慰别人,说,不要紧,让他们抄好了。杨水根说,抄?
备芳自知失言。警察是让她想到了大哥。其实,大哥的事,跟警察无关,他不是失踪在派出所,是失踪在本地的纪监部门。失踪是民间说法,其实应该叫留置。大哥留置在纪监部门已有三日,三日前,大哥曾打过她电话,说,有些东西,该毁掉的就毁掉,该转移的就转移。后来,两人间再也没有电话了,她打去几次,打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