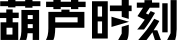做记者之前,牛姜一直认为自己颇具个性,做记者写了一年多采访稿,他不再这样认为了。这一年多他采访了太多堪称古怪的“个性之人”。同他们相比,自己只能算一个中规中矩的平庸之辈。高考的前一晚,妈妈让牛姜换上一条红色内裤,尽管他内心非常不乐意,最后还不是乖乖换上了。大学他看武侠谈恋爱打游戏,只因周遭人皆如此。毕业他听从老师建议,去了上海发展。他换了三回工作,最后应聘时尚杂志做记者至今。颇值得玩味的是,自从有了这个新的自我认识,牛姜的性格变得更加温柔和顺了,以至同居一年多的女友这天打电话提出分手,要去寻找新感觉,他当即表态支持,并不觉得这是在压抑自己。
牛姜下班回到两人租住的房子,看到敞开着的少了一大半衣服的衣柜,仿佛心里也失去了一大半内容。为了抵抗这种空落落的难过感觉,他趴到床上哭了起来。他试着争取让自己哭出声。他不久前从一本杂志上看到,遇到难过事不要强忍,大哭一场会好很多。他正哭着,来了个电话,同事老曹约他喝酒。他起身洗了把脸,提前半小时到达了小酒馆。
老曹晚来了十分钟。他眉头紧锁,一落座便解释他遇到了麻烦,老婆跟他闹情绪,抱着孩子回娘家了。老曹只顾自己倾诉,并没有察觉牛姜的面色比他还难看。
老曹说:“牛,其实我不应该把家庭垃圾往你脑袋里倒。”
“没事。”牛姜说,“我也只能陪你喝喝酒,实际帮不了你什么。”
“不,你可以帮我办件实事。”老曹说。
老曹有一个工作任务,去云南采访一位地方戏传人葛老师。家里突发变故,老曹没心情去了,想请牛姜替他完成。今天是八月十日,九月十日前交稿。
“八月二十日在维西县城有个汇报演出,各路戏曲舞蹈人马都参加,四川西藏的团队都会去,葛老师当然也会去,你就在那里采访他。采访结束了周遭游玩几天,领导那边我去说。”老曹说。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页剪报,递给牛姜,上面是关于葛老师的介绍资料。牛姜对照着扫了几眼,两张报纸大同小异,大概意思是十年前苏州的葛老师,抛下舒适的城市生活,来到云南深山,挖掘学习当地一种近乎失传的古老舞蹈——仙舞。葛老师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对仙舞进行了发展创新。葛老师不但爱上了仙舞,还爱上了当地的奇峰异水。他跳仙舞,唱山歌,准备永远留在山寨。
“牛,帮帮我吧!”老曹说。
“我文笔不好,达不到你的要求。”牛姜说。
“过谦了,牛,你有敏锐的感受力。带上部好相机,多拍些照片。这个题材冷门,到时候我帮你申请一个香港的艺术奖。”老曹说。
“我倒是对葛老师产生了兴趣,他所学的仙舞是摊戏吗?”牛姜说。
“不是摊戏,不是,也不是傩戏,就叫仙舞,仙舞不戴面具,更小众,但是越小众香港那边越感兴趣,他们从传教士写的资料中查到过仙舞,自那以后,再没有过对仙舞的介绍。牛,你这个写出来,不仅对仙舞,对当地,对杂志,对世界戏剧舞蹈史都有贡献。”老曹说。
“打住,大哥,我答应了。明天我回趟老家看看爷爷,爷爷病了。看过了爷爷,我就从南京飞大理。”牛姜说。
“谢谢,牛,我的好兄弟!你还记得浦东那个飞行迷吗?”老曹说,他端正了身体,往后靠到座椅靠背上。
“我采访过的人物还能不记得?他不也是你介绍给我的吗?”牛姜说。
“直觉告诉我,葛老师跟飞行迷不同,葛老师不会是那种滥竽充数之辈。”老曹说。
老曹说的那位飞行迷,接受过牛姜采访后,还经常来找牛姜,把一些新冒的奇思异想说出来,依然激情四射,唾沫横飞。飞行迷遇事积极进取,没有牛姜采访这类人所惯有的抑郁特征,不摆那种爱谁谁的冷傲劲儿。最近一次飞行迷来找牛姜,对牛姜说,他已经去上海吉尼斯总部咨询过了,只要有清晰的录相,他的壮举百分之百可以申请通过:从昆虫空中交配受到启发,飞行迷计划跟他女朋友,背着降落伞,在空中完成一次完整的性行为,牛姜负责全程拍摄。
飞行迷兴致勃勃许诺牛姜,学习跳伞的费用,由他负责。
牛姜哈哈大笑,回去讲给女友听,女友冷冷地回了一句话,让他无言以对。
女友说:“我闺蜜的男友考虑升职买房财务自由,你却整天结识些无聊阿乌卵。”
同样意思的话爷爷早就说过。牛姜打小爱跟一些画画的、写诗写小说的人交往,有一次,爷爷盯着他,语重心长说,“会交朋友交铁匠木匠,不会交朋友交道士和尚。”
在爷爷眼里,道士和尚是好吃懒做、光说不练的代表,比阿乌卵强不了多少。
牛姜匆匆赶回徐州见了爷爷最后一面。爷爷病床旁边站着一堆亲人。牛姜的爸爸妈妈把儿子拉到跟前,大声喊二孙子回来了,爷爷眼珠似乎微微动了一下,不知还有没有意识。最后大伯用手把爷爷的眼睛合上。
葬礼由爷爷的大孙子,市招商办的副主任,牛姜的堂哥一手主持操办。堂哥能力强,朋友多,场面上的事整得明明白白,相比之下牛姜非常寒碜,没有一个朋友来助阵。其实他也要脸,感觉没有朋友撑场面不体面,就给四个朋友打了电话,平常他跟他们联系最多。他先打给了一个写小说的朋友,他没接电话,牛姜发了个短信过去,“爷爷去世,后天火化,早七点在五号告别厅。”短信没有回。第二个电话他打给了画画的朋友,朋友接了,听后沉吟了半晌,告诉他去不了,后天他去外地,具体哪里不一定,但肯定不在徐州。第三个打给的是一位独立导演,导演责问他为什么不早点说,他已另有约定,如果昨天通知还赶趟,今天不能了。牛姜说昨天爷爷还活着呢。导演深表遗憾,定好了要去扬州试女主角骑马的戏。第四个电话牛姜没有勇气打了,他犹豫半天,给他的诗人朋友发了个短信。还得说诗人朋友讲究,很快回了短信。诗人正在新疆天山采风,将马上回乌鲁木齐,到乌鲁木齐后再买机票往回赶,他估算过了,差不多后天中午能赶上午饭。牛姜回短信,那就不麻烦他了。

葬礼上,爷爷的其他孙子外孙辈都有朋友带着车来,唯独牛姜,孤零零一人。妈妈悄悄问他,女朋友呢?他告诉妈妈,他们分手了。
吃席时他跟堂哥和堂哥的朋友一桌。牛姜简单夹了两筷子起身告辞。堂哥说还没介绍呢。于是他把堂弟升了两格,以编辑部主任的身份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然后再把他的朋友介绍给牛姜,都是各行各业有头有脸的人物,牛姜嘴上喊久仰,实际没往心里去,只是当介绍到一位来自云南的客人,一位开矿老板的时候,他才正眼看了看对方。那人跟他年纪差不多,身材敦实,皮肤较黑,小小的眼睛看人时含着笑,给人的感觉却干练狠辣。
云南客人说:“欢迎随时到我们云南。全省我都可以安排接待,一句话的事。”
牛姜一激动,差一点把他明天一早就要飞大理的事说出口,但他忍下了,他觉得那样更麻烦,不如独来独往的好。
云南客人说:“你要是往深处走,到我老家转转,那就方便多了,跟到了家一样。我带你进山,给你头人的规格。”
大家哄堂大笑,牛姜跟着咧了咧嘴,心想他爱咋吹咋吹,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次日,牛姜跟父母道别,飞往大理。临别前劝慰了父亲两句,父亲刚刚失去他的父亲,意志有一点脆弱,只跟儿子握了握手,没有说什么。以往跟儿子分别,他总要嗦好些人生大道理。
到达大理,牛姜没有停歇,坐客车去了维西。
在维西民族体育场附近,牛姜找了个旅馆住下。他躺在床上给老曹发了个短信,“宿维西,明天看葛老师演出。”
第二天牛姜匆匆吃过早餐,直奔体育场。体育场正门上方挂着一条横幅,“二○○八年云贵川藏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歌舞演出汇报大会”,牛姜亮出记者证,进到接待楼贵宾区。他一间一间按照门牌指示寻找,找到了葛老师所在的19号室,门是开着的,屋内坐着站着十来个人。
牛姜判断,这十来个人是来采访葛老师的记者,但葛老师并不在此处。
牛姜想跟同行们打个招呼,没等开口,有人喊了他的名字。那人坐在里面,穿着打扮很有品味,牛姜一进门首先注意到的人就是他,只是没有认出来他是谁。
“牛老师。”那人说。
“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牛姜这才认出来他是北京某报的记者,他们在一次采访中相识,事后还喝了一顿酒,但实在想不起来他叫什么。
“对,邵揶。”邵揶看出来牛姜的尴尬,“牛老师也来采访葛老师了?”
“是啊,老邵。”牛姜佩服对方的机智,顺着他的话说,“我专为葛老师来的。”
引来屋内其他人一阵哄笑。
牛姜不知所以。
邵揶说:“那你请回吧,刚才组委会来通知,葛老师的舞伴半途突患急症,葛老师带她求医,赶不过来了。”
“苦也。”面对这个突变,牛姜没有丝毫准备,他转身退到走廊,给老曹打去电话。
老曹倒是沉着,他说反正已经到维西了,能找到葛老师最好,葛老师没来,采访一些了解葛老师的人,凑成一篇稿也可以。
“要不要换一个人,这里有好多表演团体。”牛姜说。
“不,只写葛老师。”老曹说。
牛姜再回到房间,好多人已经离开了,只有邵揶在等他。
牛姜说:“还是那个电话呗,晚上我们再约。我去组委会要一点葛老师的资料,然后观看一下演出,晚上我约你,喝点酒。”
“好的,还是那个号码,晚上联系。”邵揶说。
牛姜从组委会要了一些葛老师的资料,比剪报内容并没有多多少。葛老师全名葛存正,一九七○年出生。牛姜开始以为是位老先生呢,原来只比自己大十来岁。葛存正来边区义务支教,迷上了当地戏曲,他们称为仙舞。后来葛老师跟了一个剧团,边学习边演出,一待就是十多年。
牛姜把葛老师获过的一些奖项,拍了下来,以备后续整理。他觉得这一点点收获根本对不住机票钱,就以唠家常的口吻,询问接待他的会务小姐还有没有其他跟葛老师有关的内容,小道消息也行。会务小姐摇摇头。一旁的一位中年男子朝牛姜招了招手,牛姜立马去到他身旁。组委会的人都穿着少数民族服饰,唯独这位中年男子身着西装。西服男小声说:“你打车去长途客运站,应该还来得及。葛老师的前妻领着两个孩子刚从这里离开,他们来找葛老师,跟你一样,也白来一趟。”
“她叫什么,长什么模样?”牛姜直起身。
西服男说:“不用管她叫什么,你只要赶得上就认得出来,她跟两个孩子都穿红罩衣,戴着高冠帽子。她已经再嫁,住在镇里,每年汇报演出,她都会带着孩子来看葛老师,两个孩子一年里只见爸爸这一次。葛老师的趣闻轶事多的是,但最好还是问他的前妻。”
牛姜赶忙往楼外跑,招手一辆拉客的微型车,没讲价就上了车。
“去长途客运站。”
车子开动后司机才说:“六块。”
“八块,只要快。”
司机左拐右突,把他送到了客运站。他在客运站大门口追上了红衣公主和两位王子。组委会人员说得对,千万人当中,绝对不会认错,三个人打扮得鲜艳夺目,光彩照人。
“你好,耽误你几分钟。”牛姜递上名片。
高个子红衣公主没有接。
她身旁一左一右站着两个黑皮肤、双眼放着精光的小王子,其中较大一位,有八九岁左右,弟弟比他矮一个头,小个四五岁。弟弟伸手要接名片,被哥哥后发先至接了过去。
“妈妈,牛。”哥哥瞅着名片说,看样子他识字。
“旱牛还是水牛,小牛还是老牛?”弟弟跺着脚问。
红衣公主开口说话,她叽里咕噜说了一堆方言,牛姜虽一句也没有听懂,但心想只要能开口就有机会,他赶快表明来意。他说,他是葛老师的崇拜者,他想从她这儿了解一些葛老师的事迹。
红衣公主不会听不懂他的话,但她不动声色,继续用方言说了一串。
“我妈妈不接受访问。”王子哥哥翻译说。
“对,我亲哥说得对。我葛阿爸也不接受。”王子弟弟说。
红衣公主点点头,拉起两位王子的手就要离开。
从此刻起,写葛老师这件事已经不仅是杂志的公事和朋友间的私事,而是成了牛姜自己非要做成的一件大事,神秘的使命感和莫名的责任感促使他下决心必须把它做完美了。他承认自己不务实,但他不承认自己是阿乌卵,或者说哪怕自己可能是阿乌卵,但他并不心甘情愿。
牛姜按下挂在胸前的相机的快门,眼望红衣公主说:“请帮我一下忙,我想把葛老师深度报道出来,给全世界人们看。”
真挚是伪装不出来的,牛姜的急切模样红衣公主看在眼里,她改用普通话说:“我们要上车了。你去螺螺寨,葛老师的女主角应该在那里治病。论亲戚她是我的小表妹。现在是九月,晚上的风凉下来了,我们家族的女性会受病,一种怪病,这种病医院治不了,只有螺螺寨的罗神医能治。你询问螺螺寨大家都知道,不过路可不好走。”
“谢谢。”牛姜目送红衣公主翩然离去,“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老大老二都是葛老师的孩子吗?”
“我是。”王子哥哥说。
“我不是。”王子弟弟说。
“对的,弟弟是我跟现在的丈夫生的。”红衣公主回答,“把葛老师写得好一点,他是我们仙舞的灵魂。”
王子哥哥转头,向着牛姜拍了拍腰部。
“如果你敢污蔑造谣,柴刀跟你讲话。”王子哥哥说。
“铁拳伺候。”王子弟弟举了举拳头。
红衣公主说了几句方言,拉着两个儿子进到了检票口。
这么美的妻子,这么好的儿子,葛老师怎么舍得离婚呢?仙舞值得他如此奋不顾身,还是另有原因?女演员小表妹是怎么回事?一大串问题在牛姜的脑海里翻滚增殖。
晚上跟邵揶喝酒的时候,牛姜不断把话题从薪酬房子往葛老师身上引,希望能从邵揶那里获取一点内容,可是收获甚微。邵揶对葛老师知之甚少,说出来的点滴,也是白天偶然听来的。他告诉牛姜,葛老师喜欢年轻的女演员,有点像电影导演,其实这也无可厚非,选择漂亮女演员是仙舞的一部分。
回旅馆躺在床上,牛姜思量明天要不要真的去螺螺寨。冲动已经降温,没有在客运站那么强烈了。他给老曹打去电话,把情况简单交待了。老曹支支吾吾,说怎么都可以,螺螺寨可去可不去,让牛姜自己定,文章允许自由发挥,加一点想象夸张,多排列一些形容词副词,足可以交差。他并不想让牛姜为了一篇文章吃太多的苦。
牛姜问:“老曹,换了你,你会不会去螺螺寨?”
“会去。”电话那头的老曹这回没有犹豫,“因为葛老师让我产生兴趣,我们周围没有这种人,而且我对西南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着迷了好多年了。要不是家里有急事,我不会麻烦你。”
“明白了。”牛姜说。
“你可以周围玩一玩,当旅游了。”
第二天早晨牛姜退了房,叫了辆拉客的车。
“去螺螺寨多少钱?”他问司机。
“到不了螺螺寨。”司机说。
“我知道。开到最近位置就行。”牛姜说。
“按公里数算吧,不多要你,昨天你多给了。”司机始终歪着脖子。
真巧,这是昨天拉过他的那位司机。
牛姜端量了一下司机,他四十多岁,可能颈椎不好,一直歪着脖子,他下车打开后备厢时,身体也是歪着的,看样子腰椎也不太好。但开起车来却像个赛车手,反应迅捷,动作灵巧。遇到前方修路塞车,他见缝插针,不断往前插,直到塞得死死的,一点缝隙也没有了。司机拉下手刹,歪着身子下了车,他下到了路旁的玉米地,玉米地里有一条不显眼的小路,他沿着小路往里走,我以为他要方便,可他迅速返回到车上。
车子没熄火呢,他直接拐进了玉米地,玉米已经收完了,剩下些耷拉着叶子的玉米秆。玉米秆不断擦到车身,司机毫不在意,开了有十几分钟,他又并上了大路,已经绕过了堵车路段。牛姜非常佩服这位大哥的车技,无论哪一行,只要是行家,都会得到他的尊重。
一边开车,司机一边跟牛姜闲聊。当他得知牛姜来自上海,便不无得意地告诉牛姜,他的儿子在上海读大一。
牛姜问他哪个大学。
“交大。”司机说。
“我说你一提儿子满脸都是骄傲呢。交大,那很厉害。你培养得不错。”牛姜说。
“还真没怎么操心,都是他自己努力的。孩子懂事,所以我没白没黑地干活赚钱么。要是儿子将来能留在上海,买房咱买不起,租房也得花不少钱呢。你,买房了吧?”司机说。
“还有多远?”牛姜说。
“快到了。”司机拐上一个通往一处高地的土路,一直开到了无路可开。
“下车。”司机说。
他弯着腰,歪着脖子,打开后备厢,把牛姜的背包拿出来交给牛姜,又从里面拽出一辆折叠的小自行车,打开来支在一旁。他折断几根树杈,放到车尾处,然后推着自行车退出来,这样你在远处,若不仔细观察,还真发现不了树丛中有一辆出租车。
牛姜疑惑地问:“大哥,你这是要?”
司机说:“不会多收你钱。下面的路,我免费赠送。上车。”
司机跨在自行车上,他往前挪动挪动,好让后座的空间大一点。
牛姜问:“螺螺寨还有多远?”
司机说:“不远,但容易迷路。我载你到能看到它的地方。”
司机摸出一个小通讯录和一支签字笔,说:“你要是信得过我,留个电话。你放心,没事我不打扰你,除非儿子那边有什么重要事情,需要咨询的时候,我才会打给你。你要是不愿意,我不强求。”
牛姜给他留了电话,坐到了他的小自行车上。
司机载着他往山下冲去。想不到这小车还这么结实抗造。
到了坡底,又颠簸着骑了一段路,司机停下。
他往低矮处一指,山峰绿树间,隐隐约约确有一个村寨。
“那就是螺螺寨。这是最近的路。你从这里往下走,方向一定别弄偏了,一会儿走到下面,就看不到寨子了,别迷路,看看太阳的位置。”
牛姜谢过了司机,背着包往下走去。
司机在身后说:“要是能定准了哪天回,我来这里接你。”
“定不了。”牛姜脚一滑,差一点摔倒。
“慢点,牛老师!”
上山容易下山难,牛姜庆幸出发前换上了一双丹纳登山鞋,不然脚脖子得崴多少回了。走到望得见村寨楼顶的位置,他坐下来,喝了几口水,吃了一个面包,休息了一会儿,起身继续前行。他知道,再往下走,就会看不到寨子,只能看见树、天空和山尖,很容易迷路。
在潮湿阴暗的林荫中穿行,他越走越心虚,有几处岔路,他必须做出选择,每次都是模棱两可。忽然,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锣鼓乐,校正了他的方向。锣鼓乐伴着人们的吆喝声,女声和童声的歌唱声,越来越清晰,说明他走对了。再往前走了一段,听得出锣鼓乐是从录音机里放出来的。
牛姜从山路并入了村路,螺螺寨终于到了,但愿葛老师还在这里。
寨子中间有块平坦地,一位姑娘带着一群小孩跳舞,寨民在围观。
姑娘领舞,边跳边唱歌,发现小朋友跟不上节奏,她就顿一下脚,把刚才的舞蹈动作重新来一次。
寨民发觉来了个外人,纷纷转头看牛姜。两个小男孩试探性地跑向牛姜,距他两步近位置,刹住车,然后快速折返,见牛姜站着没动,再次前冲,笑意从他们的眼睛涌到脸上。
牛姜眼前一亮,好久没有看到这般纯净的笑容了。
领舞女孩去到地上的录音机旁,换了一盘磁带。
一首熟悉的曲调响起,领舞女孩开口唱了起来。刚才跟着她跳舞的孩童退到周边,拍着手打拍子。
……歌声使我迷了路
我从山坡滚下
女孩唱到这里,调皮地瞅了牛姜一眼,牛姜赶快拍打了几下裤腿,他在下山时摔倒多次,裤腿又湿又脏。
今天晚上请你过河到我家
哎呀呀
我们相依歌唱在树下
姑娘大方地向牛姜伸出双手,邀请他上前。
牛姜扭扭捏捏。
两个小男孩从后面推他的大腿,把他推到了她的跟前。
这下牛姜像被启动了开关,开口唱了起来。他跟着她的调,一起把这首歌唱完整了。
喂饱你的马儿带上你的冬不拉
等那月儿升上来拨动你的琴弦
等那月儿升上来拨动你的琴弦
哎呀呀
我们相依歌唱在树下。
唱到最后一句,她头向牛姜这边象征性地一偏。
“啊!啊!”旁边有人哑巴一样喊了两声。
“阿璎姐!阿璎姐!”孩子们跟着提醒有人喊她。
“来了!”姑娘回答。她关掉录音机,提起来,离开了场地。
那个“啊啊”的哑巴站在不远处,拄着拐杖,冷冰冰地注视着牛姜。
阿璎走到他跟前,扶着他的胳臂,一同走了。他的腿有毛病,走路一瘸一拐。
牛姜问身旁的一个小男孩这人是谁,是她阿爸吗。
“葛老师不认识?大名鼎鼎的葛老师。”
牛姜赶快打开相机,拍了几张两人的背影。
在一个木栅栏大院门口,牛姜追上了他们。
牛姜说:“葛老师好!我是来采访民舞大会的记者,专程来采访您的,我从维西翻山越岭,终于找到您了。”
葛老师用拐杖一划拉,让牛姜走开。牛姜站在原地,眼看着葛老师推开院门,走进了院子。这是一栋村寨里少有的带院子的房子,葛老师等阿璎进院,回手关上院门,把牛姜关在院外面发愣。
“他听不懂我的话?不能啊。”牛姜想。
在门关上之前,阿璎回头望了牛姜一眼,快速转回去,很害怕葛老师的样子。
牛姜不能硬往门里闯,他询问一路跟着跑的两个小男孩,让他们带路去找支书。
两个小孩蹦蹦跳跳,带着他来到一栋竹楼前。一个小男孩双手做喇叭状,用土话从楼里喊出来一个六十左右的老者。
牛姜主动上前做了自我介绍,同时递上自己的名片。
老者把名片拿在手里,认真聆听牛姜的话。
牛姜说明了来意,他有意强调了“民族艺术”“走向世界”等词汇。平时他不这样讲话的,听都不爱听,但很奇怪,到了需要运用的时候,张口即来。
这套话术果然有效,面无表情的老者变得热情起来了。
老者说:“我这就带你去,大上海的记者来采访了,必须认真接待。我让葛老师开门,后面的事就靠你自己了,葛老师不是螺螺寨的。我不能下命令。但他住在这儿,就得给我开门。”
牛姜说:“开门就行,你为我引见一下,剩下的我来。他为什么不欢迎采访?”
老者说:“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不过平常葛老师就不怎么爱讲话。牛记者,你在螺螺寨能待几天?晚上住在我这里吧。”
牛姜说:“谢谢,太好了,住个一两天,采访完葛老师我就走。咱们现在就去找葛老师怎么样?我怕葛老师离开螺螺寨。”
“不能,他的腿伤还没好呢,走不了山路。”老者说。
牛姜说:“我在维西听说,女演员病了,葛老师才没去成演出大会。”
老者说:“阿璎吗?她确实病了,老毛病,吃了我的两副药就好了。”
“你就是罗神医?”牛姜说。
“不敢,不敢,祖先传下来几个灵验方子。阿璎住的那个寨子,叫铜铁寨,比我螺螺寨大多了。铜铁寨在铜铁山里,用脚走的话,离这里两天的路。铜铁山里出铜铁,铜铁寨里出美人,不过铜铁寨的美人受了诅咒,好几辈子了,她们容易得一种怪病,每年过了夏天,都要发作一次,两只胳膊肿胀得像腿那么粗,皮肤肿成了一张透明的薄膜,耽误太多事了。这几年,山里寨子的女娃学男娃,去城里打工,铜铁寨里的女娃出不去,这病去不了根。”
牛姜好奇地问:“那你是用什么治?”
罗神医说:“草药,蒸蒸晒晒,配药时念咒唱曲。我家婆子配药,我是党员,不搞迷信。我负责上山采药。”
牛姜说:“属于巫医范畴。”
罗神医说:“随便叫什么,管用就行。”
牛姜问:“这就走吧,边走边给我讲讲葛老师。”
葛老师苏州人,多才多艺,二十多岁时自愿支教到铜铁寨当老师。铜铁寨是仙舞的大本营,葛老师喜爱上了仙舞。仙舞在当地叫鬼舞,鬼字本没有贬意,城里的文化人觉得不好听,改叫仙舞。改了也就改了,山里人跟着叫仙舞,仙舞鬼舞,只是叫法不同,内容没变。葛老师不像其他支教老师,下来只是锻炼体验一下,时间一到都回城了。葛老师不回去,甘愿留在山寨,后来他娶了铜铁寨最漂亮的姑娘阿红为妻。他们夫妻有矛盾是很久以后的事情,阿红想搬去镇上住,葛老师喜爱上山下涧,到各寨子跳仙舞。
“不过,寨子里的年轻人反倒不怎么爱这个了。”罗神医叹了口气。
“他们舞团只有葛老师和阿璎两个人?”牛姜问。
“是的,只有他们两个人,不需要伴奏。随便到哪个寨子都能找个人敲竹筒竹板,葛老师可以边敲鼓边跳舞。跳双人舞时,可以放录音机。葛老师和阿璎跳的仙舞,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好的仙舞,比跟阿玉跳得还好。阿璎有文化,在镇上上过学。”
“阿玉是谁?”牛姜问。
“也是葛老师的舞伴。”罗神医说。
他们来到了院子门前。
“阿璎,开门,是我。”罗神医拍拍门,竹门虚掩着,朝里推开了。
他们进到屋内,空无一人。
罗神医转了一圈,说:“自行车行李呢?都不在了。这事只有葛老师做得出来,不告而别了。”
“我得追去。”牛姜慌了。
罗神医带着牛姜往寨口赶。罗神医跑起来,速度比牛姜还快,边跑边说:“跟上,跟上我!怎么了,年纪轻轻的?加快速度,葛老师腿伤还没好利索,跑不多远,我们追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