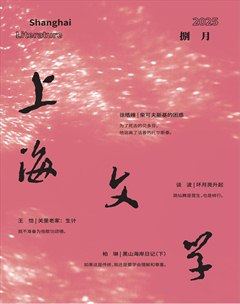一、神思——柴可夫斯基的困惑、警匪片与《乞力马扎罗的雪》、伦勃朗与《文心雕龙》、福楼拜差评第三卷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言,曾几何时,海明威对我们一代,是个神。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神,曾几何时,托尔斯泰对于柴可夫斯基,是个神。他出现在柴可夫斯基作品演奏会,听哭了,令柴可夫斯基忐忑,神为我落泪,我何德何能。
一八九三年,柴可夫斯基去世,托尔斯泰给妻子写信:“他跟我的心贴得多么近。”
柴可夫斯基生前给金主梅克夫人写信:“我确信,托尔斯泰是个有点反常的人,与他结识没给我带来任何东西,就像所有的结识一样。”
那场演出后,两人见面没聊好。
柴可夫斯基受不了托尔斯泰将交响乐划分为好典范的“莫扎特—海顿”系列,与坏典范的“贝多芬—舒曼”系列。托翁将老柴列为莫扎特系列,老柴还是受不了贝多芬遭贬,向梅克夫人吐槽:“把举世公认的天才降低到自己理解的程度,是低能者行为。”
为了死去的贝多芬,他远离了活着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论艺术》,是他招艺术家反感的集大成。劝青年学子,每当事业萎靡,心情沮丧,就去读此书,慨叹审美、思考均差之人,却写出了欧美排名第一的小说。
那我们呢?
非常励志。
卡尔维诺认为《乞力马扎罗的雪》糟透了,不伤感的海明威,才是他的神。
海明威佳作,不直接写死亡与虚无,人物是技术控,内行的钓鱼、斗牛、炸桥、造爱,高度专注于自身行为。人物如一条脱水后扑腾的鱼,越积极,死亡与虚无越彰显。
从一项技术上找自尊,进而发明出个人道德,之后为恪守道德,全然违反技术指标,是海明威式硬汉。
《老人与海》中,老人多日捕不到鱼,依旧得意于自己技术一流,只是运气差,捕到大鱼后,遭鲨鱼抢食。放任鲨鱼,以求安全回岸,是技术角度的正确选择,但他拿船桨当武器,跟鲨鱼搏斗了。
一个技术主义者不要了技术。
一九九五年的《盗火线》,今日是警匪片经典。当年面世,我们一代上大学,观感差,好莱坞俗套剧作法,为了担纲动作戏的警察男主不单调,给他添加中年危机,如此套路已看腻。
还好此片是双男主,另一男主是盗匪,明明可以逃脱法网携女友远走高飞,却非要处死一个向警局出卖同伙的内奸。该走不走,结果走不了,被警方击毙。
影片开局,表现他是一个极端技术主义者,比所有同伙专业,反复斟酌计划,有漏洞即不实行,一遇意外,便断然终止整个行动。但他在惩罚内奸和逃脱法网之间选择了前者!
惩罚内奸是道德,逃脱法网是技术,他选择了道德,犹如拿船桨打鲨鱼的老头。
观众扼腕叹息,先逃了保命,时过境迁再回来惩罚内奸,不好么?但还是为他的鲁莽而激动。一流文学在三流电影里打折得不剩什么了,影院里依然力量巨大。
男生成长,都会诋毁自己一度的神,卡尔维诺一度批评海明威文风矫饰,甚至觉得活得也矫情,对他狩猎冒险的新闻报道,听厌了。
选择崇拜一个偶像,为提升自己;否定偶像,也是为提升自己。海明威对托尔斯泰,没反复,青春至死都尊崇。理由之一,是同样写战争,自己写不过人家。海明威宣称自己写过了司汤达,毛姆随海明威,也宣称自己写过了司汤达,司汤达真是个悲催的存在。
毛姆认为伯爵级别的高等贵族并不产生艺术家,出个托尔斯泰,奇了怪。西方贵族扶持艺术,自己不做,艺人是一个固化小圈子,平民进不去,贵族耻于进。
东方相反,上流社会才出艺术家。王安石出身平民,散文列入唐宋八大家,这怎么算?
他是北宋丞相。
写出千古文艺理论《文心雕龙》的刘勰是穷孩子,年轻娶不起妻,虽然血统属下等贵族。父亲一代垮的,以北京的前清贵族为例,一代垮了,这家人便垮了,祖辈的审美和见识延续不下来,再交不到高阶层朋友,张口一聊,别人观感差,便不会带他玩了。
差着阶层,便差着审美与知识,现实如此残酷,刘勰凭什么点评文艺?之前写文艺理论的名家,曹丕是皇帝,陆机是侯爵。
刘勰三十七岁写完《文心雕龙》,拦南梁开国功臣沈约的马车献上,街头商贩行径,为贵族圈不齿。
下层人猜上层事,估计沈约看了心里乐。比如《文心雕龙》说诗文可通军事,写着写着,自然懂。司马相如诗文名动天下,但他写文没通军事,智慧未开,致使文也不行,止步于词藻华丽,内行人看不是一流。
我看着都乐,可想把沈约逗成啥样。
明朝王阳明、晚清曾国藩为文武全才,诗文是专门学的,军事也是专门学的,刘勰见解,相当于只看到一个人上了鲁迅文学院进修班,不知他是军事学院本科生。
沈约为《文心雕龙》站台,宣传得天下闻名,意义应不在文艺。捧一个小官低见,混淆视听,应是某种政治企图,难道为搞傻贵族?
是我大学时的见解。
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两年,拍专题片遇上位北大附属医院的老中医,会古琴、武当剑、太极拳、书法、藏区学术,还有《西游记》唐僧原型玄奘从印度取回的唯识学,哪一样都够我学一辈子。
学中医,是先学会做菜,才学上。他年少在医馆当制药小工,问诊开方子不会教小工,见少东家是美食家,他就学了做菜,以美食换教学。
我说那可费劲了,您还得学做菜。
他说不费劲,许多事我是一看就会,别人显示个基本,我自己能发明,就会做菜了。我质疑,少东家从小好吃好喝,您是穷孩子,从小没吃过什么,能让他贪嘴您做的菜,难度太大。
他说生手到高手,时间很短,我还得学医呢,不能在学做菜上耽误时间。他一生所学,有的甚至没开始学,似乎就懂了一半。
有真人为例,才知“文学通军事”的说法,在高智商者有可能。认为刘勰可笑,因我智商低。
大学毕业十八年,又遇上例子,一位中文专业的同龄人,办金融班。讲不了金融专业课,讲的是金融的“心法”,赚的比他在杂志社、网站供职的文学系同学多得多。
生源是企业家的夫人们,据说招生标准是老公资产不低于十亿,刚过亿,不好意思进班。智商真高。
托尔斯泰智商不高。
专注,也可发生神思。
柴可夫斯基年少即看托尔斯泰小说,觉得他把人写透了,此种洞察力等于神。接到托尔斯泰写给他的字条,说喜欢你音乐,要见面。他怯场,认为到了托翁面前,还不给一下看透了?自己作为一个人,没秘密了,实在无法忍受。
神要见,不能不见,老柴做出了自己会失态崩溃的准备。等见面,发现托尔斯泰对他没有洞察力,一场尬聊。《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是这人写的吗?对老柴,是不解之谜。
我们这代人熟悉托翁一个烂大街的典故。写《安娜·卡列尼娜》时,夫人发现他哭得不行,说安娜要自杀了。夫人劝,死活不全凭你一支笔吗?不让她死不就行啦,别把自己搞得这么难过。他说不不,是她要死,我拦不住。
这种“让人物自己说话、自己行动,作家不干涉人物命运”的文学理念,小孩时听着很对,等我开始写作,发现没法操作,还是要靠主观设计,人物本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不存在“不干涉人物命运”的情况。
所以托翁的说法,不是正经话?
作家煞费苦心建立人物行为逻辑,后面写就省事了,按逻辑顺下来就行了,说是“不干涉人物命运”,是自夸起初设计得好——如此理解了很多年,一日突发奇想,托翁跟夫人讲述的,会不会并不是文学理念,而是写作状态?
去查《文心雕龙》,其《神思篇》写道:“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还有一句“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
睡眠有梦,写作入迷时有神乎其神之思,打破时空观念,超越个人生活经验,之前不知的也知了。
托翁写安娜,其性质,等同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萨满招魂。
刘勰父辈没落,等同平民,他搞文艺评论,可理解。托尔斯泰属高等贵族,分的遗产厚,自己还会赚钱,明确是富豪,怎么也轮不到他搞艺术。
他虽富有,仍是没落贵族。贵族除了爵位还有官阶,爵位高,官阶低,便是远离了贵族核心圈子。一些世交爵爷们办的沙龙,还进得去,闲聊、跳舞而已,而贵族核心圈的军政信息,已对他们屏蔽。
海明威写“一战”,是基层体验,没上层信息源,不知“一战”究竟发生了什么,因而迷惘。托尔斯泰年轻时参加过俄、英、法争霸的克里米亚战争,是下等军官,视野局限,比海明威强点,强不到哪儿去。
他的两个哥哥官阶也一般,提供不了什么,至于到档案室、图书馆搜史料,别人也能搜,不具优势。毕竟是贵族子弟,小时候多少听到点祖辈口传,凭的是这吧?
这种老话,按北京人经验,不能信。你家已脱离贵族核心圈二三代,语境不熟了,光听老话,会理解错。在现实层面上,托翁不具备写《战争与和平》的条件。
但他进入神思状态,达到“物无隐貌”之境,盘活祖辈老话和图书馆报刊,不知也知了。
《文心雕龙》披露,屈原从小嘴笨,所以别人看他,都不认为有才华,但屈原专注,发生神思现象,嘴笨之人写出妙语。
德国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加印九十余次的畅销书《教育家伦勃朗》,讲伦勃朗通过画画,对宗教、政治、经济、心理学全通,并对两百年后的德国发展提出纲领性意见,隐在《夜巡》一画中。作者引用尼采理论:“通过艺术直观感受获得的洞见,远高于科学研究推导出来的学问”。
是西方描述的神思现象。
“二战”结束后,伦勃朗的神思色彩被抹去,普遍称他只是个画家,不再是德国人,又成了荷兰人。伦勃朗以自画像闻名,之前德国政要说一看就是德国人的脸,荷兰政要附和,说太对了。
当代例子,是一九九二年轰动世界的《野兽之夜》导演西里尔·科拉尔。之前是个业内常见的混不出头的年轻人,新秀都不算,演员、摄影、导演都干,十年无起色。得了艾滋病,临死前超水平发挥,庸材变天才,拍出名片。
你勤学苦练,博览群书,每个演出都看、每个艺术家讲座都听,结果一个不读书、混日子的烂人,不知受了什么刺激,神思开启,一下超过你。
他成名后当渣男、坑合作者钱,风评日差,即将恶贯满盈,但一拍片,还是比你强。柴可夫斯基对托尔斯泰本人简直是反感,但还是被他小说吓得灵魂颤栗。
因为有神思现象,努力与成果不成正比,所以学艺术很冤。
《战争与和平》,海明威一类平民出身的作家群叹自己写不了,输在生活背景。其实是“这山望着那山高”,高看了托翁。
贵族中亦差距巨大,晚清北京城中皇亲国戚、名臣后裔多,大多闲人,逢当军政事变,茫然不知,比平民见识强点,是订了英文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