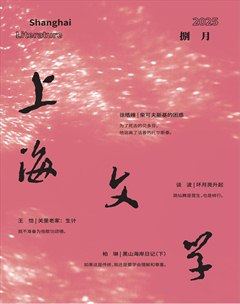相轻与相重
建安“三曹”,记得曹操歌咏的雄浑苍劲,记得曹植文采的风流倜傥,只记得曹丕“典论”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几近毒舌。嫉妒是普遍人性,岂独文人然。与曹植争太子,曹丕笼络文人,并无“文人相轻”一说。一旦上位,便逼老弟凄凄惨惨七步成诗。所谓“文人相轻”,不过是个雅致的借口。
深究这些,意思不大,莫如感知文人世界其实一直存在的温暖。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漫游中相遇于洛阳,从此结下一辈子的交情。
随后李杜三次同行:一起游梁宋,在太行山访仙问道,遇到边塞诗人高适。次年又相约游东鲁,寻找隐士高人。
李白交际广泛,但对小自己十一岁的杜甫格外看重: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没几天,就想起“何时”“金樽开”。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
一喝酒就想起上次杜甫喝得大醉。思念滔滔不绝犹如汶水。
杜甫更倾心: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
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冬日有怀李白》)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梦李白》二首其一)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梦李白》二首其二)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不见》)
杜甫共为李白赋诗十五首。春日,冬日,获罪,流放,李白永远在杜甫梦中。
李白和杜甫,是文人相重的典范。后世诗人学者闻一多由衷赞美:“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了。”(《杜甫》)
已入暮年的贺知章,读到李白的《蜀道难》,瞬间被磅礴的气势、奇诡的想象震撼。长安见面,不顾自己的高龄与身份,直呼李白为“谪仙人”,随后解下腰间的金龟饰,换来美酒与李白同醉。贺知章去世后,李白独自饮酒,想到当年的金龟换酒,不禁潸然: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李白与贺知章的忘年交,如同一坛陈酿,越久越香。
刘禹锡与柳宗元同中进士,自此命运交织。
两人积极参与的“永贞革新”,仅仅持续了一百多天便告失败。两人一同被贬。流放地相隔千里,两人一直书信往来,遥寄思念。
十年后,被召回京城,却再次双双被贬:刘禹锡贬播州,柳宗元贬柳州。柳宗元得知播州偏远且困苦,而且刘禹锡的母亲年事已高,便冒着生命危险上书请求与刘禹锡对换贬谪之地,表示即使罪加一等也无怨无悔。朝廷为其所动,更改刘禹锡任连州刺史。
四年后,柳宗元病逝柳州。刘禹锡惊闻噩耗,如得狂病,嚎啕大哭。此后,花费二十余年整理柳宗元的诗稿,编纂成《唐柳先生集》,将柳宗元的儿子抚养成人。
刘禹锡柳宗元之谊,始于志同道合,历经患难与共,终于生死可托。
八○三年,二十四岁的元稹与大他七岁的白居易一同登科,从此一同吟咏风雅、走马行猎,醉饮于长安酒肆,三十年间唱和不断。
白母去世,元稹虽财力不宽裕,却慷慨解囊,助白居易办丧事;元稹被贬,为母亲丁忧,没了俸禄,白居易“三寄衣食资,数盈二十万。岂是贪衣食,感君心缱绻”。二十万钱相当于元稹半年俸禄。
无论是相聚还是分离,两人相互赠诗酬唱,每每收到对方的诗,都要细究韵脚,对仗工整地进行回复。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和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整整一百个韵脚一模一样,把唐诗的格律表达发挥到了极致。
元白都支持永贞革新,为以身犯险的二王八司马鸣不平。他们一同发起新乐府运动,成为这场诗歌革新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
元稹病逝,白居易痛哭:“今在岂有相逢日,未死应无暂忘时。从此三篇收泪后,终身无复更吟诗。”祭文说:“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播于人间,今不复叙。”又九年,白居易写道:“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年轻的王安石参加科考,出类拔萃。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盛赞其“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特意设宴款待,席间写诗《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盍留连?”
以李白、韩愈的才华比肩王安石,满满的钦佩和殷殷的期望。
后来王安石变法,欧阳修反对,公然不执行“青苗法”。但止于君子之争,决不落井下石。
欧阳修去世,王安石作《祭欧阳文忠公文》,无一字贬损。
熙宁二年(一○六九年),王安石拟改革科考,苏东坡上奏反对。
“乌台诗案”发,为苏轼辩护的只有三个人,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都是苏轼的政敌: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和王安石。
后者时已归隐江宁,立刻派人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将自己的亲笔书信呈给皇上: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逃出生天。这才有了《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奠定了伟大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元丰三年(一○八○年),苏轼从黄州往汝州,经江宁,专程拜望王安石。王安石闻讯,马上风尘仆仆赶到渡口迎接。两个生命都已流过“政治三峡”的人在钟山谈诗论佛,煮酒和诗,通宵达旦。
王安石评苏东坡:“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王安石病逝,苏轼亲自执笔为评:“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闲,靡然变天下之俗。”
政治上是对头,文学上是知音。苏东坡和王安石,都有着一代文豪的大度与风采。
恕道与直道
“林语堂”这个名字,最早给我深刻印象,已是一九八三年。当时中国作协组织我们几个人采访海南农垦,中间去过苏东坡曾经流放的儋县,在书摊见到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最早是在美国用英语写的,出版后寄给国内朋友翻译,朋友忙,延宕多时,干脆自己翻成中文——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中文本。
我由此知道了林语堂牛得不行:出于寒门,天资聪颖,六岁在村塾发蒙,十岁离家上小学。靠二哥的津贴上了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教了三年英语获得领半官费奖学金的资格,往美国哈佛读硕士。官费停止,去法国教华工识字,攒钱去德国读博士。最终向北京大学借了两千美元(实由胡适先生垫付)完成学业。一九三三年,萧伯纳逗留上海,林语堂推出《论语》专号,介绍萧伯纳,为社会上的“幽默热”推波助澜。一九三四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一九三五年创办《宇宙风》,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
一九三五年后,林语堂第一部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即成畅销书,被视作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奠定他在国际文坛地位的《生活的艺术》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历五十二个星期,在欧、亚有近二十种译本并且四五十年畅销不衰,单在美国就再版四十次以上。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继《生活的艺术》之后,再次被美国的“每月读书会”选中。林语堂成为美国文艺界社交场合的宠儿。但在民间场合,他从不露自己的身份。崇拜者的信每天几十封,他让女儿替他回信,口述得头头是道,标点符号,另起段,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