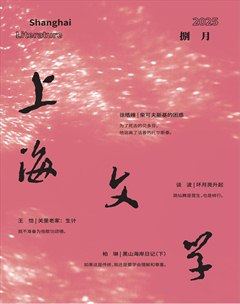一二七四年,马可·波罗从帕米尔高原的瓦罕走廊进入新疆,经喀什、叶尔羌、和田、且末、哈密等地,去往中国北方,他对新疆的地理、风土、人情等,都有生动记载和描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西域探险考察热”中,斯文·赫定、奥雷尔·斯坦因、保罗·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大体都是沿“玄奘之路”和“马可·波罗之路”进入新疆的。
尽管仍有一些学者质疑马可·波罗是否亲历过新疆,认为其记载可能参考了波斯、阿拉伯商人的口述,但无可否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文又译《马可波罗行纪》)首次向欧洲系统报道了新疆——那里的绿洲城市、商贸网络、多元信仰、饮食文化、浩瀚沙漠……这些,激发了西方对丝绸之路和亚洲腹地的想象,为研究元代西域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在东西方交流史上留下了华彩一笔。马可·波罗的传奇经历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启发了二十世纪至今的小说家、剧作家和传记作家,如尤金·奥尼尔的《马可百万》、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陈舜臣的《马可·波罗》等。
斯坦因曾四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活动,盗挖了大量文物,他的入疆路线与马可·波罗的线路有一定重叠,但主要还是凭借和依赖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他称这本书是“无价的地理与历史指南”,“在每一步探索中都能感受到玄奘的存在”。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三三年,斯文·赫定五次进入新疆,是楼兰的发现者(楼兰的发现同时要归功于他的土著向导、罗布人奥尔德克),他途经的喀什、和田等丝路南道重镇以及一八九五年的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线路上与马可·波罗的记载有重合,赫定称马可·波罗为“东方探险的先驱”,是自己的精神导师之一,在《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一书中,他写道:“马可·波罗的勇气和对未知的渴望,至今仍在激励着每一个走向荒野的人。”
与归国的玄奘法师一样,马可·波罗是经瓦罕走廊登上帕米尔高原的,同行的有他的父亲尼可罗·马可、叔父马飞阿。时年,马可二十岁。“离开沃克汉省(瓦罕)后,我们向着东方和东北方向继续再走三天的路程,一路上爬坡越岭,最后到达一座大山的顶巅,极目远眺,只见四周的崇山峻岭,高接云天,使人确信我们已登上世界最高的地方。”(《马可·波罗游记》第一卷第三十二章)
他准确地说出了这片高原的名称:帕米尔(Pamir Plateau)——《汉书》中的“葱岭”,玄奘笔下的“波谜罗川”,塔吉克族称之的“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兴都库什山交会的巨大山结。
马可·波罗一行在高原上骑行跋涉了十二天。他说,一路上景象荒凉,渺无人烟。群山巍峨,万仞高山直冲云霄,轻易看不见飞鸟在高山上空盘旋。大山顶上空气稀薄,气候寒冽,所以在高山上点火(注:主要是牛粪火),燃烧点很低,不能产生像平原上那样的热量。用这种火烹煮食物,熟得很慢。
帕米尔高原上栖息着很多野生动物,如雪豹、马鹿、棕熊、野牦牛等。马可·波罗尤其注意到了一种大如毛驴的“野绵羊”,羊体硕大,羊角长达三四掌尺,有些羊角甚至长达六掌尺。牧羊人利用这种羊角制成日常生活用的器皿,用来盛放各种食物。也有人用羊角围成篱笆,防患狼的入侵。
马可·波罗提到的这种“野绵羊”,就是帕米尔盘羊,也叫大头羊,它是盘羊家族八个亚种中体形最大的,成年盘羊重达二百五十多公斤,犄角长两米左右,角形呈螺旋状,表面布满环形的褶皱,由头顶向下并向后弯曲,有时可达三百六十度。生物学界有一个惯例——以首次发现或记录一个新物种的人的名称来命名这个物种,所以十三世纪之后,帕米尔盘羊就有了一个流传至今的新名称——“马可·波罗羊”。
从帕米尔再走四十天的路,马可·波罗来到的第一个绿洲城市是喀什噶尔(现喀什)。他说,这个地方幅员极其辽阔广大,城镇和寨堡林立,人民讲自己特殊的语言。他们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纺织业尤为发达。喀什噶尔有美丽的花园、果园和葡萄园。棉花、亚麻和大麻的产量也很丰富,由国内的商人运销世界各地。从马可·波罗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三世纪下半叶的喀什噶尔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伊斯兰教并未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喀什噶尔以东的叶尔羌(Yarcan,今莎车),马可·波罗盛赞它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城市,城里有风光明媚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