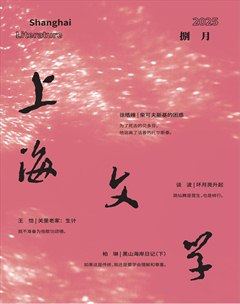一
“我想吃顿砂锅……”
父亲气息微弱,声音颤抖。我低下头,耳朵贴近他的嘴边,才听清了他的要求。我不敢看他的眼神,他的眼神不再犀利,不再咄咄逼人,凝重,无力,比他吐出的字句还要含混,近乎祈求。
父亲性格倔强,甚至有些古怪,一辈子不愿意求人,与子女间,他更是时刻保持着父亲的尊严,不曾说过软话。他费尽心力表达出想吃砂锅的意愿,这意愿一定在他心里占据了很久,也折磨了他很久。他本是心直口快之人,从不藏着掖着,心里有事是一定要说出来的。后来年纪大了,似乎刻意收敛,但他终于忍不住,不想留下遗憾。
我该满足父亲所有要求的。父亲提出来,是我这个做儿子的在这段时间护理的疏忽,甚至是失职。我早应该想到,父亲爱吃砂锅,砂锅是那个物质匮乏年代我们的家庭大餐。和饺子一样,并非平日就能摆上饭桌,要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后来日子好过了,吃砂锅的频率加快了,也要十天半月才吃上一次。每次吃,都很庄重,有仪式感,只是再后来,日子更富足了,反而冷落了砂锅。
父亲习惯做主,即便临近生命的最后阶段,也不愿意按照别人的意图做事。他在省城医院检查身体,住院治疗,稍有恢复就执意回到自己的家中,儿女好说歹说,他才同意到女儿生活的小镇调养。他怕我分心,耽误我的工作。他不习惯大都市拥挤喧闹的环境,也不喜欢大医院的嘈杂和人满为患。小镇安宁,舒缓,他待得舒心。他似乎清楚自己时日不多,甚至为自己选好了墓地。他告诫我,若是真到他不行的那一天,要及早去医院,别给妹妹家添麻烦。给国外的弟弟打电话,回不回来不重要。平时视频跟见到真人一样,弟弟在国外不容易,他不想给弟弟的工作和生活添乱。
我跑遍整个美食街、小吃店,竟然没找到一家砂锅居。有砂锅粥之类的菜品,父亲不喜欢吃。他问我,这么大的镇子,就没有一家做豆腐砂锅的?
年迈的父亲爱猜疑,他怀疑大夫的诊断,不相信我们的陈述,即便亲眼所见也是将信将疑。一切都和他的愿望有着较大的距离。他怀疑,猜忌,唠叨。我们又分头筛查,依然是同样的结果。在网上也没有搜到砂锅居。母亲对我说,不如咱们自己做,你爸什么都舍得,就是撇不下那个砂锅,他走到哪儿背到哪儿,好像他的命根子。
这是父亲的虔诚,也是他的悲哀。砂锅成了他的念想,成了他对过往见证的唯一物件。他舍不得丢弃,也不肯拿出来,很久了,我们没有做过一顿砂锅。
二
砂锅,是父亲心心念念的饕餮美食。
父亲早年经常出差,他说出来的每一个地名我都觉得新奇,觉得是遥不可及的远方。我还没离开过县城,一步也没离开过,没坐过火车,甚至连汽车都没坐过。父亲骑自行车上下班,有时候去托儿所接我,把我夹起来放在车梁上,喊一声上车喽,回家喽!我就莫名地兴奋,催爸爸骑快点,要像火车那样快!
火车站在县城的最东面,我家在县城的最西面,偶尔会听到火车的鸣叫,知道有火车开来,又有火车会开走。那个庞然大物在我的眼睛里很神秘,也很神奇。长长的,高高的,大大的,可以载很多人,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火车一声长鸣,喷出一串串烟气,慢慢启动,车上的人与送行的人就挥手告别了。我听见汽笛声,就会心跳加速,似乎那就是心驰神往的状态。我每次嚷着要跟父亲出差,他都不肯带我。他说大人有大人的事情,等我长大了,县城里留不住的。
父亲一定品尝过各地小吃。生活在偏僻的北方小县城,物质不丰富,物流也不畅通,出差带回稀罕的东西,让别人家羡慕,是家庭添置物件、增添喜气的特殊渠道。县城里人口少,也相对封闭,缺少流动。我甚至能记住街面上每个人的面孔,如果有外地人来,不用打听,不用介绍,都会认得出来。每每有人外出,有陌生人到来,是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同事同学都希望帮助捎带紧俏物品。但人们腼腆,既抱有幻想又难以开口。张口求人,总会给人带来麻烦。那该是最朴实的“带货”原始模式,大包小裹,身背肩扛,火车汽运,轮渡步行,既费心费神费力,又未必讨好。父亲不开朗,给人很不随和的印象,不易接近。我猜得出很多时候那些人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倒也成全了父亲,省却了带货的烦恼。
男人很少做家务,挑水劈柴、掏炕抹墙这些体力活自然义不容辞,若是这样的活计也推给女人,会被人戳脊梁骨。男孩长大了,身子骨结实了,长辈也会逐渐把这些活计过渡给晚辈。至于洗衣做饭、油盐酱醋、缝补洗涮,都是女人分内的事。油瓶子倒了不扶,是旧时男人的特权,算不得稀奇。
父亲没有眼力,家里缺啥少啥他似乎心里没谱,总要母亲提醒。出差之前好些天,母亲就暗暗地列出单子,写上要买的生活必需品,然后两个人逐项核对,统一认识。生活拮据,要计划着花销,一分钱掰成两瓣花。列出来的单子总要勾勾抹抹,多半被否掉。有时候甚至整个单子都作废了,父亲空手而归。出差一次要十天八天,半月甚至月余,父亲也容易把母亲的叮嘱忘在脑后。没有电话,地址又不确定,出差的时段基本等同失联,母亲盼,我们也在盼。父亲回家,带回糖果点心,数量不多,更显珍贵。南方的食品精致,既能刺激我们的味蕾,更值得我们到处炫耀。
记不清是哪一次,父亲出差回来已是半夜。敲门声把我们惊醒,听清熟悉的声音,母亲披衣起身,拉开电灯开关,打开房门,父亲带一团寒气进屋,冲我们微笑。他卸下身上的包裹,伸展酸痛僵硬的胳膊,照例掏出我们爱吃的糖果点心。母亲赶紧护住,三更半夜的,不能再喂肚子了,白天再吃。我们抓耳挠腮,兴奋的情绪被浇灭大半。睡梦被搅醒,美味又吃不到嘴,一分一秒地熬时辰,该有多么残酷。
父亲还在翻腾包裹,拿出纸包纸裹的物件,拆开一层,又拆开一层,露出一个带盖的小锅。锅边还有把手,油光铮亮的,涂满了釉,我们都未曾见过。母亲接过来,端详了半天,告诉我们,这是砂锅。
砂锅有什么好?我们把嘴唇噘得老高。
父亲说,豆腐砂锅可好吃了。
母亲说,记得那句话么,打破砂锅问到底,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三
早年间的家庭孩子多,绝少三口之家。若不是和老人住在一起,父亲理所当然就是一家之主。日子不宽裕,生活压抑,家庭氛围便不轻松。父亲大多不苟言笑,与子女之间也难言平等,彼此不可能成为朋友,或许有的父子还成了“仇人”。
我是家里的长子,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和睦。父亲继续着他的威严,我也到了叛逆的年龄。父亲常与母亲争吵,我觉得父亲蛮横,偏向母亲。父亲打过母亲,我挡在母亲身前,也被他痛打。那一幕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直到有一天,父亲与母亲大吵,他又要动手,我横在他俩中间,死死地抵住父亲。面对身板坚硬,高出半头的我,父亲拼尽全力也挣脱不开,终于在气喘吁吁中消磨了他的怒火,放弃了动手。家里的争端第一次由我来平息,第一次以父亲的“败落”偃旗息鼓。我看出父亲闷闷的,心有不甘,似乎也无可奈何。家里一下子没了声响,死一般地沉寂,一连好几天都很压抑。
此后父亲长时间与我冷战,不理睬我。迫不得已说话,他也让母亲传话,或者冷不丁吼我,脸涨得通红。我则小心翼翼,生怕再次惹恼他,给他痛扁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