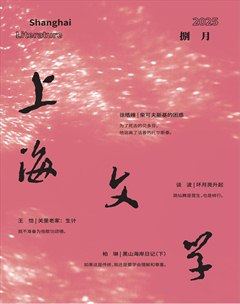一
我家有个大大的瓦煲,棕色的。有些人家炖汤用的是一件件骨致的小瓷盅,可我家人多,要用瓦煲才能装得下那么多汤料。我的奶奶,不对,在广东应该叫嫲嫲才是,喜欢给家里人煲汤,这是我从小喝到大的记忆中的味道。
一餐看似简简单单的住家饭,其实要耗费广东师奶一天的心血。人多口杂,众口难调。就像番茄炒蛋,爸爸喜欢吃甜一点的,总说还不够甜,我却喜欢淡一点的,已经觉得甜到苦了。当然以前我也喜欢甜的,嫲嫲说我和爷爷一样,都是“糖塔”。小时候我和爷爷一人捧着一根甘蔗啃,把牙齿都啃坏了,现在知道要爱惜牙,啃不动了,也不敢再这么任性。
我喜欢吃糖,经常缠着爷爷问有没有东西吃。爷爷说我是“咀头王”,但还是会在房间里藏几包QQ糖或AD钙奶,我问的时候他就时不时拿一包出来。可现在,放假回家,爷爷就算主动给我留了很多零食,我却不那么敢吃了。也许因为年纪大了,受一些断糖理念的影响,不再敢吃那么多甜食。
在口味上,我们家很难达到一致。也许是因为我从七年前离开家去广州读大学,一年前又前往上海读研后,口味渐渐改变了,逐渐被食堂和外面的餐饮店影响和同化。而家里人,也因年纪渐长,对味觉的敏感度渐趋下降,需要高盐高甜才能刺激味蕾,感知食物的香气。但有一点,我们永远能达成一致的,就是嫲嫲煲的汤。每次她说自己“一担心机滚啖汤”的时候,我们就都会捧场得天花龙凤,对嫲嫲的厨艺赞不绝口。
老火靓汤好喝,因为里面添满了各种滋补的食材,要在火炉上炖煮起码一个半钟头以上。煲一啖汤,不仅要考虑汤料之间的搭配和功效,还要用心用情去熬煮、去把握火候。广东的夏季总是“水火交织”,老广们总会把“湿气重”“热气”挂在嘴边,这时嫲嫲就会煲各种清热解暑的汤,像冬瓜薏米猪润汤、竹蔗粉葛蚝豉猪肉汤、绿豆白鸽猪骨汤。到了冬季,需要喝一些滋阴补血的暖身汤,像太子参羊肉汤、发菜鸡脚猪横脷汤。还有一些四季皆宜的如海底椰炖竹丝鸡、冬虫夏草红参炖鲍鱼等等。不过至今我还是区分不出西洋参、太子参、红参、党参等的区别,只知道这是些好东西。汤中加了参会带点苦涩,又略微回甘。冬虫夏草、花胶、云苓、北芪基本都是汤料的标配,红枣桂圆放得越多,汤就越甜。
粤菜讲究新鲜和食物本来的味道。记得我曾问过嫲嫲的拿手好菜糖醋排骨里加了什么酱,她一下子就不高兴了:“加什么酱!油就油,盐就盐。”嫲嫲煲的汤也是这样,不放一粒盐,最多加点白糖提提鲜,毕竟要吃的就是食材本味。她很反对我们在外面吃东西,总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出面的东西吃埋吃埋就会形成一个患的。”确实,家里做的绝对是最安全、最干净的。外面的东西虽然好吃,但都是各种调味品调制出来的,调味品本身也是“科技加狠活”,吃多了绝对出问题。
其实嫲嫲也不是一开始就会这么多的。她总说自己“做女”,也就是未出嫁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会,一切都是在慢慢学慢慢做中懂得的。
年轻时,嫲嫲很辛苦。爷爷调到市里的机关来了,她还在镇上,要喂鸡养狗,照顾家公家婆,还要带两个儿子,不过都这样过来了。当年她在房管局工作时,还要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敲门家访。她总说:“你们都没捱过艰苦的岁月呢!”
二十一世纪初,我出生。根据政策,嫲嫲可以办理提前退休,出于要照顾我的想法,她退下来了。有一天她在路上遇到以前的工友,别人问她现在在干什么,她说:“开幼儿园呢。”工友问:“什么幼儿园呀?”嫲嫲说:“欣欣幼儿园咯。”欣欣是我的小名,嫲嫲口中说的幼儿园,其实就是只为我一个人服务的幼儿园。
其实嫲嫲最怀念的还是以前工作的时候,那时单位效益好,每年能拿到不少分红,还能组织大家全国各地旅游。而爷爷的单位就只吃财政饭,年底几乎没有绩效或分红。嫲嫲总是不无遗憾地说:“要是不提前,没准还能混个副局退休呢。”我笑笑说:“那看来是我耽误你了。”嫲嫲就说:“没有啊,你情我愿的。”
退休后,嫲嫲总一个人在厨房忙进忙出。下午三点,她会给自己熏艾条做艾灸。烟雾缭绕,氤满整个厅房。她眼睛不太好,做过白内障手术,时有走神,腿上就会不小心烫到。密密麻麻的一个个小洞,触目惊心地排布在小腿上。
她在厨房从早忙到晚,有时也觉得辛苦,不想做了。广东人有给父母交家用的传统,嫲嫲试过不想做了的时候,大声扬言道:“反过来我给你们钱雇你们做呢,你们肯不肯啊!”话是放出来了,但也没真的这样做。因为嫲嫲这人也很嫌姜嫌醋(挑三拣四),觉得别人做得马虎,又不合口味,还是自己把午饭和晚饭的工作承包了下来。洗菜、切菜、煮菜,忙前忙后。我只能给她打打下手,洗洗菜,切切葱,剥剥虾。虾刚从菜市场水盆里打捞出来,还活蹦乱跳,一捏,就从水盆里蹦出来,弹得满脸都是。
逢年过节时,嫲嫲会打薄撑。薄撑是一种用糯米粉和粘米粉混合制成的小吃。面团在锅上撑开薄片,沾上用冰片糖熬的糖水就可以吃了,甜甜的,黏黏的,糯糯的。黄糖的甜很绵密,甜度很高,软软糯糯的薄撑沾上一点糖液真的很好吃。即使吃多了会腻,会饱滞,消化不了,但还是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嫲嫲做的薄撑其实很粗糙,远不如外面茶楼的精致,时不时还会失手,薄撑摊得薄厚不一,薄的那面要么沾到锅黑了,要么焦了,厚的那面要么没熟,要么吃起来实实的,并不松化。但那是我最怀念的味道,也是绝无仅有的味道。别人无论做得再精致,再美味,也不可能复刻出嫲嫲的手艺来。每到逢年过节,嫲嫲就会打几份薄撑,让先祖和菩萨先吃,以示神心。
小时候,我最爱在广百广场对面的红丽糖水铺吃芝麻糊拼花生糊。黑白鸳鸯的配色,犹如一幅八卦图。店里经常没有花生糊卖,可能是买的人少,要看运气才能碰到。后来老板索性不做花生糊了,我也没有再遇见过那熟悉的味道。直到大学时在广州东山口才碰到过一家小店有卖,好吃是好吃的,一样香醇回甘,可跟记忆中的味道还是不一样。我想,要是让我再尝回记忆中的味道,我也一定能认得出来。
我还喜欢在广百对面的红丽糖水铺吃云吞,每次嫲嫲带我去广百书城看完书,我就会让嫲嫲带我吃一碗云吞再回家。爸爸妈妈更喜欢另一家老字号巧心面店的煎饺,觉得红丽的云吞一般般,但我却觉得很好吃。红丽的汤底最让我赞不绝口,咸鲜浓郁,云吞馅里还裹有白芝麻,配上两颗吸满汁水的生菜,别有一番风味。
红丽糖水铺到现在都还是用传统的方式点单,餐牌在墙上,付完款后老板会在收银台的抽屉里摸出一张彩色小卡片递给顾客,卡片上写着餐单,服务员上菜后再把卡片收回。本来那里有两家糖水铺,后来合并成了一家,还兼卖牛杂。
现在红丽还在,巧心却关门了;糖水铺还在,广百大楼却倒闭了。广百楼下的端州月饼还在,仍是每年中秋送礼首选,可端州大酒店却不在了。还记得小时候和爷爷嫲嫲去那里喝早茶,还有茶楼阿姐推点心车,一笼笼茶点推过来让顾客自取。现在点心车早已几近绝迹,非常难再碰到了。广百对面的皇朝酒店也早就结业,老板早就移民。以前生日都是在皇朝定的蛋糕,在精装的菜单本上选蛋糕款式。老式蛋糕总是用忌廉裱出大红大绿的花叶,喜气洋洋的。现在的皇朝西饼是当时的师傅舍不得,后面开的,直到现在我们还时不时会去皇朝西饼买买面包。
我最喜欢西饼铺里的荔枝酥。每次吃时就会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粤曲《荔枝颂》:“身外是张花红被,轻纱薄锦玉团儿,入口甘美,齿颊留香世上稀,什么啊,可是弄把戏,请尝个新,我告诉你,这是岭南佳果靓荔枝……”轻松快乐的旋律总能让人想起童年。很小的时候,爷爷嫲嫲就会教我们唱儿歌、唱红歌、唱粤曲。我一边模仿红线女大师的动作、眼神和表情,一边咿咿呀呀地学唱,爷爷嫲嫲一边给我打拍子,一边乐呵呵地笑。夏天,家里会买一些应季荔枝回来尝尝,有时是桂味,有时是妃子笑,有时是糯米糍,不过还是桂味最常见。嫲嫲总说:“一个荔枝三把火啊,不要多吃。”
城市在改变,时代在更迭,那些陪伴我成长的店铺说不见就不见了,唯有记忆中的味道长青。
有一次我梦到嫲嫲,梦到她生病了,打电话过去问候,还好一切正常。但是没想到当下是没什么,过几天她就因腰疼入院了。她在医院占了个床位,做了两周针灸,白天到医院做理疗,晚上回家休息。老人家穴位难找,被扎得满身是血,可她连一声都没哼。真能忍。她说她年轻时也这样,因为血管细,护士怎么都找不到,白挨了好几针。辛勤、隐忍、克制。一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这句话我在嫲嫲身上看到了。
嫲嫲很有神心。每天早上都会从家内拜到家外,晚上再从家外拜到家内。土地公、观音菩萨、灶君、天官和门官,都要挨个拜遍。香烛的烟雾缭绕在整个厅房,每天,我们都细嗅着幽幽的檀香开启新一天。香火的味道清新悠长,宁神静气,似是能洗涤人的整个肺腑,净化人的心灵。
逢年过节还会拜下床头妈,这个时候嫲嫲就会让我打开房门,通风透气。洗头也很有讲究,初一十五不给洗,过年要开年之后才能洗,人日不能洗。以前总觉得嫲嫲给自己立下各种规矩,束缚自己,禁锢他人。但自从那一次我跟嫲嫲去买元宝蜡烛香,就改变了看法。
我问嫲嫲:“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呀?”她说:“求祖先保佑各人身体健康咯。”我不解:“要身体健康不是得靠自己锻炼吗?”她说:“饮食也要,作息也要,锻炼也要,有人心再加上有神心,就会好上加好。”卖香烛的阿婆第一次见我就和我说:“你嫲嫲好有神心啊,怪唔之得教得几个孙甘叻甘有孝心啦。”所以后来,我也认可了嫲嫲的生活方式。这不是迷信,而是一种坚守。
每逢过节前,嫲嫲都会叫上我一起,提前叠好元宝、金银纸和衣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