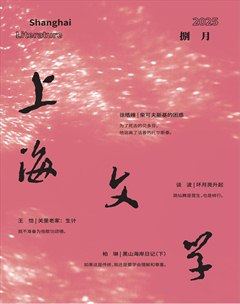我正在打开藏书——好吧,这个题目借自瓦尔特·本雅明,我必须开诚布公,此文或许没有任何原创价值,我若能让本雅明的意见在一个世纪后的情景中再呈现一次,也就心满意足了。我读过此文的两个中文译本,均为友人编选,其中一个版本对标题借用那句话的翻译是“藏书人是否已经日暮途穷”,另一个更流行的版本则是“这种人已行将绝迹”。这种人就是我这种人。正如本雅明说过的那样,在受人冷落的角落中发现一本孤零零无人问津的书,只有自己懂得其价值,买下来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王子买下一个卑微却美丽的女奴,最终的目的是还之以自由。书获得解放的命运,就是在一个懂得它的人的书架上占据一个尊贵的位置。这恰与中国人通常说“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意思完全相反,书不是获得颜如玉的方法,书就是颜如玉。书不是途径,而是目的。经年累月,我的藏书越来越多,家中各个楼层都有放书的地方,几乎每个房间都有书架,在学校我还有两间办公室可以放书,在国内不同居住地点也都存有一些书,到目前为止清点藏书数量已经变得越来越难。本雅明援引法国大文豪法郎士对庸俗商人的回答,就像任何商人收藏瓷器的目的不是把所有瓷器都用一遍,藏书的人也不见得把所有的书都读过。“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几十年前还在学生时代,仅仅有千册藏书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一点了。何况从本雅明的时代至今,知识分子的迁徙命运始终未曾改变,书随着人在世界上的旅程不断增长,虽然未曾读完每一本书,但每一本书都有属于特定时间、地点、心情的气息,打开来就召回一段记忆。我在自己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书,都能记起获得这本书的情景。打开自己的藏书——我完全相信本雅明那篇文章的最终意义——正是打开自己的记忆,藏书看似混乱无序,却是人生或人间情景的呈现。
然而,此时距离本雅明写作已经过去一百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藏书,一个电子储存卡就可以装下我全部的藏书——不,如果有足够大的容量,甚至可以装得下我们学校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文献。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读书。我们从机械复制时代,到了数码复制时代,又到了数码生成时代,现在是公认的短视频时代,视听组合的“全息”传媒,替代了一行行线性阅读、需要调动想象力和批判力的个人经验过程。现在是“只争朝夕”的时代,哪儿有二三素心人在荒江老屋中商量学问?藏书、读书,都是需要漫长一生的事,而且在逆行人生中或许更是显得无用,像是看花听雨闻香。我能理解我的学生们不藏书——有的是电子设备,也能理解上海地铁里的上班族们无暇读书——我曾被学生批评把读书看得如此尊贵,这本身是一种特权的显示。学生批评我的话让我思考了很久,不仅让我明白了自己是上个世纪的人——真的还是本雅明、周作人、钱锺书的同时代人,而且读书意味着我有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资本,时间。
试想收藏的全部意义,都在时间之中才有价值,读一本书需要几个小时到一天、几天甚至几周,而对所读的理解也只有在时间中才体现出价值。甚至,正如一位诗人所说,一切阅读都应该是不断的重读。所有的书都只有在重读中才真正产生价值,这意味着,时间对于书的关键意义。我可以这样理解诗人的话:在我所有藏书中最古老的那些,不是指其版本多么古早,而是对我个人来说,是从青少年时代一直陪伴身边的书,如楚图南翻译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印有黑白木刻插图的《呼啸山庄》,印有钢笔插图的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老古玩店》《孤星血泪》,改革初期重印的名著名译《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欧也妮·葛朗台》和《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译)、《伪币制造者》(盛澄华译)、《还乡》和《无名的裘德》(张谷若译)、最早重印的《财主底儿女们》(路翎译)、封面从洁白到弄污的《新诗潮诗集》(只存上卷)、春风文艺的两本《朦胧诗选》和《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在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断重读的上海译文版《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喧哗与骚动》《情人》《细雪》,以及陕西师大出版社印刷的、看上去每个铅字都有暴动感觉的第一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些书后来我不断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