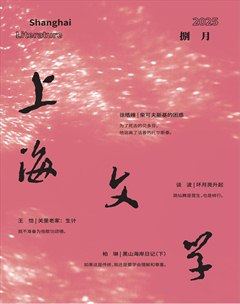一
动念写这篇文章,源于偶然看到的文化新闻,“话剧《人世间》迎来百场纪念演出,从小说到舞台缘何长演不衰”,它引发了我对文学与影视关系的思考。长篇小说《人世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二〇二二年作为央视开年大戏登陆CCTV-1黄金时段,创下多年来黄金档收视率新高,原著作品经由电视剧“出圈”而形成的大众影响力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二〇二三年底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的电影级质感成为彼时最热门的文化议题,“黄河路”“排骨年糕”等海派符号直接催生新的网红打卡地,据说电视剧热播期间上海某些商圈客流量加倍激增。二〇二五年电视剧《北上》播出后沿线几十个大运河文化遗址的参观人数创单日新高,相关“二创”视频播放量破十亿次。三部由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的现象级剧作,正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文学与影视的双向奔赴,为文学与影视的互动提供了极具研究价值的样本。
茅盾文学奖小说的电视剧改编,虽有着依托优质文本的天然优势,但实际创作中每一步也颇不容易,要在文学性与大众性之间小心翼翼地平衡。它们的火爆当然并非偶然的IP红利,都是主创团队精心的跨媒介转化。执笔《人世间》剧本的王海鸰坦言“梁晓声的文学作品提供了非常扎实、鲜活的人物基础,改编的难点在于严肃文学和大众电视艺术之间的区别”。原著中以周家三代跨越五十年的人生和命运起伏,串联起知青下乡的青春磨炼、恢复高考的知识觉醒、国企改制的时代阵痛、旧城改造的利益博弈,这些历史节点在小说中主要是以苦难叙事为底色铺陈的。电视剧改编的关键策略落在了“调高温度”的基本主题和情感选择,虽没有刻意淡化老工业化基地平民生活的艰辛,但着力在家庭关系与细节中将苦难转化为更日常的生活肌理。同时,电视剧还调整了部分人物命运的戏剧张力和性格力量,比如女主人公郑娟在小说中是被动承受生活和命运的底层女性,剧中明显为她加了戏,赋予这个人物更多成长弧光,这样既保留了原著的基本故事和人物轮廓,又让观众强化了对平凡人生力量的共情。《繁花》的电视剧改编是一场更显张力的美学角力,金宇澄的沪语小说原著自带市井史诗的粗粝感,而王家卫执导时则注入了强烈个人风格的电影美学,剧中至真园的霓虹招牌在雨幕中晕染成旧胶片般的暖黄,排骨年糕的热气在慢镜头里凝成白雾,黄河路的梧桐叶在转场时化作记忆的碎片……这些画面是王导用镜头语言对沪语小说的二次“编码”,小说原作的主体性和导演的“作者性”碰撞与对话之后呈现出来的视觉盛宴令电视剧《繁花》成为当下影视列表中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也因此圈粉无数。《北上》小说原著以京杭大运河为脉络进行时空串联,堪称一部凸显厚重感的流动文化史诗,而电视剧改编则在故事结构、人物关系上做了较大的重构,并且弱化了原著中的历史溯源,转而强化关于当下与未来的故事性和烟火气,剧中“运河文化”不再是博物馆里汇集的文物,而成为当代人对话历史和确认自我的路径。三部作品的改编,各有各的难度与挑战,亦各有各的“转化之道”,或调温度,或融风格,或重构叙事,共同诠释了殿堂级文学经典与大众化电视剧艺术如何双向赋能。我们从中看到,经典为影视提供精神的根脉,让改编有了穿透时空与人心的文化底气;影视为经典注入传播的活水,让文学从纸页间走入更广阔的审美与文化生活现场。
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已沉淀下百余部获奖作品,这些作品如文学星图中的坐标,标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它们不仅是优秀的代名词,更承载着持续经典化的考验与使命,而所谓经典,从来不是静态的“完成时”,而是在代际阅读、多元阐释与艺术转化中持续生长的“进行时”。何为经典?或许没有绝对标准,但在我们的基本共识中它需有厚重的精神纵深,能让不同年龄和文化背景的读者在字里行间照见自己的生命投影;它还要携带时代印记,以细节的血肉感见证某个历史时刻的心灵史与风俗史;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精神的“公约数”,在反复阅读中被不断激活,成为个体确认自我、对话世界的精神镜鉴。四大名著的常读常新,鲁迅笔下的国民性剖析以及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对复杂人性的叩问隽永绵长,皆因如此。而经典的生命力,在于其开放性与未完成性,一部经典小说,从纸页走向人心,从个体阅读走向集体共鸣,需要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再创作——普通读者用生活经验为文本注入温度,研究者用学术视角为经典拓展深度,影视改编者则用影像手法为经典开辟新的传播场域。这其中,影视改编的特殊价值现在愈发凸显,它以视听语言为桥梁,令“未完成”的经典文本在跨媒介的大众传播中获得新的生长动力。当我们讨论这三部改编剧的时,本质上是在探讨文学如何借助影视的能量打开新的天地,影视又如何在文学的滋养中获得更深厚的精神底色。《人世间》《繁花》《北上》三部小说同名电视剧引发的热潮,包括对具体改编策略和效果的讨论,甚至争议,正是这种文学—影视共生关系的生动演绎。在多媒体资讯勃兴、新大众文艺崛起的今天,影视改编不是经典的终结,而是另一种方向上的新生,用大众更易接受的媒介形式,将“厚重”转化为“可及”,将“深度”转化为"共情",将“历史性”转化为“当下性”。
二
如果说上述三部茅盾奖长篇小说的改编,已然勾勒出荣获顶级文学奖项、代表一个时代文学高度的作品与作为大众文艺的电视剧之间双向赋能的生动图景,那么,当我们深入分析另一些作家作品在语言向影像转换中的得失时,原作那种不可复制的特质与魅力反而显得更加清晰,这种对比丈量着文学与影视的互动边界,更照见了文字本身不可替代的精神内核。这类作家中,张爱玲最具典型性。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张爱玲始终是最独特的那一个,其早期作品被从文学史中“打捞”出来以后虽一度“无处安放”,却被反复阐释、研究以及在影视媒介中获得了新的文本形态。若论影视改编的适配性,张爱玲小说堪称“天生的电影文本”,她以天才般的敏锐将烟火日常与豪族恩怨罗织成色彩饱和度极高的画卷,从葛薇龙眼中“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到白流苏看向堂屋中“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再到王佳芝牌局桌前的“戒指展览会”,视觉化美学基因贯穿始终。更妙的是,张爱玲小说叙事从一开始就暗合了镜头语言,“在衣橱里混了三个月”的时空压缩、“镜子里的也老了十年”的心理外化等,都天然具备转化为影像的叙事势能。
然而,张爱玲小说的影视转换显然又是极难的。首先是如何在镜头与台词的框架中保留其独有的叙事辨识度与文字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