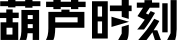奔腾壮阔的江河最初有着怎样的起始?作家刘大先历时半月踏查三江源地区,以艰难行走丈量冰原河谷,以微小肉身体味广袤自然,高海拔地带的缺氧、失温与迷路,一次次生理的极限挑战加深对河流源头的哲学认知。文本穿梭于实地探察与藏地传说之间,穿梭于冰川、寺庙与石经城之间,让我们听到严酷自然中放大了的历史回声。
从源头开始
人们在婴幼儿时代的形貌大体是相似的,长大后才面目各异,河流也一样。河流伊始,不过是一些从不同泉眼、石隙、草缝中渗出的细流,汇聚到一起后慢慢获得隐约的形象,当它向前流淌的时候,不断有新的水源融入进来,同时也会有一些支脉分流离去,最终它壮大起来,奔腾汹涌,同经过的土地、山峦、人文相互交织,彼此成就,形成了自身的个性与品格,并被赋予形形色色的意义与价值。
像长江、黄河、澜沧江这样的河流,它们的名字就是超级词语,早已超越了字面本身,富含着浓厚的地理、历史与文化积淀,高度浓缩、意味隽永,以至于成为一种各具特点与内涵的符号,延伸为关于母亲、故乡、生命和人生旅途的种种象征。
大多数人对这些大词所指涉事物的理解都是片段性的,或许有的时候还停留在图像和印象的层面,亲身去完整观察与体验的微乎其微。即便是生活在它们岸边的人,所知晓和熟悉的也只是局部。我们也许看过从高峡间涌出的急流,于山峦处曲折蛇行,甚或凭恃悬崖峭壁站立起来,然后在平原上缓慢而稳定地行走,到出海口不动声色地融入一望无际的深蓝。但是,我们看不到全部。没有多少人能够沿着任何一条河流从头走到尾,或者有人能够完成这样的壮举,他的感知也很难对那条河流的形状有总体的把握。
这个时候人们也许会借助于地图,那是经过无数人探勘的成果,有了空天遥感和三维测绘技术之后,立体和直观的界面更加友好了,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宏观的全貌。我们知道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全景和流域:
唐古拉山东北麓格拉丹东雪峰流下的沱沱河冲破可可西里荒芜的高旷荒原,在囊极巴陇汇合当曲、莫曲、牙曲、丹曲、布曲等无数河流,汇聚为通天河,又在曲麻莱与从五道梁东南而下的楚玛尔河交汇在一起。于是,这三大源头归宗南下,到玉树藏族自治州巴塘河口融为金沙江(丽水),在地球上最为褶皱的横断山脉、云贵高原边缘奔突,直到四川宜宾岷江的河口,流到湖北宜昌这一段是川江,然后是到湖南岳阳这一段的荆江,从此奔腾在洞庭、江汉、鄱阳、苏皖和长江三角洲平原之上,便是我们熟知的长江。它从南京开始被称作扬子江,在上海的崇明岛汇入东海。
黄河则从巴颜喀拉山的约古宗列盆地涌出,与卡日曲一起流入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的扎陵湖与鄂陵湖后,绕过阿尼玛卿山,在四川若尔盖与白河汇合形成九曲第一湾,向北通过龙羊峡,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处接纳了湟水,穿过甘肃兰州,冲积出从宁夏到内蒙古巴彦淖尔及呼和浩特一线的河套平原,到托克托县的河口镇为上游。然后,黄河以近乎90度的转弯南下,在山西与陕西分别接纳了汾河与渭河,于潼关再次以90度的弧度拐向东,经过小浪底之后同洛河、伊河、沁河相遇,到河南郑州桃花峪这一段为中游。下游部分的黄河因为从黄土高原裹挟的大量泥沙,成为地上的悬河,穿过山东济南,由东营进入渤海。
长江与黄河被称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西向东的过程中滋养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无数民众,澜沧江却是自北向南,途经最为丰富复杂的民族与文化地域。长江源区在黄河源区的西南面,它的东面更南的地方就是澜沧江源区。从玉树州的莫云乡和扎青乡的吉富山与扎西乞瓦湖起步,扎那曲与扎阿曲汇合为扎曲南下,穿过囊谦县,一路吸收布当曲、宁曲、子曲、热曲等无数条知名不知名的小河,在西藏的昌都与昂曲汇合为澜沧江。澜沧江在昌都左贡县境内与玉曲河汇合,过了曲孜卡乡进入云南,一路南下,在横断山脉中劈山突进。经过西藏芒康县和云南迪庆州德钦县的时候,开始同独龙江、怒江与金沙江并驾齐驱,呼啸而下。在云南,它陆续融入永春河、黑惠江、漾濞江、威远江、补远江、流沙河、南班河。然后,金沙江拐弯,独龙江注入缅甸伊洛瓦底江,怒江到缅甸成为萨尔温江,注入缅甸海,澜沧江则从西双版纳南腊河口岸同样进入中南半岛,成为贯穿整个半岛的湄公河,途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最后从越南胡志明市流进南海。
然而,无论看过何等样的地图乃至动态视频,都替代不了身体的抵达和脚步的丈量。肉身在广袤的大地上是微小的,也正是其微小才能带来最真切的感受:水与天空的颜色,风吹过耳边的声响,手指触碰江面的温度,脚踩在陡峭或者平坦、潮湿或者干燥的堤岸泥土上的感受……如果想让那些词语和图像回归到它们最初的物质和本真,就需要自己去行走。
一切都要从源头开始。在此前的人生中,我已经断断续续地走过无数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它们多多少少都与这些著名的大河有关。我想去看看那些蔚为大观的壮阔波澜最初有一个什么样的起始。带着这种好奇,附加着对于水的温情和历史地理的爱好,我踏上了探访三江源的路途——这三条不同流向的河流之所以被放在一起,是因为有着共同的起源地,都在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为中心的区域。
2023年6月,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走了一条类似于蝴蝶结式的路线,把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一市五县与三江源有关系的地方踏查了一遍。从西宁飞到州府玉树市,溯通天河(藏语叫直曲,即牦牛河)而上,经结古镇、隆宝镇、安冲乡拉则村,称多县的直门达,治多县立新乡长江第一湾、多彩乡群果安顿牧场、加吉博洛镇,杂多县扎青乡扎西拉吾寺、燃智嘎日冰川、扎西乞瓦湖、阿多乡、莫云乡、查旦乡,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沱沱河镇,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聂荣县、安多县,格拉丹东雪山,返回治多县索加乡囊极巴陇、东经扎河乡,到曲麻莱县约改镇、麻多乡约古宗列盆地,南下囊谦县白扎乡、香达镇、娘拉乡、吉曲乡、吉尼赛乡、毛庄乡,最后返回。
高海拔地带高强度的奔波与行走,足以让人身心疲惫、精神涣散,我只能在路上简单记下走过的地方和印象深刻的景象。在那个过程中,我是一个充满新奇却又毫无准备的行者,每天都是浑浑噩噩的状态。回来之后很久才缓过来劲,慢慢消化,那些纸面和屏幕上的地图逐渐勾连成片,形成它们在现实中的全息景象。时过境迁之后,那些高原反应、舟车劳顿、寒冷与饥饿反倒显得弥足珍贵,它们赋予了一种仅仅通过视听形象所不具备的感觉和体察。我曾经看过世界上最著名的那些河流比如亚马孙河、拉普拉塔河、伏尔加河的文字、图片和影像,但始终仅仅是一些信息、知识和印象,没有肉身的直接接触,就难以获得经验上的自足。那种亲身经历的直接性、自得感,是间接经验得来所无法比拟的。用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所谓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结古:遥远的集镇
1914年8月,不到30岁的中学老师周希武(1885—1928)被抽调到兰州,随同甘肃勘界使、忠武军统令周务学(1868—1921),到青海玉树进行勘界调查,路途崎岖,道路艰难,花了八九个月才跑完行程。如今交通便捷了许多,开车从西宁到玉树,大约是12个小时。我从北京飞到西宁,休整了两天,再从曹家堡乘飞机到玉树巴塘,不到一个半小时。玉树藏族自治州下辖玉树市、称多县、囊谦县、杂多县、治多县和曲麻莱县,共有45个乡镇,开车的话,平均每天跑一个乡,问题应该不大,可能只需要一个半月就走完了。
“玉树”是藏语译音,原意为遗址,可能是指统一金沙江与黄河上游诸多小国部落的格萨尔王的王宫遗址所在地。格萨尔这位史诗中的英雄,从历史进入神话后,实迹反倒变得扑朔迷离了——从安多、卫藏到康巴一带,他似乎无处不在,但又不在某个确定不移的地方。玉树这块广袤的地方联结了青海、四川、西藏、新疆四省,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区位相当重要。周希武当年到玉树做调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殖民者勾结西藏卖国分子非法订立《西姆拉条约》,鼓吹西藏“独立”,还把青海全部划在其境内。在主权与边界意识逐渐觉醒的情况下,为了稳定局势,甘肃当局才派专员到甘肃与四川交界处,勘察地貌,会勘玉树的界务(彼时玉树归甘肃西宁道管辖)。
从巴塘机场出来,烟灰色的乌云笼罩天空,暗沉的天色映照草原的嫩黄。我准备先行了解一下巴塘弦子的故乡,就直奔玉树州牦牛黑帐篷游牧文化民间博物馆和牦牛黑帐篷民俗文化体验馆。这个由厚重的牦牛毡搭建的帐篷,坐落在宽阔平坦的巴塘草原之上,几乎有两个篮球场大,里面是各种本地民俗风情物的展陈,还细分了一个玉树雅砻江流域古村落生活体验区。牦牛与羚羊的标本栩栩如生,只是因为很少有人光顾,帐篷内部空气不流动,气味不大好闻。
从帐篷出来直奔玉树市府结古镇,快到宾馆的时候,看到有一段叫感恩路,不免好奇。开车的师傅说,那是2010年地震后新修的,此地治安以前很差,但是震后来自各地的驰援救灾,给人们精神上带来了一种洗礼,爱传递爱,社会风气都好了很多。结古镇坐落在诸山中间平坦地带,通天河穿过市区,河岸就有一座圆形的格萨尔广场,中间方形台基上伫立着耀武扬威的格萨尔王。
“结古”在藏语中是遥远地方的集镇的意思。这暗示了它的前世,就像陈晓写到的,它“在100多年前就形成了一个国际性市场。拉萨的布匹、兽皮、鹿角、麝香、藏药,俄罗斯的火枪,甘肃的铜器和细面条,四川的茶叶和丝绸,云南的糖,以及来自印度的干果和各式各样小玩意儿,都可以在这个狭小寒碜的集镇上看到。同样商品在结古的卖价比在打箭炉(即今日的康定)更便宜。打箭炉的货物主要来自上海,长距离运费让货物成本很高。结古物价更便宜则是因为那些来自中藏(大致是拉萨与日喀则为中心地带)的茶商,他们在来路上不愿意空着驮包,但必须在结古卖掉所有货物才能装载茶叶。货币最能表现这里贸易的广博和发达程度。19世纪,结古通行的货币不是黄金白银,而是(印度的)卢比。
贸易带来流动的人群和逐渐繁茂的其他事业,作为信仰载体之一的寺庙显然是其中之一。宾馆窗户外,就可见不远处北山顶上红墙金顶的寺庙,那便是结古寺。像藏地无数寺庙一样,它已经被开发成旅游观光的景点,然而这不过是外人视角。对于本地人而言,寺庙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人神共处的思维依然残留在这遥远地方许多人的心中。如同各地藏传佛教寺庙一样,结古寺门口立了一座铜制的香炉,两端则由面目狰狞的神兽抬起。神兽獠牙威猛,环抱圆盘,我说不出来它的名字,估计应是自然崇拜中的灵兽。圆盘中雕刻的则是法轮,环有火焰纹饰。它隐含着密宗护法神大黑天守护曼荼罗(坛城)的意思,是藏传佛教与本土苯教结合的产物。
也许不是旺季,结古寺几乎不见外地游客,进到里面,殿宇昏暗,只有艳丽的经幢垂下来,微弱的光线照在金碧辉煌又造型繁复的佛像之上。七八个紫袍喇嘛悄无声息地围在一起,有个小喇嘛举着手电筒照明。我很好奇,走过去,发现他们在搭建坛城。我对此毫无了解,只是众人屏息凝神,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敬畏之心。不过,这些总归让局外人感到有些压抑。
从结古寺出来,时间还早,我决定再去一下文成公主庙。文成公主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出发,历经两年多才到拉萨,据说其中有一年就是逗留在此处。本地陪同的人说,因为文成公主和陪同她的大臣禄东赞相爱并且怀孕,所以耽误了时间。禄东赞(噶尔·东赞)因此回到拉萨还被松赞干布刺瞎了眼睛。这是一个超乎我认知的民间传说,至少正史书籍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载。史料中的禄东赞并没有失明,在松赞干布去世后(650年,永徽元年),还作为大相辅佐年幼的赞普芒松芒赞,在攻灭白兰部(游牧羌人在川西青南建立的部落王国)和征服吐谷浑(鲜卑人融合羌人等建立的王国,后来吐谷浑化入汉族和土族中)的过程中,实际上掌握了吐蕃的军政大权,直到667年(乾封二年)才病逝。安多地区民间口头流传的这个故事,多少是对禄东赞守护者形象的想象,隐喻透露出对政治联姻中情感因素的补充——看似离谱的传说,表明民众更愿意听到贴近普通人性的故事。
由结古镇往南返回去机场的西景线东面20多公里处,便是文成公主庙所在地巴塘乡的勒巴沟。勒巴沟的山上刻有“玉树千年唐蕃古道”几个字,沟口在禅古村,有一座平淡无奇的禅古寺。继续往南不远,峡谷两侧的山上布满五彩经幡,一条小溪从谷底流出。拐个弯,就到了文成公主庙。这是全国唯一的一座专为文成公主建的庙,其实供奉的是贝大日如来佛,所以它的名字又叫贝大日如来佛石窟寺。如果没有文成公主的名,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专门从路上折返回来观瞻,因为此类寺庙在青藏地区可谓数以万计。
文成公主庙依崖而建,面临溪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唐蕃古道的重要文化遗存之一。如今能看到的无疑大多是翻修后的建筑,与结古寺的焕然一新相比,显得格外朴实无华,虽然有三层,但不过10米左右高。庙四周悬崖和面积较大的石头上都刻着经文。殿堂正上方的岩壁上凿刻有九尊浮雕佛像,居中的主佛像便是贝大日如来,还保留了唐代美学造型的浑朴端庄。雕像对面的壁画,记录了文成公主教当地藏族人民耕作与纺织的事迹,那些多为美好的附会。
司机才旺说带我们去新寨村的嘉那嘛呢石经城看看。他父母刻画嘛呢石的地摊就在石经城旁边,他也正好可以顺道看看父母。才旺有一个弟弟根秋和一个妹妹卓嘎雍吉。弟弟结婚了,以挖虫草为主业,弟媳考了教师编制,妹妹还在上护士学校。前几年他们去杂多县,全家一天能挖四五十支虫草,大约一斤。在当地卖三四百元钱一斤,拉到州上就是2100元一斤。加上父母在石经城画石头的收入,才旺兄弟父母四个人一年可以净挣二三十万。现在石头价格下降了,但是具体多少,他没说了。
石经城是玉树最负盛名的文化遗产。我不了解石经城的前世今生,在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很具规模但又有点像城堡废墟的嘛呢石堆。看上去杂乱无章的白石头,每一块都画上了经文、佛像或图纹,附着五彩的颜料。时间累积了空间,当它们都达到一定体量的时候,就产生了崇高感。
一块被罩在亭内的石碑记载了石经城的来历,它是由嘉那活佛多德松却帕旺所创。活佛祖籍西藏昌都囊同,自幼潜心向佛,足迹遍及印度及藏地各个朝佛圣地,曾经先后在峨眉山、五台山等地学经礼佛20余载。1715年的某日,云游到结古新寨村时,他在一眼清泉中发现一块自显六字真言的佛石,于是立志修建嘛呢石经堆,以此弘扬佛法。多德松却帕旺在这里放下了第一块嘛呢石,此后300多年的时间里,无数僧侣和信徒念经朝拜、祈福许愿的时候,便往上添加几块。凿石堆经渐渐成了此地风气。年复一年,到解放初年据说嘛呢石和其他经文石已有25亿之多。旧的嘛呢堆在“文革”期间被破坏,1986年才重新开放,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如今堆积成了占地接近4个足球场那么大、高近3米的巍巍石台,又接近20亿块了。
20亿块的说法,是想当然的估算,尽管刻在石碑上,也未必作得准。不过,如果说此地的嘛呢石堆的规模是世界之最,当不是虚言。遗憾的是,我生长在祛魅了的世俗化语境中,对于此类前现代时期流传至今的制度性宗教并无特别信仰,也不太能体会其内在的激情。一种信仰能够长久流传并影响深远,与其环境与生活之间有密切关联,不在其语境中的人往往难以感同身受。以我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藏族聚居地方的经历和体验,他们信仰中关乎超越性的部分,往往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对于神圣性的守持,更多体现为心灵上的虔敬,而不是戒律条规的机械照搬。
石经城边修建了数个浮雕镀金的白塔,广场上有一对姐妹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跳舞,面前放着两个塑料箱子。穿着紫色藏裙的姐姐窈窕漂亮,穿着绿袍的妹妹顶多十来岁,粗服乱头,倒也跳得舒展开放、有模有样。她们应该是卖艺的,舞蹈未见得多高明,就是径自地跳着。下午时分,游客寥寥,半天也没见人往箱子里投掷钱币,可能现在的人都很少用纸币了。但她们好像也并没有特别在意,仿佛心态上有种听天由命的恬淡。这是此地凡圣之间的常态。
溯通天河而上
从车子往下搬行李的时候,我注意到后备厢有煤气罐、高压锅和两只工地上常见的大塑料桶,里面塞满了油盐酱醋之类杂物,还有胡萝卜和大白菜。这些东西是西宁的朋友为我们赴三江源考察准备的,当时不得其解,很快我会知道它们将派上的用途。
早上从结古镇出发,半个小时左右,抵达拉布乡的直门达水文站。这是一处重要的所在,通天河由青海入四川的半道。作为长江源头支流之一,通天河水浑浊,在山间路上看着并不宽广湍急,走到近处,看到一只绿色铁皮船搁浅在河滩,大小比照,才发现它其实相当开阔。路边偶尔可见盛开的甘青铁线莲,黄色的,小小的。日晒强烈,在六月末的称多,匍匐而努力向上伸展的铁线莲绽放出让人欣慰的勃勃生机。
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纪念碑就立在通天河畔群山环绕的一个洄流处。这个高达十多米的白石雕塑于2000年揭碑,碑顶呈两手的造型,正面镌刻了汉、藏文雕刻的碑文。我看了一个简介才知道,碑体6.621米,是长江正源地格拉丹东雪峰高度的微缩版;基座面积363平方米,象征三江源保护区36.3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基座高4.2米,是为了表明三江源4200米的平均海拔;56块花岗岩堆砌的碑体,则寓意了中国的56个民族。爬到路边山顶向下眺望,感觉纪念碑就像一个定位仪,锚定了河水的走向。
驱车前行到隆宝镇,这里曾是唐蕃通使线路上的列驿。此地有一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片缓滩湿地上,稀稀朗朗地点缀着蓝紫色的刺芒龙胆、点地梅和金莲花,无数黑白相间的牦牛在安静地吃草。大鵟盘旋在空中,寻找机会捕猎地上的鼠兔和旱獭。湿地上确实有很多孔洞,那是土拨鼠的狡兔三窟。那些呆头呆脑的土拨鼠,憨态可掬,跑起来也不快,但是总能在我试图去拍照的时候钻进洞里。湿地延伸尽头是通天河的支流伊曲河,河面开阔,散落着三三两两的斑头雁。
高原地区消耗大,清早的食物很快消化殆尽。在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路上,一个路人也没有遇见,山峦旷野中漫无止境行驶着的孤独与无聊加深了饥饿感。大约10点半左行到一处河流转弯处,我们停下来准备做饭。寂静深处的平坦之地还残留有村庄的遗迹,一个破烂不堪的低矮羊圈,几棵看上去呈四方形排列的桦树显示出它们早先是人为种植的。河岸边有很多特别光洁的大石头,应该被前人用作洗衣板或者是凳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人们放弃了这个村庄。
通天河在这里由浑浊缓慢变得清澈而湍急,在一处旧房门边找到拉则村的字样。拉则即插有长杆与经幡的石碓——藏传佛教的影响在这高原群山中也是无远弗届。高山遮挡,手机失去了信号,我后来查了一下,拉则村属于玉树市的安冲乡。这个乡有900多平方公里,但只有6000多人,是藏族银匠集中的地方,民间制作藏族饰物和打造藏刀的工艺很有名。不过,自始至终,我一个人也没有见到。
烈日高照下的静谧,有一种迷人的意境。我躺在一块光滑的圆石上,一动也不想动,看着黑魆魆不生草木的山体。空中不时有鹰鹫徘徊在山岔间,它们看到了人,准备伺机而下,寻找一些可能的食物。
煤气灶和高压锅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处——在高原,水的沸点低,不用高压锅很难把食物煮熟。我们生火煮了一锅面,又炒了洋葱羊肉和西红柿西葫芦鸡蛋兑进去。树阴下微风徐徐,听着喧腾的河水吃口热食,一天中最好的时候,难得地惬意。
心满意足地吃饱后,决定逛一逛河对面的古村落。吃饭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那个村子不同于一般的土木结构,是石块砌成。顺着河岸碎石路走了一圈,找到一架木桥,进入那个废弃的无名碉楼群。许多建筑修缮得很好,院落整饬,刻有经文的残石垒叠齐整,门口甚至有宽敞的院场,正对着河流,显示出村落曾经被人用心经营。
这个一度兴盛的村庄,如今一个人影也没有。那些石屋显然许久无人居住,人们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此岸位置较高,如同悬崖,河流就在崖下奔涌。群蜂在黄花中间飞舞,发出嗡嗡嗡的声音。那金色与黑色相间的蜂,比普通的蜜蜂要雄壮剽悍许多,能够飞到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度,是采集珍稀植物花蜜的崖蜂。我喜欢这种地方,远离喧嚣,却并不颓败,反而充满了野性的力量。
沿着通天河峡谷,从安冲乡翻山越岭过河到尕朵乡,是卓木齐格秀拉康及碉楼群。在藏语中,“卓木齐”意为大村庄,“格秀”意为军营遗址,“拉康”即神庙或佛殿。卓木齐村,相传是元代蒙古人安营扎寨的大本营,曾是元朝在称多地区设置的大驿站之一。
格秀拉康坐落于铁青色的半山,是一座被嘛呢石墙、白塔、经幡、转经轮环围着的祠堂,正在修缮中,一台巨大的黄色挖掘机就停在山脚下的路上。祠堂为一里一外,一个大套间。从外间至广间,遍地尘埃,四壁都绘满了彩绘壁画,每一个顶梁柱的顶部也都绘有彩图,笔画从着装到服饰除了藏传佛教绘画艺术的风格以外,还具有明显的蒙古族风格。所有的东西都落满了灰尘,给人感觉好像它们从一开始就是这么陈旧。
祠庙是一个叫作蕃襄雍珠嘉措的藏人所建,后由元朝的军官格秀丹增秋嘉加固修复,约有800年的历史。这两个人我都查不到来历与去处,他们如今只剩下了不容易被人记住的名字,即便在当时也可能都是地方性的小人物。祠庙里有六宝:即蕃襄雍珠嘉措的法鼓,能够象征吉凶兴衰的宝石朋多勒多囊依,供奉在佛殿圣水中的一对黑白青蛙,生长在祠庙顶上生机盎然的吉祥红灌木泽日紫寿,形状犹如缝制袈裟时留下的针脚一样整齐的祠庙顶棚求勾拉珍,以及会说话的壁画多杰森巴佛像——传说该佛像前曾堆满了杂物,佛像仙灵说道“请不要挡我”,因此得名。这些烦琐的地方性知识,外来者即便知道了,也是一头雾水,因为它们本身也是游移不定,变动不居的,那是一种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1857—1939)所说的含混朦胧的“元逻辑”的产物,尚没有被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式的分类法清晰地划定在某处,并不跟从现代以来的理性知识传统。它们的顽固性增添了世界的多样性,因而弥足珍贵。
格秀卓木齐村东侧的帮夏寺院,曾经是蒙古人所信奉的藏传佛教萨迦派(花教)寺院,也在修缮中。老喇嘛开门带我们进去,看到寺内供案上有很多黄金佛像。本地居民也许还有蒙古人的血缘,但他们身形瘦削,面目立体,从外表已经看不出来扁平大脸的痕迹。岁月悠远,不同的族群都融合在了一起。很多时候,地理、气候、食物对个体的影响,要远大于血统。
玉树市的北角处,是称多县与治多县交界处的立新乡,有着著名的长江第一湾。绕着盘旋着的路往山顶去,拐角处遇到一个全身捂得严严实实的少年,背着双肩包,卧在地上,摩托车躺在一边。他正在给一个鹤嘴锄似的小镐剔土,那是挖虫草的工具,锄头已经磨得锃光瓦亮。我问他收获如何,他没有说话,指了指张开口的背包,里面挤了几株。
正是暮色四合之际,在万丈的峰顶俯瞰山势水形,长江恢宏宁静,绕过巍峨群山,激起人的豪情。所以下山的时候,我没有走栈道,而是从侧山坡,连跑带跳滑下去。一路上点地梅怒放如同蒲团,让人心花灿烂。那些点地梅为了避开烈风,花瓣都坚实密集地挤在一起,紧紧地趴在地上。
往治多县府加吉博洛镇去的路上,看到无数的牦牛在夕阳下悠然四顾。明亮的日光在苍云背后,给云彩镶上了璀璨的银边,折射到地上的水中,为青灰的大地增添了一些耀眼的斑斓。一只狐狸懒洋洋地卧在草地,我大声地呵斥,它也无动于衷。大自然在这里呈现出悠然无畏的面孔。
治多县入口有一座轩昂的山门,上书“十全福地”,天空转为宝蓝色,那是夜晚将近前天空最后的光芒。坐在岭·格萨尔王后大酒店楼上,可以看到整个县城多是低矮的平房,远处山脊上是经年的白头雪。
从治多到杂多
清早起来从加吉博洛到多彩乡,经过一条晃晃悠悠、锈迹斑斑的铁索桥,到了群果安顿牧场。泥巴堆的墙,刷上白垩,黑窗户,顶上木头椽子则涂上一圈黄色,这是典型的藏式老房子。尕玛求开和他妹妹住的地方。
尕玛求开是县里的一个中学老师,之所以老回乡里来,因为他还是一个环保志愿者。他给我们准备了早午餐,羊血肠、风干羊肉和酸奶,都是之前煮熟的,已经放得冰凉。天气冷,毫无食欲,我削了块干羊肉,嚼不烂,生吞下去,勉强吃点酸奶。到后山溜达了一下,走了半天,看到薄薄的草皮上散乱放置的嘛呢石。毫无征兆地突然就下起了冰雹,我找了匹小马骑上,它怎么也不愿意走,我只好下来,用冲锋衣帽子套起头,怏怏而返。
藏人习惯在路口建立城镇,故其许多地名以“多”为后缀。青藏高原上有难以计数的以“多”命名的城镇,称多县、治多县和杂多县也是这样。从治多往杂多走,地势渐高,也愈加寒冷。道路蔓延,茫无一物,唯有山峦起伏,周边少有人迹。车子在茫茫大地上行走,渺小又脆弱。透过车窗,只能看到不断在视野中掠过的碎石与河流,对于整体的地势一无所知,懵懵懂懂地踏入未知的旅程,就像盲人摸象。这一点像极了命运,也许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不带地图的旅行,任由东西,不辨全景。
这就是荒原。它还不是一般的那种可以被开垦或者改造的荒原,因为它在人类诞生之前数百万年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不会退却或者消失,除非大自然本身发生剧烈的变动,比如大陆板块的挪动或者地壳内部岩浆改变流向,带来山体与水体乃至气温与气候的总体变化。人类的诞生、活动和科技的发展当然已经改变了地表和地貌的大部分样貌,但这里依然是人力尚未能征服的地方,也许永远不会被征服。荒原对人类的整体生态是有用的,却又很难利用,只能去“保护”它,其实也不是保护它,而是保护人类自己。
荒原缺少生命感,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被它的陌生风情所触动,但是很快就会在千篇一律的景观中感到无聊。目光中的景物很久都没有任何变化,山连着山,云牵扯着云,石头旁边还是石头,道路前面还是道路,天空上面依然是天空。它是重复、单调、乏味,偶尔会让人升起绝望。不过,也许它的重复、单调、乏味中就蕴含着自然本身的秘密和本质。无朋的空间中,时间似乎凝滞,外界的宏阔逼迫身在其中的人们返回到自己的内心。荒凉艰苦之地的人一旦产生某种精神上的信仰,往往会非常坚固,自然条件也许是很重要的成因。
荒原缺少生命感,并不是说它没有生命。杂多县就是以冬虫夏草闻名,产量占据了青海省总产量的大约60%。冬虫夏草就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生命,说它是草,也是虫,但其实它既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而是真菌,一种别样的生命。当蝙蝠蛾的幼虫在冬季被冬虫夏草菌(它被详尽地划分命名为肉座菌目麦角菌科虫草属真菌)侵入后,菌丝就在虫体内生长繁殖,最终导致幼虫死亡并充满菌丝。次年夏季,从幼虫头部长出形似草的子实体,就是所谓的冬虫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