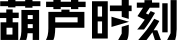一套房子,一场僵持不下的离婚官司,几乎耗尽了青桐的大半辈子,当她化身保姆,进入自己的小说世界时,她被雇主的人生经历打动,跟他一同骑着红马奔向草原……
窗外是棵玉兰树。春天时,枝枝杈杈间缀满硕大的粉白的花朵,风一吹,花儿便啪嗒啪嗒地往下掉。此时,花儿早已落尽,浓绿的叶子层层叠叠地堆砌着,一只蜗牛正从浅褐色的树干上往上爬,身后拖了一条白亮的印迹。偶尔,一两声蝉鸣从枝叶间冒出来,将这个午后抻得冗长、拖沓。
青桐将目光从树上收回来,感觉两个手臂有些酸麻,忙将手中的洗衣盆放在了地上。盆里是男人的两件白底条纹衬衫,这两件衣服面料不错,青桐担心机洗伤衣服,直接手洗的。洗净后的白衬衫挂在衣架上,时而飘荡一下,很像天空的云朵。
回到房间后,青桐到洗手盆前洗了把脸,一抬头看到了镜中的那个人,竟有了片刻的愣怔。在他们家干保姆已一个多月了,平时难得细细地照一次镜子,现在看这张脸似乎都有些陌生了。书房的一角也被收入镜中,书桌遮住了男人的半个身体,青桐只看到他胸部以上的部分。那张脸的线条很硬,皮肤黑里透着古铜色。短袖衬衫最上端的扣子没有扣,露出突出的喉结,那喉结不时地动一下,像一只呼之欲出的小耗子。青桐望着镜中那个鼓鼓的喉结,摸了摸自己的脖子,笑了笑。
主卧的门闭着,男人的妹妹小蓉在里面睡觉,难得周日她能在家里一次。
过了一会儿,主卧的门打开,小蓉打着哈欠从里面走出来,尽管她后来像补救一样捂住了嘴,青桐还是从镜中看到了她舌头上那层厚厚的舌苔。“这鬼天气,开空调凉,不开空调热,连个午觉都睡不好。”小蓉嘟囔着,“真是烦得很。”男人从电脑前抬起头:“不缺吃不缺喝不缺钱花,有什么烦的?”小蓉不满地说:“烦跟吃喝有关系吗?”男人说:“你该到建筑工地上搬一天砖,一天下来累得臭死,哪还有心思烦啊?”小蓉说:“西北市场刚开了一个六十万的店,这两天嚷嚷着要退货,就因为这事明天还得出差。”
男人小声说:“想挣大钱就得别嫌这嫌那的。”
小蓉转过脸来,说:“你听说没有,那个老尤娶了个二十来岁的小媳妇?”
“那是他的事,跟咱没关系。”
“他都奔六了吧?哼!有能耐娶,未必有能耐守住。”
男人笑说:“你倒挺能操心的。”
小蓉气呼呼地说:“哥,你还想当个长期的弼马温啊?”
男人笑笑,说:“我感觉当弼马温挺好。”
小蓉摇了摇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哥,你真能咽得下这口气?看老尤那个春风得意的劲,又是高薪又是娶小媳妇,你甘心?”
青桐不想他俩就这个话题再聊下去,忙岔开话题说:“你们听见没有,有马在叫呢。”小蓉说:“听错了吧?这可是市里啊。”
隐隐约约地,远方又传来一两声马嘶,也是,市中心怎么会有马呢?
“我妈睡着没有?”小蓉问。
“刚才还在说梦话,我再过去看看。”
老太太正在打瞌睡,腿上的毯子滑到了脚边,让那只白猫当了床铺,阳光从窗户里钻进来,恰好爬到她的脚边。青桐抬脚轻碰了一下白猫,白猫抬眼皮瞟了她一眼,继续打着呼噜。青桐将老太太扶到床上,躺好,然后将窗帘拉上半截遮挡住午后的强光。耳边似乎有一只蚊子在嗡嗡地叫,她找了一圈儿,却没有找到蚊子,这边刚坐下来,耳边又响起了嗡嗡声。
客厅里,小蓉正在接电话,男人看了她一眼,继续将头埋在电脑屏幕前。小蓉挂掉电话,急匆匆地走进自己房间,片刻后,又走了出来,“有个客户过来了,我得赶紧过去,吃饭时就别等我了。”她拿着一把小花太阳伞,边说边往外走,随着防盗门砰的一声响,人已没了踪影。
远方隐隐约约地又传来几声马嘶。
青桐打开窗户,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依旧是车辆和行人。
那颗黑色的头颅依然伏在电脑前,她走进去,问:“好不容易调休一天,也不休息一下?”他说:“先将这些马儿的照片处理好了再说。真难为这些马儿,这么多年了,在摄影师的镜头里一直是配角。”屏幕里是一匹匹马,白马、黑马、红马还有灰马,它们或站立花丛或卧于草场或仰天长啸或四蹄腾空,颜色各异、姿态多样。众马的照片中夹杂着几张新娘的照片,新娘子穿着洁白飘逸的婚纱骑在马背上,背景是紫色的薰衣草花丛。青桐知道马场在黄河的北岸,除此之外还有花场,花场种的是薰衣草、鼠尾草和百合等。那些花儿从初春一直开到深秋。
青桐说:“真想过去看看。”
“真想去?”
“嗯。”
“有空就带你去啊。”
“因为这些花儿和马儿,你才去做驯马师的吗?”
男人叹了一口气:“说来话长……”
事情最初源于一场会议。当时,这家大型私企的业务进入了短暂的低迷期,业务部有五六个业务经理便想趁此机会请假休息。请假申请需要三级领导签字才能通过,业务经理们先将请假申请交给了业务部的总监,总监签字后报给了市场总经理,最后到了公司的副总裁老尤那里。尤副总可能考虑着当时是生意淡季,便大笔一挥,批了“同意”两个字。这件事让另一个副总裁安副总知道了,安副总来公司才两个来月,正属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阶段,安副总考虑着业务经理有一大半人请了假,且集中在十天之内,这十天市场基本处在一种瘫痪状态。于是,安副总找了个机会将其中的利害关系跟董事长说了一嘴,董事长听后马不停蹄地召开了一场会议。参会的是各部门的骨干人员,在会上,董事长发了一通火,在请假申请上签字的三个领导都做了检讨,尤其是尤副总,来公司七八年了这是第一次当众做检讨。念完检讨后,尤副总准备坐下时,手中写有检讨内容的稿纸掉在了地上,他弯下腰去捡却没捡起来,还是坐在旁边的人帮他捡起来的。
这场会议之后,安副总从之前的单位陆陆续续地挖过来七八个人,这七八个人都让他放在了一些相对关键的位置。同样是副总裁,公司上上下下都是人家老尤的人,而自己却势单力孤,那不等于自己把自己逼入死胡同吗?
没过多久,公司内部进行了调整。尤副总负责事业一部,安副总负责事业二部。自分开后,事业二部又开了几家子公司,和一部比起来,二部在业绩上已经领先一步。但是,一些关于安副总的传言也在悄然滋生,比如,暗地里拉拢公司的客户、将资源占为己有、准备另立山头等,流言飘来飘去,就飘到了董事长的耳朵里。那一阵子,公司增加了新的项目,常常出现资金周转缓慢的情况,为此,董事长将员工的奖金和福利削减了一部分。对于资金问题,尤副总倒能沉得住气,安副总却不行。他知道他和尤副总都想甩掉这个“副”字,两人表面上一团和气,暗中都使出了浑身解数,老尤入职公司更早,资格上比他老,他只能在业绩上下功夫了。可是,事业二部正处在蒸蒸日上之际,却因为资金之事影响了员工福利,怎么能不让人焦躁?
那一阵子,安副总常常失眠,还脱发,早晨起床时,常从枕头上收集到一小撮头发。听闻洪家楼有位老中医,医术很是精湛,在一个周末,他开车去了老中医的诊所。老中医年近九十,须发皆白,看起来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