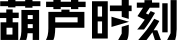在沃镇,渔船载着男人们出海,久久不回,急坏了等待父亲们归来的少年们。听祖母说,这是个劫,必须有人在台风前死去,此劫才能化掉,船才会返航。几个少年天真地设想,不如就在镇子里寻找一个“替死鬼”……
上
1
“瓦婆又在海边跳起了傩舞。”这是我来到沃镇后听得最多的一句话。
我在两天前来到了沃镇,镇上的人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这个外来者,似乎我的到来冒犯了他们,他们并不掩饰自己的态度。他们在研究我的同时我也在研究他们,他们的直率让我显得并没有过于无礼。他们眼中传递出来的含义很宽广,一如沃镇东、南、北三面的大海那样深不可测。我抹了一把脸,确定脸上无任何异常,异常的只是他们毫无理由的奇怪目光。也许他们看见外来人的机会并不多,我是这么想的。
据我观察,镇上人大多是沉默的,他们显得有些神不守舍,却又对外来者过于警惕。只有在谈论某件事的时候认真到几乎虔诚,比如——瓦婆又在海边跳起了傩舞。
我再一次听到这句话时是在汉漓家里。汉漓是我在沃镇唯一的朋友,他独自居住在海边一个木头房子里,父母与妹妹住在镇上,他只在父亲捕鱼归来后才回家一趟。“像来走亲戚的。”父亲总这么说他。而他对此无动于衷,继续享受他在海边的日光浴。而大多数时候,他在木屋旁边的小树林里,找两棵稍微高大和结实一点的松树,在中间吊一铺网床,躺在上面,咬一根松针,摇摇晃晃,无所事事。
无所事事只是表面看来如此,据我所知,他正在策划一场逃离,逃离沃镇。这是十九岁的汉漓正在密谋的一件大事,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离开这个鬼地方,越远越好。当然,这么重大的事情自然少不了他的好朋友卢三谷参与。而他们之所以把沃镇叫成鬼地方,是因为瓦婆。他们从懂事开始就把那个老女人定义为鬼,只因每次瓦婆跳起傩舞,这镇上必定要有人死去。
“又要有人死去了。”三谷说。太阳刚落山他就来到了汉漓的木屋里,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个子瘦瘦小小的,眼睛笑眯眯的一个大男孩,嘴巴总是微微张开,像在笑着。
“很久没见瓦婆跳傩舞了。”汉漓说。
“傩舞?”我说。
“说是舞,不过是一个老婆子戴着面具的手舞足蹈,沃镇人说这是瓦婆和天地神灵的对话,谁都看不懂,可又传得头头是道。”汉漓说。
“上一回跳是几年前,三天后梨花家的二婶子就死了,之前人还好好的,能说会笑,半夜自己一个人划着小船出海,第二天船回来了,人却没了。”三谷哪怕在说死亡的时候,仍然给人高高兴兴的感觉。
“瓦婆真那么神?”我感到好奇。
“没那么神,不然她该能说出这次死的会是谁。”汉漓说。
“那是天机,通俗点儿说就是一种职业道德。”三谷深信不疑。
“瓦婆多大年龄?”我说。
“我阿婆说她超过一百岁了,像只老海龟,连她住着的老宅子都像一个老龟壳。很少有人看见过瓦婆,她几乎不出门,出门总没好事儿,年轻人都当她鬼一样地躲着,生怕沾了晦气。镇上人都说她长了一张,一张,古怪的脸。”三谷努力想着形容词,挠了挠头。
“我从不信那样的鬼话。”汉漓讥笑一声,他在雕刻一块巴掌大的木头,看不出是个什么玩意儿。汉漓的手指特别细长,长得挺好看的,像一双女人的手。
“她靠什么生活?”我继续问。
“镇上的老女人把她当神一样地供着,少不得她吃喝的东西。”三谷说。
“要来台风了。”汉漓有些烦躁地打断我们的对话,他停下手中的活计,看向窗外。不远处便是大海,能听见海浪像无数只小海怪那样哗哗地冲上沙滩。
“天气预报说了,三天后,台风‘乌卡拉’会来。”三谷说。
“这屋能经得住台风吗?”我环视这个简易搭建起来的小木屋,充满了担心。
“我会赶在台风到来前离开这个鬼地方。”汉漓认真地说,又刻了一刀。
“如果瓦婆的预言是真的,你们认为会是谁死?”三谷显然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
“没有人会死。”汉漓把刻下的木屑吹掉。
“也不一定。”三谷说。
“那你说说看,会是谁死?”我说。
“我把沃镇的人都研究了一遍,觉得有可能死掉的只有四种人。”三谷卖起了关子。
“哪四种人?”我说。
“第一种老人,第二种病人,第三种出海人,第四种仇人。”三谷掰着手指一口气说完。
“沃镇就百户人家,一目了然,看不出谁老弱和生病到快要死的。你看东伯,七十岁了还出海,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没空死。”汉漓说。
我点点头,说了一句连自己都觉得有哲理的话:“死是个奢侈品。”
“那还剩下两种人,出海人,还有仇人。”三谷说。
“海面挂了风球,渔船明后天就会陆续回来。而至于仇人,我还真没觉察出沃镇有人反目成仇要干死对方的。要真有,也是你小子挑拨离间。”汉漓开起了玩笑。
“还真有。”三谷说。
“谁?”汉漓说。
“霖洁和她的画家情人。”三谷说。
“我说是你小子妒忌到神志不清了吧,镇上人都知道霖洁爱那画家爱到要死要活的,哪来的仇人。”汉漓说。
“你不懂霖洁。”三谷反驳。
“我只懂你,你喜欢霖洁。”汉漓冲我挤了一下眉毛,我立刻做出一副八卦的样子。
“那个画家是个混蛋,他当霖洁是什么了?用人吗?”三谷越说越气。
“人家两口子的事情,轮不到你来评判。”汉漓说。
“可霖洁是我朋友,她有一天和我说要把自己杀掉,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再也忍受不了这么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有一天画家会离开她。又有一天她悄悄地告诉我说她改变主意了,决定把画家给干掉,这样他就会永远属于她了。”
“可现在他俩还好好的,我偶尔看见他俩来海边散步,他用沙子堆城堡,完了她帮他擦干净手,像小孩那样宠着他。别太相信女人说的话,那不过是些气话,就像我母亲每次和我老鬼吵架都说让他死在外头别回来了,可一到晚上十点老鬼不回家,她就丢了魂似的。我敢说你钟情的霖洁姑娘,只要画家搂着她,给她说一堆甜言蜜语,她又会爱得无怨无悔了。”汉漓说。
“不是那样的,她真会动手。”三谷争辩。
“那我们打赌。”汉漓说。
“我懂她。”三谷使劲点头,像在说服自己。
2
我到沃镇的第二日,天气仍然晴朗,仿佛台风只是一个谎言。海滩上明显比昨日热闹,像在举行什么仪式。
“是甩喜鞭,台风前有渔船回来就用喜鞭报喜,感恩天地神灵的庇佑。”汉漓告诉我。
这是我第一次看做海人甩喜鞭,对于沃镇人而言这是一个神圣的仪式。执鞭人叫通伯,五十出头,人长得不怒自威,像一尊门神。
巳时刚过,腰间绑着红绸的通伯光着双脚站上了临时搭建的高架台,左手叉腰,右手执鞭。鞭长七米,生铁打造而成,重达八斤,像一条黑色蟒蛇盘绕地面。
海滩上的人越来越多,一些是来等亲人返航的,另一些是来看甩喜鞭仪式的。远远地,海面终于看到有渔船返航。通伯也早早瞧见,可就是摆着架势纹丝不动,只待报喜之人奔向高架台正式报来,方才活动身体,准备起鞭。
也不知通伯怎么地就把铁鞭抡举在头上转动了起来,他的身体刚中带柔,随鞭有节奏地晃动。铁鞭在他头上逆时针转动,数圈后他突然改变方向反手一甩,鞭在空中发出“啪”的一声,像炸响了个大炮仗。鞭不歇停,继续转动,直到甩出八个响鞭。休息一分钟,再来八个响鞭,第三轮时仍然虎虎生风,气势毫不减弱。
海滩上好不热闹,陆续返航了数条渔船,幸运的人们盼回了亲人,喜鞭声不绝于耳。汉漓的母亲和妹妹也来了,可她们的希望落空了,一直等到未时,太阳把她们烤得头晕晕,汗津津的,可连父亲船只的影儿都没见着。而我的朋友汉漓此刻正躺在松树林里的网床上,摘一枝茂密的松枝挡住眼睛,像是睡着了。等不来他父亲渔船的母亲和妹妹失望而归,在经过松树林时抛落了一串叹息。母亲站在儿子的网床前左右为难,想要离去,又不甘心,只在最后所有的委屈与指责化为一声哽咽——你父亲的船还没回来……
松针挡住了汉漓的眼睛,只见他的嘴巴微微张开,像熟睡的样子,又像在微微笑着,让我想起了三谷。直到他母亲和妹妹离开,我看见他起伏加剧了的胸膛。我悄悄地走开。
海滩上的人越来越少,沙面徒留深深浅浅重重叠叠的脚印,欢乐的,悲伤的,失望的,着急的。
海水微微涨潮,我站着的地方已被海水淹没了双脚,小小的浪头一下又一下地抚过我的脚踝。每次海水退去,我的脚又陷入了沙中更深一些,像踩在柔软的棉花堆里。日头依然很猛,晒在海面上,银晃晃一片,我有了少许晕眩感。海边风很大,背部却火辣辣的,汗水滑落,像有无数只蚂蚁爬过。我把左手食指伸进嘴里,吮了一下,咸咸的,略苦。
“小心会中暑。”汉漓不知何时来到了我身边,太阳照在他脸上,他不似海边人的黝黑、强壮,反倒略显苍白、瘦弱,带着一些书生气。
“你中过暑吗?”我问他。
“有,可那时我不晓得是中暑了。”汉漓眯起眼睛看着大海的远方,海天交接处一艘渔船也看不见,“那一年我九岁,跟着老鬼出海,和我同龄的几个小伙伴也被带上了船,按父辈们的要求提前体验出海。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沃镇的男生,小学毕业就跟着父亲出海的多的是,那比继续上学更能令他们高兴,就像把鱼儿放回大海那样自然合理。只有我和三谷反抗,出海对我俩来说是噩梦,我们晕船,面对满船的小鱼小虾不知所措,活像两个另类。在沃镇,不上船的男人相当于废物,我和三谷仿佛窥见了自己未来废物的一生。当然,我们的父辈也预见了这一点,他们要给我们一点儿颜色瞧瞧,于是在一次闯祸后,他们逮着了理由把我俩分别绑在一张椅子上,椅子放在甲板中间,一晒就是三个钟头。”汉漓眯着眼,仰了仰头,汗水从他额头滑落,他用力深呼吸,仿佛这会儿他还被绑在那张小椅子上。
“三个钟头。”我闭目低语,努力去感受三个钟头被绑在大太阳底下的滋味,而那会儿,汉漓正身处茫茫大海的一艘渔船上。
“头一个小时三谷还不断地和我说话,后面我们都渴得说不出话来了,嘴唇爆裂,喉咙干得想咳又咳不出来,整个人像快被点燃了。我开始处于晕眩状态,迷糊中我听见三谷说‘快看,有海妖’。我一转头,看见三谷的脑袋像被拍死的海蛇软塌塌地耷拉在一边,嘴角溢出一些白白的东西。我拼尽全力喊了一声‘海妖来了——’就又迷糊了过去。”
“为什么喊‘海妖来了’?”我觉得好笑。
“我那会儿什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三谷说的‘海妖来了’。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发高烧,好像真的看见海妖了,又或者在三谷说有海妖时我就深信不疑了。不管怎样,我那句‘海妖来了’还挺管用,父亲们都跑了过来。那次后,我俩再也没被体罚过,只是更坚定了父辈们把我俩定义为废物的看法。也好,我这个不被待见的垃圾因为不配上船,反而顺利读到了高中毕业,还是在县城里读的,认识了你小子。”汉漓擂了我一拳,呵呵笑了下,又说,“我那时才知道沃镇是多么小。”
“因祸得福了。”
“也不见得,我高中毕业后,老鬼又把我出海的时间提上了日程。我记得有一晚他喝醉了酒,他说他怎么就生了我这么个儿子,说沃镇的男人就应该上船,死也该死在海上。我俩第一次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拿最恶毒的话骂对方,差点儿动起手来,他一副恨不能掐死我的模样,可是我长大了,比他还高,不再是那个任由他绑在椅子上晒太阳的废物。然后他就喊我滚,从那天起我就想离开这个鬼地方。”汉漓用力踢了一下海水,海水已涨潮到膝盖了,“两天后台风就来了,我要赶在台风到来前离开。”
“恨你老鬼吗?”
“谈不上,这是命,沃镇人的命。生来只知道出海打鱼,从没想过还可以有另一种生活,从不肯接触外面的世界,他们宁愿相信一个满口胡言的鬼婆子的话。”
“你相信瓦婆的预言吗?”我的脚陷进了柔软的沙子中,痒痒的。
“我不信。”
“可三谷说之前她的每次预言都灵验了。”
“那不过是巧合。”汉漓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他汗津津的脸转过来看着我,嘴角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句子仿佛在牙缝里被他给挤了出来:“今晚我就要拆穿谎言,敢不敢跟我去西边洞,就是那鬼婆子住的地方?”
“为什么不敢?”我说。
“算你有种,我之前叫过三谷去,这小子一开始答应了,后面又了。他对鬼婆子的那套浑话深信不疑,今晚我俩得带上他一起。”汉漓的眼睛闪亮闪亮的,一滴汗珠滑落至他眉心,他甩了甩头,汗珠落入海里。
海水涨至大腿根部了。
3
晚上九点,我和汉漓离开了小木屋,朝西边洞走去。当晚的月亮被云层遮盖了,夜色显得比平时更为深沉,我们打着手电筒走路。在一条必经之路的三岔路口看到一个人影,是三谷。他正耸着肩,双手插裤兜里,无聊地踢着路边的小石头。我们走过的时候他一言不发,默默地跟在我俩身后,像多么地不情愿。
“胆小鬼!”汉漓故意大声说笑。三谷似没听见,沉默着。我也沉默着,这样的夜晚注定是一个严肃的夜晚,所有的轻松愉快都与之不匹配。我们三个很快就达成了默契,谁也不说话,勾着头朝前走。
瓦婆住在镇西一个叫“西边洞”的老宅子里,门前是海滩,大片枯萎的红树林从半退潮的海面上露出手臂长的黝黑树干。树干以各种形态分着叉,黑夜里像一群无名生物挥舞着长短不一的手臂伸向天空。
“别靠近!”三谷忽然开了口。
“什么?”汉漓没听清。
“我说,别靠近那些死掉的红树林。”三谷小声说。
“它们怎么了?”我问。
“听大人说,海上遇难者的尸体经常被海浪推到这里来,就在那些树干中间。”三谷朝那片黑黑的海滩指了指,“每次退潮大人都不许我们到这来,说这里面古怪,藏有沃镇所有人的秘密。”
“你来过吗?”我问三谷。
“来过。”三谷犹豫了一下。
“你小子这牛皮吹得真像是真的。”汉漓取笑他。
“是真的。”三谷加重语气。
“什么时候?”汉漓问。
“我不告诉你,反正就是有。”三谷显得有些激动,他停下来瞪着汉漓,一副想打架的模样,可他的嘴巴习惯性地微微张开,眼睛仍然是笑眯眯的,看着有几分滑稽。
“到了吗?我看这路越来越不好走了。”我咳嗽了一下,转移他们不愉快的话题。
“前面就是,有一棵老榕树那儿。”汉漓走在前头,我紧跟着他,三谷在我们后面两三米的地方不紧不慢地跟着。
我看见了那棵老榕,腰杆子要三人环抱的粗大。汉漓用手电筒照着它,光晕慢慢地往上移。老榕的主干分了叉,一半独立生长,另一半嵌进了旁边一间矮矮的房子墙壁中,仿佛随时要把房子劈开掀翻。长长的深褐色须藤往下垂,像密密麻麻的帘条。手电筒的光晕继续往藤条里面探索,冷不丁照到了一个人身上。是一个穿着灰色长袍的老人,剪着短短的头发,耳垂上挂着一对大大的银环,脸上的皱纹比那棵老榕的还要深刻,乍看之下分不出是男是女。
“别照了。”三谷上前一把拍掉汉漓手中的手电筒,“是瓦婆。”
手电筒掉到了石子地面,一束光射向瓦婆的脚底,看见了她穿着的小小黑布鞋。
黑暗中谁也没有说话,瓦婆朝着我们的方向定定地看了几秒,然后转身朝她的老房子走去。我们跟了上去。
瓦婆的身板子挺得老直,走得很慢,小碎步。我们几个跟在她身后两米处,不发出一丝声响,像三只夏夜里机灵的老猫。
薄薄的木门被她推开,发出长长的“吱呀”声。屋里墙角处挂着一个小小的灯泡,周围一下亮堂了起来。瓦婆走到厅堂左侧一张大椅子上,瘦小的身子慢慢地坐了下去。她一直闭着眼睛,像在打盹,呼吸均匀,能看着稍稍起伏的身体。我打量着她,她看起来和普通老人并无不同,却明显有不同之处,可又说不上来。她就那样闭着眼睛安静地坐着,无视我们三个的存在。我们三个像傻瓜一样定定地站在屋里,也不懂站了多久,保持着一个姿势,好像可以就这么一直站一个晚上。
屋外野猫适时地喊出一声尖细的叫声。我们三个似从梦中醒来,我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珠,奇怪,手心是冰凉的。
我看着汉漓,暗示他该说些什么,毕竟是他带我们到这来的。汉漓却扯了扯三谷的衣裳,示意他来说。三谷翻了一下白眼,想拒绝。我冲他讨好地笑笑,他于是又看了汉漓一眼,鼻子里无声地哼了一下,这才舔了舔嘴唇,结结巴巴地说明了我们的来意。
眼前的老人似没听见三谷说的话,她仿佛回到了自己千百年的沉睡中去。三谷又壮起胆子恭恭敬敬说了句:“瓦婆,请告诉我们,真的有人要死去么?能告诉我们是谁么,哪怕提示一下都好?”
屋里很静,屋外野猫凄厉的叫声一阵阵传来,让人心烦意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