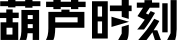十多年前那个炎热无比的夏天,我蛰伏在号称西部最现代化的数字档案中心民国档案室里摘录档案。墙上粗黑字体的“温馨提示”后面附了三个醒目的感叹句:不准拍照!不可下载!不提供远程访问!我默默存放了手机,开始了让人崩溃的工作:把毛笔书写、繁体行草、从右到左自上而下排版的各种书证函件等文档资料,如同考古般逐字辨认后转存到笔记本电脑里。作为延期毕业的中年在职博士生,我深知一纸学位证书背后的辛酸与无助。学术江湖里那句“没有论文的研究生如同没有子嗣的妃子”的调侃,真实而残酷。对于思想史的博士来说,缺乏一手史料,别说妃子,想做个卑微的嬷嬷都难啊。
我查阅的是抗战时期一所由南京迁建于重庆的国立专科学校的档案,属于教育史的范畴。提及民国教育,人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西南联大等名校“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的豪迈与成就。正如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认为的,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毕竟,国家才是理解全部教育本质的核心所在。风雨飘摇的民国政府根本无力为教育提供像样的支撑。我从眼前那万卷蒙尘的档案中窥见,民国教育的真实面相其实是相当不堪的。经费的奇缺、资源的匮乏、时局的动荡,教育是那么无足轻重,那么孤立无援。抗战爆发后,烽烟四起的中华大地更是难以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通过档案回望八十年前的抗战教育,心里多少有些苍凉和压抑,直到我看到一份申请函件。吸引我的不是其文笔的优美或字体的飘逸,而是案主曲折的求学经历。我索性检索了与之相关的全部档案,共五份。通过这些支离破碎、长短不一的文字,拼凑起了他人生最后一段斑驳而真实的时光。
案主名叫史鸿广,男,甘肃泾川人,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初中毕业于省立西安第一中学。从其呈给国立中央工校的函件略知:史鸿广参加学校在汉中考点的现场招考,但发挥失常未获录取。随后以少数民族身份请求甘肃教育厅保送入学,教育厅转函托请重庆蒙藏委员会保送。在那个没有电子邮件和网上申报系统的年代,文牍往来颇费时日。千里迢迢到达重庆的史鸿广身陷困境,“回家不得,欲进他校不能,在此进退两难之际,想绝不令生游离失学走入歧途”,于是鼓起勇气于九月三十日给校长写信求助,恳请准其入校暂住,以免流落街头。
在档案附页中找到了校长的回复。我估计,这封函复应是校务秘书誊抄后保存的。回信不长,但却体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温情与真诚。校长在表达了对其困难情形的不胜同情之后,建议去他校就读。如经济困难,可进省属高中,因为战时各校均有公费生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