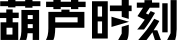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流行了百余年,各家的注解评释已然是洋洋大观,笔者近来研读此书,偶有一些感触,略述如次,或亦有助谈资。
一、“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本意
刊本《人间词话》第七则云:“‘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将宋、张二人的名句相提并论的做法应是受宋人的影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遁斋闲览》云:“张子野郎中以乐章擅名一时,宋子京尚书奇其才,先往见之。遣将命者谓曰:‘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屏后呼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遂出,置酒尽欢,盖二人所举,皆其警策也。”具体到“闹”字,清人也明确表彰过,刘体仁《七颂堂词绎》云:“一‘闹’字卓绝千古。”刘熙载也认为“闹”是“极炼如不炼”的“触著之字”(《词概·词曲概》),不过,和王国维一样,他们对“闹”的评赏可能都是基于一个误解。
宋祁《玉楼春》词云:“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词的上片主要写春日风光,下片写珍惜光阴、及时行乐之意,属于典型的上景下情的布局。“绿杨烟外晓寒轻”与“红杏枝头春意闹”为对仗句,“绿杨烟外”限定了“晓寒轻”的空间范围,“轻”描述“晓寒”;对句与出句的语法结构保持一致,“红杏枝头”为空间状语,“闹”修饰“春意”。“春意闹”,单独来看,似与常言之“春意盎然”无异,然而春意毕竟是抽象的,人们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物象才可清晰感受,“红杏枝头”实际上就承担了这个功能,因此,“闹”首先应是形容红杏开满枝头。
“闹”有密集之意,其例颇多。唐人诗云:“高枝闹叶鸟不度,半掩白云朝与暮。”(严武《题巴州光福寺楠木》)“洞庭鱼可拾,不假更垂罾。闹若雨前蚁,多于秋后蝇。”(李商隐《洞庭鱼》)北宋时期的用例,如“宿蕊斗攒金粉闹”(晏殊《渔家傲》)、“丛头金菊层层闹,木末丹花艳艳红”(韩维《次韵和相公九月八日所赐诗》)等皆是。宋祁的同乡晚辈郑獬,在诗中亦屡用闹字:“菊花又密闹,烂若金缕堆。”(《菊》)“春衫不惜露痕污,直入闹花深处来。”(《探花》)“晚花纤丽金靥闹,平莎蒙密绿发稠。”(《次韵程丞相重九日示席客》)其《昔游》诗中“绿杨阴里穿小巷,闹花深处藏高楼”一联就和宋祁《玉楼春》中的对仗更相似了,并且,这些“闹”所形容的往往就是花叶。推测起来,宋祁本意应是用“闹”表明枝头红杏的密集,这是当时作品中的常见做法,但为了与上句对仗工稳,不得不调整语序,将“闹”置于句末,这样就与红杏产生了距离,反而与“春意”紧密相连,好像是在形容抽象的“春意”。而后世对“闹”的字义认识已趋向“扰嚷嘈杂”一端,“密集”之义则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故李渔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若红杏之在枝头,忽然加一‘闹’字,此语殊难着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之见也。”(《窥词管见》)语序调整与词义窄化两个因素的叠加,让“闹”字成了论者关注的焦点,由此又引发了对其中修辞手法的分析。钱锺书《通感》即举宋祁词句为例,说用“闹”字“是想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绘成好像有声音,表示他们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用现代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这两句都是‘通感’,或‘感觉移借’的例子”。笔者以为,密集容易导致混乱无序,而混乱往往伴随着吵嚷喧杂,这里确实有一个源出日常生活经验的心理联想机制在起作用,但一定要说宋祁运用了移借视觉与听觉的修辞手段,恐与实情不符,他在下笔时,恐怕也没料到“闹”字会受后人如此好评。
按照一般的理解,王国维的“境界说”与叔本华的学说有渊源关系。叔氏认为世界是意志的表象,对应到宋祁的词句,我们似乎可以说“红杏枝头”就是一种表象,由它表征的“春意”依然是表象,而催动花开、造就春意的“意志”仍难以捉摸。词中的“闹”字,王国维无疑是从“扰嚷喧闹”之义上去理解的,所以他会认为,“闹”字使得正在作用着的“意志”显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词人已经把握到了表象背后隐藏的“理念”,并“镌诸不朽之文字”(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这就写出了“真景物”,故而“有境界”(《人间词话》)。他之肯定“弄”字,也当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过,若搁置叔本华的学说,字词批评原本就是中国古代诗文评中的大宗,前引刘体仁、刘熙载之言俱是。又如明人李腾芳评欧阳修《醉翁亭记》“有亭翼然立于泉上者”:“一‘翼’字将亭之情、亭之景、亭之形象俱写出,如在目前,可谓妙绝矣,此等不可胜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