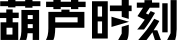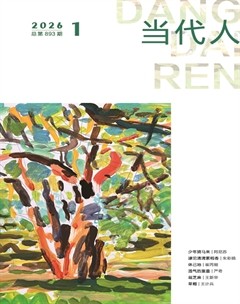一场秋雨过后,深蓝的天空上,不见一片云,西日嘎村静悄悄的。阿米站在炕上,打开窗户,拿着喷壶往玻璃上喷水。此时,几个男孩正在村前的毕勒古泰山上玩耍,他们的声音时不时传过来。额吉坐在凳子上,“咯噔咯噔”地踩着缝纫机。她转过脸,柔声说:“儿子,出去玩一会儿吧。”阿米用废报纸均匀地擦拭完玻璃,从炕上跳下来说,“额吉,我还要背诵课文呢,老师明天检查。”额吉停下手里的活儿,起身亲吻了一下儿子的额头,然后拎着奶桶走出屋子,从牛棚里牵出一头母牛,开始挤牛奶。阿米坐在窗台上,看一会儿亮堂堂的玻璃,又看一会儿天空。一行大雁慢悠悠地向南飞去,仿佛清澈的湖水里自由游动着的鱼。
今年暑假,额吉赶着牛车,牵着两匹白马,把阿米从老家带到西日嘎村,住进了舅舅家的房子。舅舅在巴镇开奶茶馆,一家人在镇上定居,很少回村里。额吉抚摸着阿米的头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额吉的眼泪掉在阿米的肩头,他假装没有察觉到,抱紧了额吉。
牛棚后面的院子里搭建起了一个小马棚,拴着两匹白马。阿米跳下窗台,给马换了两桶干净的水。他很久没有骑马了。白马看向他的眼神里充满期待,但他不想跨上马背。家乡一位独居的老额吉经常坐在村头的大杨树下,唠叨着:“哎,霍日嗨,霍日嗨……”老人家的孩子们这几年相继离世,她的老伴儿也在今年夏天的雨声中合上了双眼。起初阿米不知道“麻木”是种怎样的感觉,但现在他体验到了。以前让他感到愉悦的事情,无法再让他提起兴趣。他在额吉面前小心翼翼地收起情绪,更加努力学习,努力干活儿,努力不让额吉担心……
秋天的夕阳比夏天落得快。朦胧的暮色很快被黑夜取代。西日嘎村上空布满明亮的星星,镰刀似的月亮孤悬其中。去年秋天,阿爸开着拖拉机带阿米去草场割牧草。秋阳下,他清楚地看到阿爸的汗水闪着金光。阿爸挥动镰刀,有节奏地弯腰割草,草一层一层地躺下。他记得更小的时候,阿爸用强壮的手臂把他举起来,抛向空中,再接住。他无论被抛出多高都不觉得害怕,因为阿爸的手臂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但从今年春天以后,他再也见不到阿爸了。
一天下午,阿爸开着拖拉机拉着几只羊,往镇上走。拖拉机缓缓爬到一个长坡的中段时,一辆摩托车突然从坡顶迎面俯冲下来,眼看就要撞到阿爸的拖拉机。阿爸猛打方向盘避让,不料拖拉机翻了一个大跟头,把阿爸扣在下面,骑摩托车的男人撞在坡下的一棵树上。山腰上的牧羊人看到了这一幕,但已营救不及。两个人当场都没了。骑摩托车男人负全部责任,他没有驾照,也没戴头盔。可当阿米的额吉看到骑摩托车男人的妻子后,心软了。女人坐在轮椅上哭泣,旁边站着四岁的女儿,眼里充满恐慌。听说那天男人刚从镇上给妻子买药回来,因为妻子的疾病,他们欠下很多债,就连住的房子也多处漏风漏雨。
阿爸走后,额吉常从梦中哭醒。阿米总是幻想着阿爸开着拖拉机从村里的土路驶过。阿爸还会站在草场上等他,可当他走过去时,阿爸又转身离开,他怎么也追不上阿爸的脚步。他和额吉无法继续生活在满是回忆的家里。额吉紧抱着阿米说,“你阿爸还没去美丽的天堂德巴占呢,他舍不得我们,他想看着你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额吉的身体不停地抖动。阿米望向远方,连绵的群山飘忽不定。
阿米即将升入四年级,而村里的小学只能读到三年级,往下念书就得去更大的村子。额吉征求过儿子的意见后,卖掉羊群,锁上房门,来到了西日嘎村。额吉原本怕儿子不同意,阿米却说:“额吉不怕,以后有我呢。”阿米在路上看到,家乡的山草与西日嘎的山草连在一起,家乡的云也一路跟着他们飘到了西日嘎草原。
舅舅家的土房长期无人居住,但是房子、院墙和牛棚还在。舅舅从镇上回来,帮他们新盖了马棚,小院俨然有了生活的气息。额吉手巧,在家里开起了裁缝铺,给村里人缝制袍子。阿米写完作业就主动干家务活儿。额吉在儿子面前没有再提起过阿爸。但阿米能感受到,额吉努力保持平静的面容里隐藏着更深的悲伤。他察觉到了这一点,便经常用夸张的笑容来逗额吉。时间久了,他把这种笑容无意间带到了学校。同学们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坐在后排的图布新和全山两个男生,给他起了个外号——怪胎。即使老师第一时间进行了批评,也没能堵住这两个男孩的嘴。他们背地里继续用“怪胎”称呼阿米。
阿米并不在乎,也不辩解。五岁那年夏天,他跟阿爸一人骑一匹白马,在辽阔的草原上游荡。当他们穿过一片白杨林后,眼前出现一条十几米宽的河。阿爸一边唱着乌尔汀哆,一边骑马蹚过河水。河水很深,几乎没过了马腿。阿爸率先到了对岸,他掉转马头,扬着手说,“儿子,要做一个勇敢的男子汉。”阿米握紧马缰,用脚后跟轻轻点了几下马肚。白马缓缓走进河水,走到一半却停住了。阿爸跳下马,站在河边满眼期待地看着儿子。阿爸曾说过,马儿也跟人一样,有时也会闹情绪,或胆怯,这时要充分信任并鼓励它。阿米低下头,看到几条鱼正从马肚下逆流而上。他深吸一口气,抚摸着马的脖颈,学着阿爸的口吻说:“你要做一匹勇敢的马。”白马在小主人的鼓励下抬起腿,划开了水,紧走几步上了岸。阿爸放声长笑,他也跟着笑起来。阿爸说:“草原上的男人一定要勇敢。”那时,他不懂阿爸的意思,只觉得阿爸说的肯定都对。阿爸还经常教他搏克。等他有模有样地学会过肩摔时,阿爸故意被他摔倒在地,又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这些事情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一次语文课上,阿米的作文得了“优”,老师点名让他上台朗读。阿米写了阿爸教他骑马的经历,但上讲台后,他却怎么也读不出来,急得哭出了声。老师没有责怪他,安抚了几句后让他回座位。几个学生偷偷捂着嘴笑。图布新夸张地张开嘴用极小的声音说:“怪——胎。”他的眼泪怎么也收不住了。在学校,图布新和全山不敢过分欺负他。但一放学,他们先跑出校门,在一片白杨林里截住他。他们用小石子打他的书包。他想起额吉的嘱咐,不想惹事,只管低头继续走自己的路。这让两个男生越来越恼火。有一次,他们躲在草丛里,等他路过时突然跳出来吓唬他,把他的书包扔到高高的树杈上,嬉笑着跑了。他爬上树取书包时划伤了胳膊。额吉问原因,他含含糊糊地说,跟几个同学在树林里奔跑时不小心划伤了。他知道,额吉希望他结交一些新朋友,而不是在班里不受待见。他不想让额吉担心,更不想增加额吉的悲伤,他希望额吉能开心。额吉不知道,擦玻璃那天,从山上呼唤阿米的正是图布新、全山他们。
阿米放学后,绕开白杨林,沿着毕勒古泰山脚一条偏僻的小路回家。这条路,一边是山,一边是白杨林,除了几个往南放羊的牧民外很少有人走。落空几天的图布新和全山不甘心,偷偷跟踪他,还是把他截住了。图布新两手叉腰,说:“你这个怪胎,不许走我们村里的路,除非给我们好处。”他们把阿米的书包和口袋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好处”。他们让阿米明天带零食、零花钱,还威胁他不能告诉大人,不然就狠狠教训他。阿米看着遥远的天空,一声没吭。
晚上,阿米在两匹白马前站了很久,他没有把这事告诉额吉。他在额吉裁剪布料的声音中进入了梦境。他走在迷蒙的群山之中,一个穿着白色袍子的男人出现在前方,他背对着阿米,四周飘荡着雾气,阿米看不清他的样子。男人很快就走远了,阿米想叫住男人,但无论怎么努力,嗓子发不出任何声音。阿米被潮湿的热气包裹住,他越着急就越透不过气来。男人的身影彻底消失了,阿米在山间的草地上循着男人消失的方向使劲儿奔跑,跑着跑着,他的双腿陷入了泥沼,他的身体开始下沉,眼瞅着泥水即将淹没他的脑袋,他大喊救命。这时,他的身体被一只手拽了出来。他从梦中醒来,看见额吉正轻轻地拍着他的胳膊,轻声说:“米尼呼,别怕别怕,额吉在呢。”
“米尼高勒乌噜咧……”阿米在额吉轻柔的歌声中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没得到“好处”的图布新和全山十分恼火。他们从后面追上来把阿米按在草地上,往他嘴里胡乱塞满杂草。阿米的两只胳膊无法动弹,两脚乱踢。图布新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背,说:“如果明天还不带钱来,就让你吃牛粪。”两个男孩骂骂咧咧地走了,阿米用手抠出杂草,呕吐一阵,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了。他的嘴里充斥着又腥又苦的味道,怎么也吐不干净。
阿米到家时,嘴唇香肠似的肿起来。额吉问怎么了,他说可能是过敏了。额吉赶紧拉他到卫生所打针、抹药。阿米在家休息了两天。班主任来到阿米家,给他补落下的功课,临走前,跟阿米的额吉站在院门口聊了一阵儿。班主任走后,额吉茫然地望着前方,直到阿米走过去拉住她的手,她才缓过神。额吉蹲下身,用力抱抱阿米,看着他的眼睛说:“儿子,你有什么委屈都跟额吉说,有额吉在,你啥也别怕。”他边点头边擦拭额吉的眼泪。额吉摸着他的头发说:“你阿爸也一直在保佑着我们呢。”
远处的群山掩映在朦胧的夜色中,轮廓像铅笔画出来的一样清晰。月光如鲜奶般纯净,两匹白马发出“噗噗”的鼾声。阿米被这幽静的夜晚打动了,他的心里流淌着一条温暖的河流。
期中试题里出现了命题作文《难忘的瞬间》,阿米写了阿爸教他搏克的事。判好的卷子发下来后,阿米的作文得了满分。老师再次让他站在讲台上朗读作文。这次,他没有紧张,也没有哭。他透过玻璃窗看到了毕勒古泰山。山坡已经披上秋日的荒草,这座山并不高,却因上空飘荡着一团团纯洁柔软的白云,显得离天很近,亲切又威严。他觉得阿爸肯定来到了西日嘎草原。额吉说过,阿爸会远远地看着他。他浑身上下充满力量,攥紧拳头字正腔圆地大声朗读。等他读完,教室里变得十分安静,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当天下午,图布新和全山把他拽进白杨林,先骂了几句,接着开始动手。全山把他的双手扭过后腰,说:“你不是会搏克吗?来呀!”图布新抓住他的裤腰带往下拽。斜阳在树林里射出无数条橘黄色的直线。透过密林,毕勒古泰山的轮廓若隐若现。“儿子,要做一个勇敢的男子汉。”恍惚中,阿爸的声音刺破重重雾气从群山深处传来。他猛地一晃肩膀,用力挣脱全山的束缚,又转身推倒了图布新。他站稳脚跟,摆出搏克手的架势说,“是个男子汉就一个一个地来。”两个男孩恼羞成怒,却不料没到两分钟被他一一放倒。两个男孩气得想一起上,阿米挺直腰板大声说:“两个欺负一个算什么本事,只会给西日嘎村的男生丢脸。”这是他阿爸以前劝架时常用的语气。此刻,他尽管特别紧张,却不断在心里默念:我是男子汉,我是男子汉……图布新恶狠狠地说:“阿米,你给我等着,明天我让阿扎过来好好教训你。”
周日这天,一大早有人来家里定制过冬的袍子。额吉匆匆吃过早饭便开始忙碌。阿米像大人似的喂牛、喂马、打扫院子。干完这些,他坐在土屋前的台阶上仰望毕勒古泰山。这座山在眼前,却又显得很遥远。他一时陷入了恍惚。“啪嗒”一声,脚下突然飞来一块石子。图布新从院墙外向他招手。他本不想理会,可他又想起图布新昨天说过的话。他不想被人看成懦夫。他进屋跟额吉说想出去玩,然后跟着图布新走进了白杨林。
林中的空地上,站着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壮实少年。全山在旁边,双手抱在胸前,冷笑着说:“阿米,你不是想单挑吗,今天满足你。”图布新说:“这是我阿扎毛度,搏克高手。”毛度什么也没说,慢慢走到空地中间直接摆出架势。图布新把阿米推到毛度面前,“阿扎,我就是被他摔的,今天你使劲摔他。”无论个头力量,还是速度技术,阿米不是毛度的对手。“踢、绊、倒!”“绊、缠、倒!”“推、拉、倒!”毛度一边快速说着术语,一边摔阿米。阿米被摔了十几次,身体要散架似的,伏在地上一时起不来。毛度摔累了,休息一会儿,然后把阿米提起来说:“以后别欺负我弟弟。”阿米胸口疼得说不出话来。
阿米回家前,用溪水洗了洗脸,但没有办法掩盖肿胀的脸蛋和胳膊。额吉看到他的样子,赶紧抱住他,惶急地问:“儿子,你这又是怎么了?”问了好几遍,阿米始终不肯说出实情,只说:“不小心摔的。”额吉给他抹完药膏,炖了一锅肉,阿米吃得满头大汗,感觉身上不怎么疼了。额吉晚上没有干活儿,让阿米在家自己写作业,她出去了一趟。一个多小时后,额吉回来了,还领来了班主任、图布新、全山,以及他俩的爷爷奶奶。他俩的阿爸和额吉都在外地打工,很少回来。图布新的奶奶在孙子的胳膊上用力拍打了几下,接着哭起来,全山的奶奶也跟着抹眼泪。图布新和全山别别扭扭地向阿米道了歉。
晚上,额吉搂着阿米一起入睡。深秋的晚风已经很凉,阿米听到了额吉轻轻的叹气声。
周一开学,图布新和全山老老实实待在课桌后面,连下课都不出去玩,在座位上低头嘀嘀咕咕。而阿米这边新朋友越来越多。老师课堂上经常向他提问,下课时也会跟他唠几句。他时不时地望向毕勒古泰山,他觉得阿爸是真的保佑他了。可当他以为一切开始好转时,放学路上又被图布新和全山截住了。阿米把零钱藏在袜子里,没有被他们翻出来。图布新说:“你在家在学校,我们不敢动你,但在外面,你这个外来的,就得听我们的。”阿米愤怒地说:“照你这么说,我们学校有很多附近村子的学生,他们都是外来的吗?你镇上读中学的阿扎,在当地人眼里也是外来的吗?”图布新被怼得哑口无言。全山说:“我们不管别人,只管你,你这个没有阿爸的杂种。”恼羞成怒的图布新跟着喊:“对,我们只管你。”三个男孩扭打在一起。一个牧羊人路过,大喝一声,把两个男孩赶跑了。阿米的肚皮被图布新的格尺划出两道长印,沁出血丝,走在路上,被衣服磨得生疼。
晚上趁着额吉还在忙碌,阿米悄悄从外屋橱柜里拎着一瓶白酒出去,来到马棚里。他把衣服向上卷起,学着阿爸以前的样子,往伤口上倒白酒。一种涩涩的刺激性的疼痛忽闪而过。两匹白马凑过来,用柔软的鼻子触碰他的额头。他缓了好一会儿才回屋。“咯噔咯噔……”额吉正在踩踏缝纫机。他钻进被窝,不知不觉睡着了。
从开学第一天起,额吉就想接送阿米,但西日嘎草原的孩子们,上三年级后都自己走读。他不想被同学们取笑,更不想占用额吉的时间。额吉为他花去的时间越多,就睡得越晚。他心疼额吉。
无论阿米怎么隐瞒,额吉和班主任还是发现了,阿米还在被欺负。班主任把全山和图布新叫到办公室,并喊来了他俩的爷爷奶奶,严厉地说:“只要再有一次,你们就不用来学校了。”阿米的额吉说:“这是最后一次,否则我一定拼命。”两个男生在大人们的监督下,写了检讨书,又给阿米道了歉。经过这次,他俩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地欺负阿米了。
初冬的雪很快就下来了。阿米在上学路上听两个牧民说,西日嘎村即将举办冬季赛马节,没有年龄限制,大人小孩都可以参赛。规则也很简单,从西日嘎村骑马到三十里外的都沁恩格尔村取上一面小蓝旗,再骑回来交到村长手里即可。冠军奖励一匹马,亚军奖励一头牛,季军奖励一只羊。阿米家乡也有这种比赛。他想起阿爸曾经拿冠军的场景。他拉着额吉的手站在家乡的山顶,望见阿爸骑着白马,像风一样驰骋在斑驳的雪野上。他沉浸在自己的回想中,全然不知图布新的手已经搭在他肩头。图布新凑到他耳边说:“这周末,我阿扎想再跟你切磋切磋,你要害怕就趁早滚出西日嘎。”全山说:“不来就是胆小鬼。”这时,走在后面的三五个同学追了上来,其中一个问:“你们想干什么?”两个男生一溜烟地跑进了校园。随后几天,两个男孩总是躲着人群商量着什么。
令两个男生没想到的是,周末阿米在树林里主动等他们。毛度好像又长高了,他脱去外套,说:“你小子挺有胆量,几天不见长能耐了,今天接着摔。”毛度边说边上前,阿米没有后退。当毛度的双手搭在他肩上,他开口说:“你一个中学生摔小学生算什么本事,赢了我很光彩吗?传出去就是笑话。有本事,你就参加冬季赛马节,跟我在赛场上一决高下。”毛度愣了,停住了手。图布新和全山急了,想上来动手,却被毛度制止。一阵风吹来,雪地上的枯叶沙沙作响。毛度把两只胳膊交叉抱在胸前,一扬下巴,说:“你再说一遍。”阿米的心怦怦直跳,他盯住毛度的眼睛又重说了一遍。图布新说:“你这是找死呢,你知道我阿扎的黑骏马有多厉害吗?”全山在一旁大笑。毛度用力揉搓几下阿米的耳朵,问:“你输了怎么办?”阿米说:“我输了,就离开西日嘎。那我赢了呢?”毛度笑了,旁边的全山说:“你赢了我管你叫爷爷。”三个男孩走后,阿米在原地站了很久,才慢慢走回家。
第二天中午,阿米牵出两匹白马,在毕勒古泰山脚的空地上骑行。额吉并不反对他参赛。她的儿子正努力融入西日嘎草原。阿米跑完几圈,牵着两匹马爬上毕勒古泰山。站在山顶,他望见了这座既陌生又亲切的村子,望见了辽阔的原野。额吉正站在院子里向他挥手。
这天下午,阿米去村北的同学家一起画画,他们正涂色的时候,图布新和全山从院门口飞奔而过,紧接着,一个男人大声骂着“小兔崽子,你们给我站住”,追着跑过去。阿米和同学放下画笔,悄悄跟在他们后面,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男人在一棵大杨树下抓住了图布新和全山,阿米和同学躲在一面土墙后面偷看。男人一手拎着一个喊:“从小不学好,带你们去村委会好好反省反省。”男人连拉带拽地拖着他们往村中心走。
同学说:“肯定是偷东西被发现了。”阿米说:“偷东西?”同学说:“他们经常一起偷东西,去年从商店偷拿了十几根雪糕,刚跑出来就被逮住了。”阿米“哦”了一声,不知不觉间,他把土墙上的一个土块捏碎了。
阿米从同学家出来后,一路踢着小石子儿回家,每过一个路口,他都会停下来向四处张望。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躲避什么,还是在期待什么。
比赛终于到来。那天,西日嘎村西坡上聚集了几十个参赛骑手。阿米穿着额吉新给他缝制的蓝色袍子,骑在白马上。一匹黑马缓缓走过来,与白马并排站立,马背上穿灰色袍子的正是毛度。他侧过身,想拉住白马的缰绳,白马一声长啸,把头用力扭向另一边。毛度对阿米说:“这可是你自找的,现在退出还来得及。”阿米握紧缰绳,目视前方,没有作声。额吉牵着另一匹白马,与班主任和全班同学一同站在场外。图布新和全山得意地向阿米做各种鬼脸,对着毛度喊加油。
白色原野就在眼前。寒气顺着袍子的缝隙往身体钻,虽然风不大,却阴阴的冷。几十匹马按捺不住地踢腾,骑手们的眼神都盯向前方。阿米紧握缰绳,身体微微前倾,小小的个头很是抢眼。
一声令下,几十匹马冲向都沁恩格尔村。阿米没想到,毛度是个好骑手。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孩子,还没有更多的骑行经验,主要还是靠着马的自身条件在骑行。他们在队伍中间,黑马在前,白马在后。不过,毛度的实力明显比阿米更胜一筹。他时不时地回头喊:“你太慢了。”阿米不急不躁。阿爸曾说过,人马合一不是指暂时的疾驰,而是人与马彼此心灵相通,持续不断地平稳前行。两村中间有一条河,河面已经结冰,只能从桥上骑过。想拿冠军的骑手们,都想率先过桥。拿到小蓝旗前,竞争还不十分明显,返回时一下子很激烈。一匹匹骏马疾驰过桥。毛度和阿米紧追不舍。当他俩一前一后接近桥头时,毛度突然扬鞭,黑马岔开道,向河边奔去。冬季的河面已然结了很厚的冰,但尚未达到冻透的程度。成熟的骑手绝不会在此刻涉险。可是毛度求胜心切,想走捷径,他毫不犹豫地纵马跳上冰面。黑马扬起四蹄。
阿米也迫切地想赢得比赛,但他牢牢记着阿爸的嘱咐,“再怎么想赢,也不能玩命。”他不由得勒住马缰。毛度前一天在冰面上撒下了黑土,他以为这样做,黑马就能飞奔过河,但黑马在冰面上只跑出十几米,就“扑通”一声,掉进裂开的冰面。黑马一阵扑腾,蹿了上去,撒腿跑了。毛度两只手紧紧抓着冰面,大半身泡进了冰窟窿里,只露出一个脑袋。阿米没有多想,调转马头奔向河边。阿爸说过,草原上的人们不会光想着自己。他用脚后跟用力蹬马肚,让白马飞奔。
到了河边,白马不住嘶鸣,来回踱步,不肯上冰面。毛度的手因僵硬而蜷曲着,打着哆嗦,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阿米跳下马,轻轻地走过去,匍匐在冰面上。他抓住毛度的两只胳膊,用力往上拉。
冬日暖阳下,一匹白马急速奔跑,马背上两个少年手中举着蓝旗,西日嘎原野在眼前晃动。额吉和几个牧民骑马向他们奔来,远处的毕勒古泰山上飘荡着一片片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