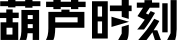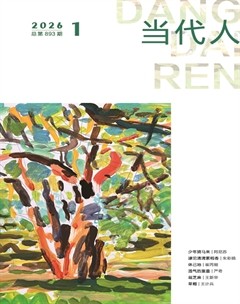“这雨已经下了一个世纪了。”旅行者从打盹中醒来,听见后座的乘客说。与窗外的雨不同,那句话带来的雨雾更加迟疑,慢慢移来,散开在他头顶。他走神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很奇怪,上车的时候还是阳光明媚,一群人挤在小小的候车亭里躲荫呢。他向车窗看去,那里被纵横分割的大块玻璃蒙上了一层水汽。
街上行人被雨线分割,每一个人都陷在移动的透明格子里,被不断垂下的雨帘贴紧。他把眼睛收回,车里的乘客并不是很多,座位没有全部坐满。雨水从四面八方赶来,敲打着车厢,使车内的压强升高,有一种无形的挤压之感。
“这雨已经下了一个世纪了,”后座的乘客又嘟囔了一声,“人都要发霉了。”旅行者回头一看,一个七十岁上下的老妇人,头上裹着丝巾,只露出一张脸,两只眼睛像两口井,什么都装得下。他飞快地把头转了回来,生怕自己会掉进去。对于她的夸张他深有同感,坐在这逼仄的车厢里,潮气无孔不入,人浑身不舒服。雨水和雾气像薄膜一样在车外层层包裹,这辆车不是自己在行驶,它是一个被打包好的包裹,正在被递送途中。递送之途耗尽了一个世纪。
但是他很清楚,上车后根本没过多久,自己也就打了个盹儿,做了个梦。梦中他独自坐在马车上,距离车夫只有一两米,却根本看不清他的面容。马车飞驰,没有马蹄声,耳旁甚至没有风的呼啸。远远地,一座城堡稳稳地立在那里,两个圆形的大窗户像两只眼睛看定了他。他感觉不是马车将他驮过去的,而是被这两只眼睛抓过去的。到了跟前,发现竟然是一座金字塔,下大上小的三角体,超稳定结构。他围着塔走了一圈,始终无法找到入口,它就像用一整块巨石雕成,甚至没有一条缝隙。他回到它的正面站定,看着中央的一枚石玫瑰。右手握住,用力旋转,没有丝毫动静,他的手上渗出了血,原来玫瑰上有极为细小的刺。刺是如此之细,他的手甚至感觉不到痛。看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禁区。
车子忽然颠簸了一下,把他从回想中拉回。而由这梦中的玫瑰,他才想起自己为何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一个偶然机会,某个豆友在他的小站留言,他回应了一下,这成为他们不时聊几句的契机。一聊就是两年。他们从未谈起个人生活,甚至也没透露过自己的长相,不过每有新作则发给对方阅读批评。正是从这阅读中,他隐约知道她所在的城市,那是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几乎就是世界的另一边。大约一年前,他忽然对什么都厌倦了,不仅日常生活已经发馊,甚至对每天敲下的鬼魅般的文字也感到倦怠。而就在那时,他发现自己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恋,和她聊得更多。她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天,他说想去找她,她不置可否,只回了一句:你会迷路的。
邻座的乘客哼唧了一声,也醒了。他身体肥胖,打瞌睡时发出低沉的呼噜声,像在赶走什么东西。现在他用肥厚的手揉了揉眼睛,往旅行者这边的车窗望出去。“西公园”,他轻轻念出三个字,忽然大喊起来,“这是往哪里开啊!西公园,我们已经出城了!”几个乘客连忙凑过来猫下腰往外看,其中一个穿着麻布衫手戴核雕手串的中年人很快镇定地站直了身子,说:“这趟车本来就有一段是在市郊行驶的,没错。”他右手中的折扇在左手掌里敲了几下,很笃定。但是立即有人附和胖子的意见,说这趟车他经常乘,它一直都在市区开的,经过的都是超市、菜场、商场,不应该经过市郊的西公园。在众人的争论声中,一个轻柔的声音说道:“我们把窗户擦干净,仔细看看就知道了。”这声音并不高,但是却像一阵风吹开灰尘。车厢里的争论声小了一点,然后又恢复了前面的热烈,就像一股水被暂时分开了一下,马上又合拢了。
旅行者连忙循声看去,是她,那个在公交站台上穿白裙子的女子。那时天气晴朗,他看见纯净的蓝天向着远方无限延伸,有仙女骑着白鲸飞过,从它的尾鳍上不时掉落一串串棉花糖,悬挂在半空中。等他把仰望的双眼下移,就看见她斜靠在广告亭边的长凳上,她的眼里也有两朵棉花糖漂浮着。她怀里抱着一只花瓶,里面插着三只干莲蓬。不知怎么,他脑海里浮现出了油画《陶》,可能是因为她身上的白裙子,也可能是莲蓬头上密匝的孔洞让人想起蜂房。“花房与蜜脾,蜂雄蛱蝶雌。”他脑海里忽然闪出这两句诗,脱口而出后不由自主地笑了。她却以为他是在向自己打招呼,便用微笑回应。那微笑像孙悟空施展法术一般,对着一只兔子射出一束强光,整个把他笼罩住,他感觉自己很快就会从人身恢复兔身,温驯地依偎在某个怀抱里。
他鬼使神差地接了一句:“你这是要‘留得枯荷听雨声’吗?”
“这花瓶里装的就是雨声,我抱着它走到哪里,雨声就在哪里。”她淡淡地狡黠地说,那声音也仿佛雨声,清脆,清亮,他的耳朵忽然伸长,像一只长长的喇叭。他不由定定地看了她好久,她的眼神没有躲闪,友好而平静。
他忽然意识到那就是她,这说话的语调他再熟悉不过了,而且就在这个城市,那必定是她。一阵汽车喇叭的催促声将他从中拔出来,慌乱之下他跳上公交,没想到她也上了车。
“对,大家认真看看窗外就知道了。”听到她说的,他不由附和,说完就去擦窗户。
这时后座的老妇人开口了:“你们这是瞎操心,我们只要相信司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