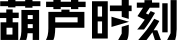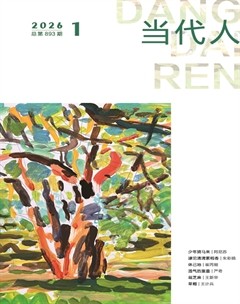村里时兴过箱,彩绘着喜鹊登枝、缠枝牡丹等图画的箱,简约古朴的红漆大箱,总有几分富丽神秘之感。我要说的,却是一只木头做的冰糕箱或曰书箱,不同时期,它分别属于母亲和我。
母亲骑一辆那个年代老式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车后驮着冰糕箱,箱里面放一块棉布,棉布下整齐地躺着甜丝丝儿的凉津津的冰糕宝宝们。“冰糕——!牛奶、白糖冰糕——!”她高声叫卖着。那时还不足五周岁的我不止一次在我家巷子口张望,看她轻快地从车上跳下来。暮色在她身后很快合拢,母亲推着自行车,带着疲惫而满足的表情带我回家。父亲帮她把冰糕箱搬下来,把棉布里的冰糕水慢慢倒出来,把化了半截的冰糕小心拿着放到碗里给我们留着,这也是那时我最期待的时刻。
母亲清理干净冰糕箱后把身上所有的硬币和毛票都掏出来,放在桌子上,一个一个分类点数。五分的,一分的,二分的。每一摞分币够一个整数的时候就把它们用纸卷成一个硬挺的小圆柱。那些分币、毛票带着她对未来好日子的憧憬——她想靠自己的劳动盖我们自己的新房。
一
父亲和舅舅不止一次讲过关于母亲的故事:八岁以前的母亲在山西太原生活。按她生于1951年来推算,她在太原的生活是在1958年之前。姥爷在太原一家公私合营的公司做财会工作。大概是时代的原因,母亲跟随姥爷回到邢台南和的老家,一家人也由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变成了农民。成年后的母亲一心想过上工人家属的生活,加之她和姥爷不对脾气,总是拌嘴吵架,就想远嫁他乡隔开矛盾。于是母亲不顾家人反对,经人介绍铁了心要嫁给当时据说是矿工的父亲。可始料不及的是,婚后父亲转正前政审没能通过,同样被打回到农村的土地上,母亲的工人家属梦就此破碎。但她很快适应了农村的环境,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勤快获得了乡亲们一致的称赞。
大概在1980年吧,那时政策允许人们小本经营了。她请人做了一个木质的冰糕箱,在木箱外漆上白漆,用紫红的漆写下“邢台”和“牛奶冰糕”。这冰糕箱对于她的意义不亚于人力车对于祥子的意义。她用自行车驮着这个简陋的冰糕箱开始了早出晚归的经营。因为后座上有箱子,她必须从车子前面的大梁上上下。那些天,每天母亲都会早早起来到邢台市里批发冰糕,再走街串巷叫卖,卖完以后才回来。忙碌一天后,母亲回来时的声音有些嘶哑无力,但她始终是愉快的、喜悦的——因为她的计划正在一天天实现:房基地有了,排好地基了,砖也都买回来了,沙子、水泥也已经拉了,连门窗、檩条等木料也都备好了。
可就在一切就绪的时候,母亲病了。开始家里人都不在意,以为母亲要给我生小弟弟了。可情况越来越不对劲,母亲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